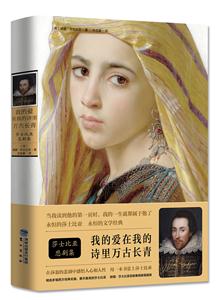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5912685
- 條形碼:9787545912685 ; 978-7-5459-1268-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本書特色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特色一:
莎士比亞是舉世聞名的劇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朱生豪是我國著名的翻譯 家,由他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語言生動優美,感情熱烈,贏得里廣大讀者的青睞。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特色二:
在這個喧囂浮躁的商業時代,藝術也變得粗制濫造,重溫經典,提高人們的藝術水準,在今天這個時代,顯得尤為重要。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特色三:
本書收錄了莎士比亞*經典的五部悲劇作品,也是現代劇院經常演出的作品,舞臺戲劇的興盛也必然帶動人們的閱讀興趣。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特色四:
書中插入悲劇作品的經典圖片,圖文并茂。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內容簡介
經典的藝術不會被時代淘汰,莎士比亞離開我們已經幾百年了,他的名字和作品依然為大家所熟知。悲劇能引發人的思考。莎士比亞的悲劇作品不僅在于故事的新奇曲折,更在于其蘊藏的豐富而深刻的人性,正如說不盡的哈姆萊特,歷史不斷變化,但人性古今相通,所以時至今日,莎士比亞作品依舊是藝術家樂此不疲的研究對象。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前言
序 言
震撼人心的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以《哈姆萊特》和《奧瑟羅》為例
傅光明
時代的靈魂……舞臺的奇跡……你的藝術是永恒的紀念碑,只要你的書在,你就永遠活著……他不屬于一個時代,他屬于千秋萬代。
——【英】本•瓊森
當我讀到莎士比亞的**頁時,我的一生就都屬于他了!
——【德】歌德
關于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代整個的戲劇情形,以及莎士比亞如何寫起戲來,大體如美國作家愛默生所言:“莎士比亞的青年時代正值英國人需要戲劇消遣的時代。戲劇因其政治諷喻極易觸犯宮廷受到打壓,勢力漸長、后勁十足的清教徒和虔誠的英國國教信徒們,也要壓制它。然而,人們需要它。客棧庭院,不帶屋頂的房子,鄉村集市的臨時圍場,都成了流浪藝人現成的劇院。人們喜歡由這種演出帶來的新的快樂,……它既是民謠、史詩,又是報紙、政治會議、演講、木偶劇和圖書館,國王、主教、清教徒,或許都能從中發現對自己的描述。由于各種原因,它成為全國的喜好,可又絕不引人注目,甚至當時并沒有哪位大學者在英國史里提到它。然而,它也未因像面包一樣便宜和不足道而受忽視。”包括托馬斯•基德、克里斯托弗•馬洛、本•瓊森在內的一大批與莎士比亞同時代,且名氣并不在他之下的詩人、戲劇家,全都突然涌向這一領域,便是它富有生命力的*好明證。
那時的情形是(今天也未必不是),對于為舞臺寫作的詩人(今天的編劇大多已不是詩人),沒有比通過舞臺把握住觀眾的思想更重要的事,他不能浪費時間搞無謂的試驗,因為早有一批觀眾等著看他們想看的,那時的觀眾和他們期待的東西非常之多。
莎士比亞也不例外,當他剛從外省鄉下的斯特拉福小鎮“漂”到帝都倫敦搞“文創”時,那兒的舞臺早已經開始輪流上演大量不同年代、不同作家的劇本手稿。眾口難調,有的觀眾對《特洛伊傳奇》每周只想聽一段,有的觀眾則對《愷撒大將之死》百聽不厭,根據古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改編的故事總能吸引住觀眾,還有觀眾對演繹從傳說中的亞瑟王直到亨利王室的大量歷史劇十分著迷。總之,連倫敦的學徒,都能對許多凄慘的悲劇、歡快的意大利傳奇,以及驚險的西班牙航海記耳熟能詳。所有這些歷史、傳奇,上演之前都或多或少經過劇作家的改編加工,等劇本手稿到了舞臺提詞人的手里,往往已是又臟又破。時至今日,早沒人說得出誰是這些歷史/傳奇劇的**作者。長期以來,它們都屬于劇院財產,不僅如此,許多后起之秀又會進行修改或二度編劇,時而插進一段話,植入一首歌,或干脆添加一整場戲,因而對這多人合作的劇本,任何人都無法提出版權要求。好在誰也不想提,因為誰都不想把版權歸個人,畢竟讀劇本的人少之又少,觀眾和聽眾則不計其數。何況劇作家的收入源于劇院演出的賣座率及股份分紅。就這樣,無數劇本躺在劇院里無人問津。
莎士比亞及其同行們,十分重視這些丟棄一旁、并可隨拿隨用的老劇本。如此眾多現成的東西,自然有助于精力充沛的年輕戲劇詩人們,在此之上進行大膽的藝術想象。
無疑,莎士比亞的受惠面十分廣泛,他善于、精于利用一切已有的素材,從他編寫歷史劇《亨利六世》即可見一斑,在這上中下三部共計6043詩行的作品中,有1771行出自他之前某位佚名作家之手,2373行是在前人基礎上改寫,只有1899行屬于貨真價實的原創。
這一事實不過更證明了莎士比亞并非一個原創性的戲劇詩人,而是一個天才編劇。但不得不承認,且必須表達由衷欽佩的是,莎士比亞是一位世所罕見的順手擒“借”的奇才,干脆說,他簡直是一個既擅、又能、還特別會由“借”而編出“原創劇”的天才。不論什么樣的“人物原型”“故事原型”,只要經他的藝術巧手靈妙一“借”,筆補神功,結果幾乎無一不是一個又一個的“原型”銷聲匿跡無處尋,莎劇人物卻神奇一“借”化不朽。哈姆萊特、奧瑟羅、李爾王、麥克白,無不如此。因而,對于莎翁讀者、觀眾,尤其學者,不論閱讀欣賞,還是專業研究,都仿佛是在莎士比亞浩瀚無垠的戲劇海洋里藝海拾貝,無疑,撿拾的莎海藝貝越多,越更能走進他豐饒、廣袤的戲劇世界。
不光莎士比亞,生活在那一時代的戲劇詩人或編劇們,大都如此“創作”,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對作品的原創性興致不高,興趣不大。換言之,為千百萬人獨創的文學,那時并不存在。在那個還沒有文學修養的時代,無論光從什么地方射出,偉大的詩人都把它吸收進來。他的任務就是把每顆智慧的珍珠,把每一朵感情的鮮花帶給人們;因此,他把記憶和創造看得同等重要。他漠不關心原料從何而來,因為無論它來自翻譯作品,還是古老傳說;來自遙遠的旅行,還是靈感,觀眾們都毫不挑剔,熱烈歡迎。早期的英國詩人們,從被譽為“英國文學之父”的喬叟那里受惠良多,而喬叟也從別人那里吸收、借用了大量東西。
莎士比亞是幸運的!
以《哈姆萊特》為例,它既是莎士比亞戲劇生涯“兩個世紀”的分水嶺,也是里程碑,以他開始寫這部不朽之作的1600年來劃線,如果他在這一年去世,后人只能隨著16世紀的結束看到他上一個世紀的劇作,而所有這些尚不足以證明他是個徹底的天才。他在揭開了17世紀新紀元之后的短短幾年里,接連為時人,更為世人,奉獻出后來者難以逾越的堪稱戲劇巔峰之作的四大悲劇——《哈姆萊特》《奧瑟羅》《李爾王》《麥克白》。
即便我們不能說《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劇作中*偉大、*震撼人心的一部,但可以明確地說,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創造的*偉大、*永恒的一個戲劇人物。從誕生的那一天起,他就像莎士比亞一樣,不僅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千秋萬代。只要人類存在,他的靈魂便永遠不朽。莎士比亞在他身上挖掘出了人性深處*豐富、*復雜的隱秘世界,在我看來,莎士比亞是要把他塑造成一個永恒的生命孤獨者。顯然,這樣的塑造又是與他天才的藝術構思和想象密不可分。
“有一千個讀者(觀眾)就會有一千個哈姆萊特”,照這句話,我們都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千分之一個“哈姆萊特”。這非常好理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他身上看到躲藏在靈魂深處的自己。如法國史學家丹納所說:“莎士比亞寫作的時候,不僅感受到我們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還感受到許多我們所沒有感受到的東西。他具有不可思議的觀察力,可以在剎那間看到一個人完整的性格、體態、心靈、過去與現在,生活中的所有細節與深度以及劇情所需要的準確的姿態與表情。”
愛默生認為,莎士比亞有著令人匪夷所思的、出類拔萃的才智:“一個好的讀者可以鉆進柏拉圖的頭腦,并在他腦子里思考問題,但誰也無法進入莎士比亞的頭腦。我們至今仍置身門外。就表達力和創造力而言,莎士比亞是獨一無二的。他豐富的想象力無人能及,他具有作家所能達到的*敏銳犀利、*精細入微的洞察力。”
在此,僅舉一個小例子:“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幾乎是莎士比亞為哈姆萊特量身定做的*為人知的一句臺詞,而且,在中國,*為深入人心的是朱生豪的譯文:“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但在英文里,顯然沒有“值得考慮”的意思。梁實秋將此句譯為:“死后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問題。”并注釋說,因哈姆萊特此時意欲自殺,而他相信人在死后或仍有生活,故有此顧慮不決的獨白。梁實秋的“這是問題”簡單而精準。孫大雨的譯文:“是存在還是消亡,問題的所在。”對原文的理解和表達,同樣精準。照英文字面意思,還可以譯出多種表達,比如,“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或者“生,還是死,這是個問題”“活著,還是死掉,這是個問題”。
有意思的是,在1603年印行的**個四開本的《哈姆萊特》中,此句原文是: “To be, or not to be, I there's the point.”按這個原文,譯成中文,意思是:“對我來說,活著還是死去,這點是*要命的。”或“我的癥結就在于,不知是該活著,還是去死。”或“*要命的是,我不知是該繼續茍活于世,還是干脆自行了斷。”無論哪種表達,均符合哈姆萊特此時在自殺與復仇之間猶疑不決的矛盾心緒。而“值得考慮”四個字,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哈姆萊特在嚴肅認真、細致入微地思考著關于人類“生存”還是“毀滅”的這個哲學問題或命題,而不是自己的生與死。
從“**四開本”的印行情況來看,“I there's the point”作為*早演出時的臺詞,更大的可能還是出自莎士比亞之手,但出自演員之口并非沒有可能,而“that is the question”顯然是修改之后作為定本留存下來的。不過,無論“the point”(關鍵)還是“the question”(問題),意思都是“關鍵問題”。因此,在這個地方,我愿把它譯成:“是活著,還是死去,我的問題就出在這兒。”這自然是個人的一點理解。但我想,若把深藏于莎士比亞不同版本里諸如此類的微妙多多地挖掘出來,會十分有意思,至少非常有趣。
《奧瑟羅》是“四大悲劇”中的一個例外,例外在于它出現了兩個男主人公。
英國著名戲劇史家約翰•尼科爾在其皇皇六卷本的《英國戲劇史(1660-1900)》中說:“在一些悲劇,尤其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中,男主人公不僅有一個,還會有兩個,而悲劇情緒就來自這兩位主人公的個性沖突。《奧瑟羅》的男主人公到底是誰?可以說,奧瑟羅本人在*后一幕之前,沒做過任何事。我們在這部劇中看到了兩個主人公:伊阿古以一種人性中的可怕弱點,玩弄著一個冷酷無情的欺騙把戲;奧瑟羅則以另一種不同于伊阿古的人性弱點,逐步走向自我毀滅。它不像《哈姆萊特》和《李爾王》那樣的戲,只有單一的男主人公。”
不必諱言,以刻畫人物性格來說,伊阿古是《奧瑟羅》劇中形象*豐滿的一個,在舞臺上似乎更是如此,他一張口說話,一舉手投足,便渾身充滿了戲。奧瑟羅、苔絲狄蒙娜、凱西奧,更別說羅德利歌,都是他手里操控的玩偶。他牽動著他們,同時也牽動著劇情演繹的每一條神經。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他幾乎搶了所有人的戲。《奧瑟羅》因伊阿古而悲得出彩、好看。甚至可以說,悲劇《奧瑟羅》的藝術成功,不在于它塑造了一個叫奧瑟羅的“愚蠢的”被害之人,而多半在于它塑造了一個叫伊阿古的“精彩的”害人者。假如兩個人的戲份兒加在一起是10分,伊阿古至少占6分。比較來看,奧瑟羅更像一個速寫白描的粗線條人物,雖有棱角,卻處處顯得硬邦邦的,而伊阿古簡直就是一個三維立體的魔鬼化身,那么逼肖,那么鮮活,那么富有大奸到極點的靈性,那么富有大惡到透頂的魂魄。
沒錯,伊阿古就是一個徹頭徹尾、邪惡陰毒、罪不容誅、該下地獄、永劫不復的卑鄙惡棍、流氓無賴、奸佞小人,把一切形容壞人的毒詞惡語一股腦全倒灌在他身上,諸如卑劣、無恥、齷齪、陰險、好色、貪婪、歹毒、奸惡、殘忍、冷酷、無情、嗜血、小肚雞腸、猜忌成性、口蜜腹劍、利令智昏、詭計多端、背信棄義、心狠手辣、喪盡天良、無惡不作之類,一點也不為過。在莎士比亞筆下,伊阿古堪稱壞人堆里的人尖兒,即便放到世界文學專門陳列壞人的畫廊里,縱使不能搶得頭牌,位列三甲絕無問題。
伊阿古不信天堂,邪惡就是他的人性惡魔,是他一切行為的出發點,是他生命的本錢和人生的指南。如此,莎士比亞創造的伊阿古這個文學藝術形象,具有了一種象征意味,即伊阿古就是那個寄居在人心*黑暗處優哉游哉的魔鬼的代表,一方面,他預示著人類一旦打開心底的潘多拉盒子,把這只魔鬼放出來,它就會不擇手段地把人的命運玩弄于股掌之間,直至將其毀滅;另一方面,他的邪惡本身又是折射人類齷齪人性的一面鏡子,它無情地暴露出,面對笑容可掬到討人喜歡的魔鬼的誘惑,人類會變得多么愚蠢,多么脆弱,多么容易上當受騙,又是多么心甘情愿、樂此不疲地當玩物,以致行為荒誕、人格缺陷、意志薄弱,像奧瑟羅一樣,*后走向自我毀滅。
不論從哈姆萊特、奧瑟羅、李爾王,還是從伊阿古、麥克白,都能斷言,莎士比亞看透了我們!無論是他那個時代的“我們”,還是今天的,抑或未來不斷延續著的“我們”。不是嗎?從人性上看,莎士比亞所挖掘的伊麗莎白時代人性上的齷齪、卑劣、邪惡,并不比“我們”現在更壞,而今天“我們”在人性上所表現出來的高貴、尊嚴、悲憫,也不見得比那個時代好多少。
在此,我們要談及兩個非同尋常的話題:
**,莎劇文本與舞臺演出的關系。
盡管莎士比亞*早是為了舞臺演出而寫戲,(也許僅僅為了多掙錢),盡管莎劇演出史已超過四個世紀,但仔細揣摩查爾斯•蘭姆200年前說過的話,并非沒有道理。蘭姆始終認為,高山景行的莎劇,那一點一滴的原汁原味,都只在他劇作文本的字里行間,舞臺上的莎劇無滋無味、無韻無致。換言之,莎士比亞的文本詩劇與舞臺演出本是云泥之別,莎劇只能伏案閱讀,根本不能上演!
時至今日,該如何理解蘭姆呢?一方面,蘭姆所說并非無的放矢,他那個時代雄踞舞臺之上的莎劇,的確多經篡改,原味盡失;另一方面,蘭姆意在強調,由閱讀莎劇文本生發出來的那份妙不可言的文學想象,是任何舞臺表演所無法給予的。莎劇一經表演,文學想象的藝術翅膀便被具象化的舞臺人物形象束縛住,甚至限制死。
第二,莎劇戲文與《圣經》文本的關系。事實上,對于讀者或觀眾的欣賞和理解來說,這一點比**點更為重要。
英國著名莎學家弗雷德里克•博厄斯說:“《圣經》是莎士比亞取之不盡的源泉,甚至可以說,沒有《圣經》就沒有莎士比亞的作品。……即便有誰能禁止《圣經》發行,把它完全焚毀,永絕人世,然而《圣經》的精神結晶,它對于正義、寬容、仁愛、救贖等偉大的教訓,及其罕貴無比的金玉良言,仍將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永世留存。”換言之,莎翁作品凝結著《圣經》的“精神結晶”。英國文學教授彼得•米爾沃德牧師甚至斷言:“幾乎《圣經》每一卷都至少有一個字或一句話被莎士比亞用在他的戲里。”
的確,莎士比亞對《圣經》熟悉到了完全能隨心所欲、不露痕跡、運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境地。在全部莎劇中,幾乎沒有哪一部不包含、不涉及、不引用、不引申《圣經》的引文、典故、釋義。我們要做的,是努力、盡力去尋覓、挖掘、感悟和體會莎士比亞在創作中是如何把從《圣經》里獲得的藝術靈感,微妙、豐富而復雜地折射到劇情和人物身上的。因此,如果不能領略莎劇中無處不在的《圣經》意蘊,對于理解莎翁,無疑是要打折扣的。
從這個角度說,豐富的注釋、翔實的導讀,不失為解讀、詮釋莎劇的一把鑰匙,也是開啟他心靈世界精致、靈動的一扇小窗。
提及莎士比亞,英國詩人、批評家阿諾德說:“恐怕這是所有詩人中*偉大的名字,一個永遠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
天長地久,莎翁不朽!
2016年9月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目錄
Ch2.哈姆萊特
Ch3. 奧瑟羅
Ch4. 李爾王
Ch5. 麥克白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節選
羅密歐 沒有受過傷的才會譏笑別人身上的創痕。輕聲!那邊窗子里亮起來的是什么光?那就是東方,朱麗葉就是太陽!起來吧,美麗的太陽!趕走那妒忌的月亮,她因為她的女弟子比她美得多,已經氣得面色發白了。既然她這樣妒忌著你,你不要皈依她吧;脫下她給你的這一身慘綠色的貞女的道服,它是只配給愚人穿著的。那是我的意中人。啊!那是我的愛。唉,但愿她知道我在愛著她!她欲言又止,可是她的眼睛已經道出了她的心事。待我去回答她吧;不,我不要太魯莽,她不是對我說話。天上兩顆*燦爛的星,因為有事離去,請求她的眼睛替代它們在空中閃耀。要是她的眼睛變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變成了她的眼睛,那便怎樣呢?她臉上的光輝會掩蓋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燈光在朝陽下黯然失色一樣;在天上的她的眼睛,會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鳥兒們誤認為黑夜已經過去而唱出它們的歌聲。瞧!她用纖手托住了臉龐,那姿態是多么美妙!啊,但愿我是那一只手上的手套,好讓我親一親她臉上的香澤!
朱麗葉 唉!
羅密歐 她說話了。啊!再說下去吧,光明的天使!因為我在這夜色之中仰視著你,就像一個塵世的凡人,張大了出神的眼睛,瞻望著一個生著翅膀的天使,駕著白云緩緩駛過天空一樣。
我的愛在我的詩里萬古長青-莎士比亞悲劇集 作者簡介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華人社會常尊稱為莎翁,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最偉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學家之一。他流傳下來的作品包括38部戲劇、154首十四行詩、兩首長敘事詩。他的戲劇有各種主要語言的譯本,且表演次數遠遠超過其他任何戲劇家的作品。
朱生豪(1912-1944):浙江嘉興人。原名朱文森,又名文生,學名森豪,筆名朱朱、朱生等。翻譯家,詩人。共譯莎劇31部半。
- >
推拿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煙與鏡
- >
我與地壇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