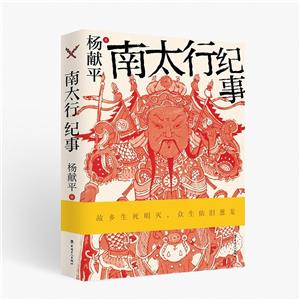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南太行紀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0874713
- 條形碼:9787500874713 ; 978-7-5008-7471-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南太行紀事 本書特色
首屆冰心散文獎得主力作;大地原聲與現場精神 人間煙火與眾生關懷;每個人都是有光的
南太行紀事 內容簡介
用文字“鉤織”出北方鄉野的生民形象,為更多的“無聲者”在紙上留下細小又隆重的痕跡。
這是楊獻平數十年來對南太行鄉域的觀察。既包括了一方地域自然、人文生態,也包括了在一定特定地理環境之間一群人與他們中個體的現實際遇。其中有對生死愛恨等永恒主題的呈現,也有對鄉村既往史和現實層面的思考。
南太行紀事 目錄
南太行民間秘史
南太行的風花雪夜
南太行鄉村筆記
南太行紀事 節選
為故鄉的南太行 1. 兩起車禍 從林哥死了!七天前,另一個外鄉人也死了,兩人在同一個地方!聽到這個消息,我腦袋轟隆作響,一股寒意旋即襲身。此前一個月,我還在老家,和從林一起吃飯、喝了幾杯酒。不過一個月,他卻轉身沒了。這太令人猝不及防了。放下電話,我心情持續灰暗,似乎被鐵屑塞滿,眼淚下落,但又不知為何。傍晚,打電話給母親,她的語調也有些黯淡,說了幾句自家的事,母親正要說這件事,我提前打斷說,我知道,我知道,弟弟跟我說了。母親嘆息,從她的聲調中,我也覺得了一種物傷其類的悲涼與黯然。 真正能夠震撼與打倒人的,從來只有自己人和來自身邊的某種事情。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早年當過三年兵,復員后娶妻生子,日子再難過,即便孩子大人破衣爛衫,也絕不會出去打工掙錢,以做小買賣,甚至以退伍軍人身份到各級政府要撫恤過日子,母親還在世的時候,他經常去蹭飯,其母過世,新農村建設,他承擔了全村的垃圾清理運輸。這才不過三四年時間,誰知道,卻在初冬的一個早晨,由于三輪車失控,撞在墻壁上,肋骨折斷,插入肺中,到醫院搶救無果,剛回到村子,就咽下了*后一口氣。 在我們村幾百年的歷史上,也只有他和另外一個堂哥死于車禍。無獨有偶的是,七天前,邢臺縣幾個人到我們村買舊石板,下坡路上,車子翻了,其中一人當場喪命。這兩人出事的地點,一在我幼年經常出入的村口,一在我們新家前面一道山嶺之下。兩者時間相隔七天。七天的“七”,在民間傳統中,是頗有些意味的,諸如“頭七”“七災”“空七”“沖七”“燒七”“犯七”,等等,其中包含甚至充斥的,盡是死亡和驚悚。 弟弟在說這件事的時候,語氣略有些平靜。我不知道他當時的心態。與我相比,他天天在那座名叫南溝的村莊,與那里的人幾乎天天見面,甚至隔河相望。也許在他看來,這些意外都是正常的。這些年,弟弟在外跑車,日復一日,每次電話,我都要叮囑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他每次都嗯嗯答應。他也說過,這些年在不同的路上跑,哪一年都會遇到別人的一些車禍,其狀慘不忍睹或蹊蹺異常。但他卻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極少去敘述怎么樣的一種見聞,哪怕再驚心動魄,他也覺得那些事情是該發生的,或者發生了,再說出來意義不大。這一次,他仍舊保持了自己沉默的本分,對從林哥及那位外地人的車禍,采取了一種司空見慣的口吻。 而我在千里之外。故鄉,或者說,故鄉的每一個人,其實我都熟悉,每次回去,看到他們逐漸老去,依舊在小小的村莊里爬山上坡,下地過河,不知名的孩子們很多,也紛紛長大,眨眼之間或是出嫁了,或是娶媳婦了。無論他們與我們家關系好壞,我都覺得,他們是長久的,誰也不會乍然而去,尤其是不會發生什么異常慘烈的禍端——死亡之事。從林哥的死,一下子顛覆了我久已形成的思維慣性,即在一個車輛極少、道路彎曲的鄉村,可能會有外鄉的行車人因為車禍而罹難,本地人則絕對不會。 當代文明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機器和各種智能工具逐漸代替并且壟斷了人的本能和技能,機車便是其中*典型的。工具助人,再返回來限制人和削弱人,甚至對人進行某種意義的“反動”與“無形切割”,這是必然的事情,也將是人類面對的又一個強大的課題。 整整一天,因為從林哥及那位外鄉人在我們村外的死,我心情灰暗,一整天都在被一種黏稠而腐朽的氣息所籠罩,幾乎喘不過氣來。下班,與妻子說起,她也覺得悲傷,說生命的脆弱與無常。我很快就把話題引到了別處。因為我知道,很多負面的消息與能量,*好不要帶給其他人。這時候,我才想起,前幾年,另一個堂哥曾無意中對我說,我們這一脈楊姓人家的族譜,就在從林哥手中。 從林哥也姓楊,兩百年前,我們還是一家人。 中國的家族,向來是先整體而后逐漸分散開來的。其中除了姓氏,同在一方地域生存繁衍之外,還有一根看不見的血線,將彼此緊緊相連,并且永難更改。盡管,因為戰亂、災禍等原因,有一部分人會遠走他鄉,有一部分人堅守原地,或者再從外地遷回來。時間在萬物之間的作用,顯然是巨大且又幽邃無比的,它不斷地稀釋和收集生死。 血緣變淡之后,即便曾經的同胞兄弟姐妹,人和人之間不僅也會陌生、疏遠起來,而且會時常因為某些資源和利益,甚至雞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攻訐、傷害,進而滋生出諸多的怨氣和仇恨,以至于你死我活,勢不兩立者有之,老死不相往來,背后捉弄與作踐、戕害的也不在少數。 這是人間的奇觀之一,也是人性幽暗與人心不定的根本所在。盡管,在我們南太行鄉村楊姓聚居的村莊,這類情況也比較常見,但沒有特別出格的事情。這其中,固然有行政及法律的作用,還有所謂的古老的“天條”與道德上的某些“律令”的約束。“行政”和“法律”的設置,其目的就是遏制人性之惡,而所謂“天意”或者冥冥中的“律令”則顯得玄秘而又不確定。 2. 血緣意義上的合作與“開枝散葉” 前些年,曾有幾次,我找到從林哥,拐彎抹角地說起家譜。他濃眉大眼,說話甕聲甕氣,嘴角間或有口水流出來。可無論我怎么說,他都說,沒見到,不知道。我無奈。也想不通,一個家譜,應當為族人共享才是,自己留著毫無用處,只能在時間中越來越陳舊。現在的年輕人也都對這些沒有興趣。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多掙錢,*好暴富,是如何把自己家的日子過在別人前頭,*好是方圓幾十里內獨一家。 可我還是很在乎家譜,我已經是小五十歲的人了。人年紀越大,越會在意來處與歸處。我小的時候,常聽爺爺說,我們這脈楊姓人家,包括沙河西部丘陵及太行山區的諸多村落里的人們,是明朝年間逐漸從山西洪洞一帶遷徙而來的。爺爺還說,在我們與山西左權縣分界的摩天嶺上,長有一棵大槐樹,一邊遮著河北,一邊籠罩山西,因此,我們都自稱為“大槐樹下的人”;民間還有身體的證據用來佐證說,凡從大槐樹下遷徙而來的人,腳的小拇趾甲不成型,且是兩瓣的,走路喜歡背著手。對此,民間有言“走起路來背抄手,小拇趾甲是兩個。” 關于這一段歷史,《明史·太祖本紀·成祖本紀·食貨志》等記載,明朝年間的移民的目的,一是充實北平及其周邊,二是朱棣將江浙一帶的部分富商遷徙至京都,三是將山西長治、榆中一帶的人充斥到河北北部、中部和南部及北京等地。其中有流民、犯官、殷實人家與富家商賈,以及赤貧之民等。其中,以赤貧之民人數為*多。 2012年2月16日河北新聞網的一則《沙河一退休教師修家譜印證明朝移民史》報道說,沙河退休教師任廣民所持家譜記載曰:“吾任氏住山西洪洞,自大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奉詔遷內地古溫州河(沙河)南岸下解。而此處民稀地荒,平野之間無非蓬蒿萋萋、荊棘森森、一望漫漫、寒煙而已。吾始祖諱泰身居此村,房屋盡壞,存身危難,唯營穴而居。于是開荒野矣種五谷;辟荊棘矣植良木。數年之間,衣食繼日,良木勝用。經營房屋以居身;造書舍以聘士儒。設教子孫,講明人倫。”如此說法,與今人冀彤軍在明、清《沙河縣志》基礎上修撰而成的《沙河市志》中“明洪武至永樂年間,朝廷多次下詔從山西向直隸等地遷民,有不少人從山西中南部的榆次、平定、太谷、洪洞、沁州、潞安、遼州等地遷至沙河縣。永樂以后,仍有遷入者。據不完全統計,沙河縣有近一半的村莊由遷民所建”的記述吻合。 任廣民所在的沙河市十里亭鎮下解村,在我所指的南太行,即今河北沙河市、武安市和邢臺縣西部農村與山西左權縣、和順縣接壤的地帶以東60公里,處在邢臺市羊范鎮和沙河市白塔鎮之間。從任廣民家譜記載中可以看出,他們這一脈任氏家族,是“奉詔”從山西洪洞縣遷徙而來的。而沙河以西,由渡口鎮以西的太行山區地帶的民眾,多由明朝永樂年間的流民和赤貧之民組成。其中,渡口鎮王瑙村的先祖明確為明時押送皇綱途中遭土匪哄搶,無法交差,便帶著一干兵眾和家人落草于此,筑城堡為防兵寇,儼然一座軍事設施,至今為當地一大奇觀和獨具特色的古村落。 除此之外的村子,大抵是貧民和流民所建造的。一如我們村子。爺爺說,我們這一脈楊家的先祖,起初只有弟兄三人,從山西洪洞,一路流徙。翻過摩天嶺,亡命向東,至今武安市和沙河市交界的西部山區,見此地太陽充足,草木葳蕤,土質尚好——古老的中國,土地肯定是人們選擇建村立宅,以為百年大計的首選。于是乎,這兄弟三人,便在尚無他人居住的一道山坳里伐木為棚,采石建屋,而后又不斷地在河溝邊、平坦處開墾田地,如此數年之后,從前狐貍和黃鼠狼、蝎子蚰蜒、野兔野雞橫行的野地,便被一縷縷人間煙火所籠罩和替代。 如我們村。 “大爺爺名諱楊天嘯,二爺爺楊懷玉,三爺爺……”這是爺爺告訴我的,而三祖爺爺的名諱,爺爺卻想不起來了。那時候,我躺在他的身邊,腦子里一直映現著這樣一幅模糊的景象:三個男人,或許還有一到兩個女人,也或許帶著幾個十來歲的男孩女孩。衣衫襤褸的他們,先是在黃土彌漫的道路上蓬頭垢面,步履渙散。男人們胡子拉碴,目光堅定而又充滿了悲傷與迷茫,女人和孩子們則皮包骨頭,拄著拐杖還在打擺子。一陣風刮過來,他們當中沒人背身躲避,甚至張開嘴巴,希望那些細膩的灰塵能夠盡入口中,用以充饑。這種悲慘的遭遇,在王朝歷史上屢屢出現。農耕時代的人,衣食不僅是維持生命、保持尊嚴的保障,且還是許多人畢生為之辛苦的唯一目標。 斯時,可能是夏天,蹣跚到摩天嶺腳下,即現在山西左權縣拐兒鎮大南莊村和水泉村的時候,饑餓使得他們感到絕望,人生的一切都變得慘淡。他們不止一次地承受死亡的襲擊,也不止一次地猶豫。人在*艱難的時候,選擇死亡素來是一種常用的、一了百了的極致手段。可是,怎么能如此輕易地離開這個悲慘世界呢?再或者,有了孩子之后,所有的父母都會變得仁慈而堅強,也會使得絕境中的人們總是萌生奮力一搏,幻想奇跡或者明天會好一點的信念。 山上有草,盡管已經被很多人挖過了,草根也變得稀缺,樹皮亦然。可山上總是可以找到可以抵抗饑餓的吃食,如觀音土,別人啃剩下的榆樹皮、洋槐樹葉子等。這一夜,他們在茅草窩里度過了又一個晚上。天幕浩蕩,群星畢集,與之相對的人間,卻是如此的荒寒與悲涼。第二天繼續行路。他們此行的目的,肯定是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土地不需要太多,能夠安身立命,繁衍生存就行了。行至河北沙河市西部山頂,放眼望去,山川蒼茫無盡,向東逶迤。斯時,這里已經有人落戶,也都是和他們一樣的人家。弟兄三個商議了一番,便在另一處山坳尋到了一塊地方,作為自己的新家。 在荒野建村,并不像加入某個村子那么簡便,不僅要滿足現實的要求,還得為子孫后代考慮。我們村所在的地方,為一小山坳,向上有幾處平坦之地,至頂部,有一斷崖朝北的方向,靠村子處,則為陡坡,一直向下,直通村莊。兩邊都有山嶺,其中還有兩個更小的山嶺,下面是河溝,水流不斷,對面是從后山綿延奔縱而來的小山包,其低處,土質松軟且肥厚,自然條件是可以滿足的。別說三家人,再有百十來人家也可以滿足。于是乎,人身一落便成了村莊。 創業總是艱難的,好在,周邊有比他們更早來這里扎根的人家,借個家具之類的,也比較容易,天長日久,相互間也熟悉了起來,起房蓋屋的時候,也都相互幫忙。互助是人類在生存路上*符合人性的法則,也是人之所以群居的優勢所在。如此幾年后,我們的村莊逐漸成型,并與周邊同類的村莊形成了相互依傍的關系。兒女大了,婚配開始,由此開始的新一輪繁衍,在南太行壯觀而又不動聲色。再后來,老人老了、死了,找了一塊地方作為墳地,一代代的人生下來,又一個個地死去。天長日久,村莊與墳塋遙遙相望,互不干涉,但又血肉相連,魂魄相牽。每年的春節、元宵節、中秋節、十月初一,活著的人在地面的村莊享受各種吃食,以及吃得飽穿得暖帶來的快樂,死去的人也會收到子孫后代為他們燒去的紙錢、衣服和酒水干果等。 這也是一種合作,或者說“血緣上的合作”,人之所以不斷繁衍,其*重要的是為自己“留個后”,這是中國人的共識,也是數千年來,人類之所以綿延不絕,我們的傳統文化一脈相承且能夠感染其他習俗人們的根本原因。 所謂的文化,人才是*根本的載體。與之相對的則是,人群的矛盾。在一起久了,肯定會有矛盾,而農民之間*根本的矛盾,無非是土地以及村莊資源的分配,不公源于權利的專享,資源的匱乏也一再激發人們將之據為己有的野心和雄心。 任何一個村莊都是一個嚴絲合縫的社會,完整且充滿了各種性質和功能。尤其是當血緣越來越淡,*初的三個親兄弟的子嗣,再過五代之后,原來一個蔓子上的瓜,也開始形態各異,各懷心態。由此帶來的矛盾和斗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但我們的村莊至今保持了一個很好的傳統,如遇到紅白事,不論誰家,村人都要去幫忙。盡管,這種幫忙之中,摻雜了相互利用的因素。就拿“白事”來說,無論是哪一家,兄弟姐妹再多,也不可能獨立地完成從收殮到安葬的全過程,必須有人施以援手。而在這件事上,外嫁的姐妹及其家人是不可以參與進來的。這種約定俗成的規矩,在很大程度上,先祖可能就是為了用來保障子孫們在大事上齊心協力,不相互撂挑子、看熱鬧——而特別制定的。
南太行紀事 作者簡介
楊獻平,詩人,作家。《四川文學》副主編。 代表作:《匈奴帝國》《生死故鄉》《自然村列記》等。 曾獲冰心散文獎,三毛散文獎,全軍文藝優秀作品獎,在場散文獎,四川文學獎等。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朝聞道
- >
山海經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我與地壇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巴金-再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