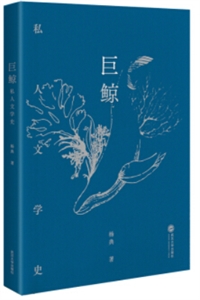-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307219533
- 條形碼:9787307219533 ; 978-7-307-21953-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本書特色
u 一掃傳統(tǒng)書評厚重之面貌,沉悶之氣象,以點(diǎn)代面,以小見大,以局部還原全貌,以奇巧代替中庸
u 參加一場私人訂制的文學(xué)盛宴,進(jìn)行一次另辟蹊徑的書山冒險,品讀數(shù)十封寫給文學(xué)的曼妙情書,重返無數(shù)個值得珍藏的開卷瞬間······
u 從《世說》到《吳宓日記》,從《怪談》到《□666》,從夏目漱石到凡爾納······實(shí)在難以想象,在薄薄一冊中,竟能體會到千奇百怪、各具魅力的文學(xué)人生
u 正典有正典的好處,野史有野史的精彩;學(xué)院派有學(xué)院派的嚴(yán)謹(jǐn),野路子有野路子的灑脫——全新的視角,獨(dú)特的選擇,造就一部精巧奇妙的文學(xué)評論集
u 將小說筆法融入隨筆創(chuàng)作之中,將古典傳統(tǒng)帶入現(xiàn)代書評體系,于漫漫文學(xué)史長河只取一瓢,經(jīng)多年釀造,終有所獲,給讀者以絕妙的微醺時刻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內(nèi)容簡介
本書是作家楊典若干年來積累的一些讀書隨筆、寫作觀念或偶然記下的書話之集錦。作者不僅用極具個性的語言對一些經(jīng)典作品進(jìn)行了解讀, 同時還將自己對于人生, 對于寫作的思索融入其中, *終提出了獨(dú)到的觀點(diǎn)與見解。這些文章并非體系化或理論化的書評, 而是一系列匠心獨(dú)運(yùn)的小品文 ; 作者在閱讀過程中, 通過對相關(guān)歷史的考證、查閱, 像盲人摸象一樣從局部去探索文學(xué)史, 將所獲所感化為文字, 充分反映了作者龐雜的閱讀興趣與深厚的閱讀積淀 ; 因此, 本作也可以說是一個人閱讀的精神史, 故稱為“私人文學(xué)史”。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前言
序
楊典/文
古人常言讀書不求甚解,卻在讀書時又大多講究分類或譜系,如清儒錢大昕之“剛?cè)兆x經(jīng),柔日讀史”云云。但我讀書真的沒有任何章法,從來就是亂讀。亂讀的習(xí)慣,是 □0 世紀(jì) 80 年代養(yǎng)成的,因那時家里空間窄,書架也少,所有書便全堆在一起,看見哪本饒有興趣,就抽哪本出來讀。一本沒讀完,又去讀另一本。常常是很多書同時在讀,有些能讀完,有些則半途而廢,不了了之。后來屋子擴(kuò)大了,書碼放得整齊一些,但這種惡習(xí)卻改不了了。大約因我不是一個喜歡系統(tǒng)化的人,故讀書方式也是野蠻的。
據(jù)說,讀書也并不見得一定要有秩序不可。如法朗士所言,讀書是“靈魂的壯游”。既是壯游,必是隨處亂走、隨遇而安,才更有冒險、驚喜與意外之感吧。我記得林語堂先生寫過一篇《讀書的藝術(shù)》,大約是說讀書可以很亂,找到原文,抄一段云:“或在暮春之夕,與你們的愛人,攜手同行,共到野外讀《離騷經(jīng)》;或在風(fēng)雪之夜,靠爐圍坐,佳茗一壺,淡巴菰一盒,哲學(xué)、經(jīng)濟(jì)、詩文、史籍十?dāng)?shù)本狼藉橫陳于沙發(fā)之上,然后隨意所之,取而讀之,這才得了讀書的興味。”林語堂還在《我的圖書室》一文中,說到過去的公共大學(xué)圖書館,是按照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進(jìn)行圖書分類。這固然好,但對一個普通學(xué)者的斗室而言則不可能。那么如何插架呢?他的辦法是“使書籍任其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諸如床上、沙發(fā)上、餐廳里、食器櫥中、廁所架上等,總之到處都是書。正如林語堂所謂“書籍絕對不應(yīng)分類。把書籍分類是一種科學(xué),但不去分類是一種藝術(shù)”。
我讀書的習(xí)慣倒沒那么凌亂,不過過去因地方窄,書太多,只好擠在一起,故而不知不覺也就按照“藝術(shù)”的方式去讀了。
讀書的根本是為了明理、思索以及更好地表達(dá)與認(rèn)識(即便完全不表達(dá),沉默無言,也是一種表達(dá)與認(rèn)識的形式),故讀書之癮若真成了惡習(xí),便會升級,變成寫書。寫書之癮再升級,便又會變成希望出版,拿給別人去看。哪怕是寫得并不好的書、壞書、怪書、無意義之書或惡德之書,也會期望別人與自己能有一些同感。
惡、怪與壞,到底值不值得出版呢?這其實(shí)是個很古老的問題。
如在 17 世紀(jì),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就說過:“德與惡本是一體, 消除其中之一, 便會把另一個也一起消除了。”——他當(dāng)年寫下這本書本是為了反對英國政府壓制出版和教權(quán)制度,但其書之影響卻直接延續(xù)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米拉波寫《論出版自由:模仿英國人彌爾頓》,以及 1905 年的俄國革命。彌爾頓之言當(dāng)初的意思是,一本書(或一切言說的自由),即便完全是“惡”的,也應(yīng)該允許出版。因唯有如此,才能使人提前作出判斷。但這個數(shù)百年前反教權(quán)式的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愿望,至今似乎也未能在世界范圍內(nèi)實(shí)現(xiàn),以至于當(dāng)惡(譬如戰(zhàn)爭、強(qiáng)權(quán)、欺騙或瘟疫)出現(xiàn)時,人們?nèi)匀徊⒉荒墚?dāng)即覺察。
待覺察時,惡已變成現(xiàn)實(shí)。也許在彌爾頓的觀念里,人若喪失一切書籍、文字和言說(無論文史哲還是科學(xué)與神學(xué))的自由,便都是一種“失樂園”。惡魔撒旦(作為極端美的墮落天使)即用自己生成之語言自由,去反抗已被世俗偶像崇拜化的天庭;而人若能獲得出版與言論自由,則是一種“復(fù)樂園”,正如□□對惡魔的幾次“拒絕”(這也必須通過反對的語言才能做到)。何為彌爾頓在□□哲學(xué)與史詩意義上的善惡樹、古蛇、性、原罪與蘋果?歸根結(jié)底,就是語言的自由。沒有語言,任何有效的思想都不會誕生,無論善惡。語言對社會現(xiàn)實(shí)的預(yù)示和批判,自古就是所有文明的先鋒,以“六經(jīng)”為思想源頭的中國應(yīng)該也不例外。可能在造物主眼里,各種語言都是惡(正如“巴別塔”即語言“變亂之塔”)的發(fā)展、演變和升級,尤其是文學(xué)與哲學(xué)。
因任何雄辯或詭辯的語言,都帶有反抗□□的特性或毀滅性。太平無事時,善人就應(yīng)該是聽話的,惡人才會唱反調(diào)。可一旦災(zāi)難發(fā)生,善人們的沉默卻會成為共謀與罪過。故善是平庸之惡,惡則是創(chuàng)造之善。這真是一件全球共同的悖論。恰如羅蘭·巴特所云:“語言即惡魔,此外并無別的惡魔。”這里的惡魔,主要是指人在反抗時對理性、自由、判斷、法治、文學(xué)、藝術(shù)、愛、科學(xué)與智慧等的綜合追求。因所有精神都必須通過書和語言才能傳遞。
書——或語言之惡,并非社會行為上的惡。作家作為人,必須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道德和公德,這是沒問題的。但歷代很多偉大的文史哲作品、改變過歷史進(jìn)程的圖書、了不起的思緒、發(fā)明與想象,往往又是反道德綁架或反世俗的。因文學(xué)與哲學(xué)同時還是人性思維的拓展,而不僅僅是“道德文章”,也就是說,作家有義務(wù)對社會環(huán)境、現(xiàn)實(shí)問題、災(zāi)難、惡或不公發(fā)表看法,表達(dá)反對,但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卻又不能完全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文學(xué)可以反映現(xiàn)實(shí),但這只是它眾多的功能之一。因文學(xué)與哲學(xué)、神學(xué)、科學(xué)、數(shù)學(xué)或音樂等一樣,同時還是人類形而上思維、極端想象力、存在與否定存在,以及絕對自由精神等的□高表現(xiàn)形式。讀書越雜亂,這種感覺就越清晰。
那么,究竟何為精神自由?這恐怕是一種有限的無限性吧。
比如當(dāng)災(zāi)難發(fā)生時,可能再焦慮的思辨、哲學(xué)或再偉大的書,此刻也只能如陷入盲區(qū)里的猛獸一般無奈。知識與書到底有什么用?自由在哪里?可能問題并不在于有用無用,只在于有還是無。人在本質(zhì)上,正如張申府先生在《所思》中言“兩人之間無自由”,何況全社會或全人類?在讀書與寫作上,我們倒是可以不再需要用別爾嘉耶夫或哈耶克式的觀念來談了。因讀書與寫作的自由主義,若不能完全體現(xiàn),其□低限度也應(yīng)該是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前傳);若能夠完全體現(xiàn),則其□高封頂是虛無主義。如何在合理秩序中重建愛與哲學(xué),或無限接近完全體現(xiàn)的一種自由?這相當(dāng)于如何兼容個人欲求、哲學(xué)與社會法制之間的磁場,其大歷史文化的中心,是個不斷將我們有限的知識吸入悖論的黑色旋渦,東西背反,過猶不及。
讀書與寫作自由,并不等同于社科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尤其是文學(xué)的自由。文學(xué)的自由是對某種無限性和反邏輯思維的挑戰(zhàn)與實(shí)驗(yàn),而不是語言實(shí)用主義的自由。
正如我們都知道什么是文學(xué)的社會責(zé)任(就像中國古代的士與文章的關(guān)系),可對“偉大的文學(xué)”,又不能僅僅以時代責(zé)任和道義之心來做窠臼。文學(xué)有標(biāo)準(zhǔn)嗎?古今中外與現(xiàn)實(shí)、時事、災(zāi)難或不公平悲劇無關(guān)的偉大文學(xué)作品,如戲劇、詩與散文,可以說與其他的偉大文學(xué)作品一樣多,甚至要多無數(shù)倍。誰規(guī)定“偉大的文學(xué)”必須寫苦難?即便在文學(xué)革命時,其也并不一定是革命文學(xué)那樣臉譜化。如王維與大部分唐宋詩人們的詩、《世說新語》里的名士之語、陶宗儀的筆記、張愛玲的小說、《西游記》、六朝志怪、明清傳奇、《金瓶梅》《紅樓夢》或《牡丹亭》;如薩德、塞萬提斯、凡爾納、納博科夫、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博爾赫斯、里爾克、特拉克爾、蘭波、卡爾維諾、艾柯、帕維奇等人的作品,以及《枕草子》《源氏物語》,還有一休、良寬與夏目漱石的漢詩或谷崎潤一郎、太宰治、川端康成等的書……
他們都曾面對戰(zhàn)爭或現(xiàn)實(shí)苦難,很多甚至曾親身體驗(yàn),但他們寫了多少時事,寫了什么現(xiàn)實(shí)?似乎也沒有多少。他們只關(guān)注人的內(nèi)心、幻想、愛情與人性本身的奇異與沉淪、美與性、怪癖與尊嚴(yán),有時甚至就寫閑情、荒謬與頹廢,寫那無所不在的“無”,難道不行嗎?難道他們寫的就不是“偉大的文學(xué)”?偉大的文學(xué)主要建立在偉大的虛構(gòu)上,而不僅僅只有“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才算得上是偉大的文學(xué)。真正能反映或鏡鑒人類永恒價值與矛盾的文學(xué),大多數(shù)時候,正是那些亙古不變的奇思異想與非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是“壯游”而非“視察”。尤其在進(jìn)入現(xiàn)代性后的世界,戰(zhàn)爭的形式也在不斷變化,難道不許偉大文學(xué)的形式也發(fā)生一些變化嗎?語言三十年會有一個流變,文學(xué)更是嬗變的。一切文學(xué)□□□,也都是一種文學(xué)短見,不適合于偉大的文學(xué),只適合于沒有偉大文學(xué)天賦的人。文學(xué)的社會角色的確有起伏,但不會消失,文學(xué)并不來自 19 世紀(jì)的西方,而是從甲骨文或希伯來文時代就開始了它的責(zé)任、消遣與力量,也必將與未來人類與人文精神共存亡。看上去天馬行空的《莊子》、《神曲》、《天方夜譚》、《封神演義》、魚玄機(jī)或巴塔耶的詩是偉大的文學(xué),當(dāng)然,像奧威爾、加繆、巴別爾、赫胥黎、海明威或吳宓等人那樣直擊現(xiàn)實(shí)的作品,也是偉大的文學(xué)。文學(xué)只有好與差,是與不是,但沒有任何衡量標(biāo)準(zhǔn)。沒有任何一種文學(xué)―哪怕它再偉大(或再具有語言之惡)——能有資格變成其他文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設(shè)定“文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本身就是反文學(xué)的。本書就是前些年積累一些讀書隨筆、寫作觀念或偶然記下的書話之集錦,是我個人對書齋生涯的零星瑣憶。讀者隨意翻到哪一頁,都可直接瀏覽;任取其一,皆可獨(dú)立成篇,如艾柯的《密涅瓦火柴盒》,也正如林語堂所言的那種“藝術(shù)”或曰隨意吧。故我將抽屜中現(xiàn)存的、尚未在別的書中出版過的書話篇什,也全都盡量放在這本書里了,以便總攬記憶。
中國古人很重視歷史,但清代以前其實(shí)從無什么“文學(xué)史”。因在中國人看來,閱讀就像往事,有時會渙散,有時又銘心刻骨。一切書都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而書一旦創(chuàng)造出來,便又會完全變成獨(dú)立之物,并反哺于人,甚至還會倒過來去創(chuàng)造一個人,橫練一個人。一個人的讀書與寫作范圍,本身就構(gòu)成了那個人的文學(xué)史。比如很多早年讀過的書,我自己其實(shí)都忘了,但它們卻暗中對我有著潛移默化的可怕影響。甚至在血液里,在脾氣上,在對虛構(gòu)與敘述的癖好中,仍秘密操縱著我今天的生活與言行。這種文學(xué)史□□于任何學(xué)者們編撰的那種羅列名著與名家的文學(xué)史,是每個讀書人的根本精神史。很多作家都寫過這種讀書式“私人文學(xué)史”,如巴塔耶《文學(xué)與惡》、布魯姆《西方正典》、卡爾維諾《為何讀經(jīng)典》、薩瑟蘭《耶魯文學(xué)小歷史》或鄭振鐸先生《西諦書話》等,讀書本身就是私事,這并不稀罕。其實(shí)在生活中,就算是真歷史,也并非是那些公開的編年史,而是以往發(fā)生過的全部細(xì)節(jié)、遺忘乃至誤解的大雜燴和每一個當(dāng)事人隱秘的情緒。歷史從無整體,每個人都在盲人摸象,看見的只是局部,表達(dá)的更是局部的局部,且都很渺小。文學(xué)亦如是。讀書與寫作亦如是。故我索性將一切我與書之間的糾葛、記憶、淡忘、議論與嗜好,將能夠出版的僥幸與某些不能被出版的遺憾等,包括我與書之間的相互否定或混淆之總和,皆一概統(tǒng)稱為“私人文學(xué)史”了事。
□0□0 年 3 月,北京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目錄
飛頭之國:幻想力缺席時代與小泉八云之《怪談》
輕野船與琴:關(guān)于《倭漢三才圖會》中所見之琴
瞎驢神髓:談一休色情詩、白骨禪與盲女森
重復(fù):在葛飾北齋山下讀詩
老魂驚:關(guān)于夏目漱石《木屑錄》《漱石詩集》之短札
世間有一面笨蛋的墻:從徒步北齊長城想到養(yǎng)老孟司『バカの壁』
制服與氣味:我鬼窟與少年刺客
全副武裝式和平寓言:續(xù)書傳統(tǒng)與道洛什·久爾吉《1985》中的自由主義
第三約的詩學(xué):吉皮烏斯《那一張張鮮活的面孔》中的俄羅斯思想
文學(xué)利維坦:波拉尼奧《□666》的“巨鯨”結(jié)構(gòu)主義
巨著的鬼魂:《日瓦戈醫(yī)生》之電影式微與小說追遠(yuǎn)
圖譜、激情與泛薩德連鎖記憶:關(guān)于布林德爾《新音樂:1945 年以來的先鋒派》之短札
惜物華:關(guān)于沈起予譯本盧梭之《懺悔錄》隨記
世說門下走狗(一):略談角田簡《近世叢語》及續(xù)與背景
世說門下走狗(二):從王世貞《世說》箋本與補(bǔ)本看“語林”之影響
仿佛若有光:讀梁啟超《陶淵明》小思
元人的百科全書:夏日讀《說郛》偶得
丑齋孤本與未死之鬼:略談元人《錄鬼簿》之讀法
病詩無言病:清人田雯《病愈早起成詩》與“廋辭”傳統(tǒng)
猛志鏡像:從巴塔耶《內(nèi)在體驗(yàn)》到《金瓶梅》中絕嗣之刑苦
氣球上的清朝:讀插圖本儒勒·凡爾納《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
喻血輪辭海:談民國喻血輪《綺情樓雜記》之大陸首版
與身俱存亡:袁克文舊作及《寒云藏書題跋輯釋》之短札
后野史時代的怪癖:偶讀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
革命式絕望:文言《懷舊》兼紀(jì)念魯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盲目輿情萬古同:因見郭鼎堂先生新版《李白與杜甫》而想到的話
細(xì)膩的火:讀《吳宓日記》兼論一點(diǎn)寬容
豮豕之牙:夏日讀《養(yǎng)豬印譜》而想起“國之大畜”
愛情仇恨詩人:讀《三詩人書簡》及藍(lán)橋尾生之隱喻
書信時代:夏夜讀《穆佐書簡》偶記
再見,哀歌:對早年閱讀之火的一次懷疑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相關(guān)資料
這才能和天性是攔不住的,一代代還是會出人。
——陳丹青
“楊典是當(dāng)代少有的通才,知識淵博。他目前只被小眾認(rèn)可,如果能被大眾認(rèn)可,這是時代的一種幸事。”
——余世存
“這個愛書人向我們展現(xiàn)了深厚的文脈家底和逼人的絕對才氣……”
——詩人子午
“楊典的書是我內(nèi)心隱秘的珍寶,但更是新一代文學(xué)的閃光。”
——詩人柏樺
“楊典是具有相當(dāng)之素養(yǎng)的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之文人,更是一位鐫刻有八十年代氣質(zhì)的思想者。”
——北大教授陳均
“楊典從不謙虛客套,但也不狂妄自大。他對自己才情的自信,當(dāng)然讓某些人看了刺眼。老實(shí)說,他的確傲了些;不過,他說的,都是些真話。我喜歡他這樣稍稍讓人刺眼的自負(fù)。”
——臺灣學(xué)者薛仁明
巨鯨:私人文學(xué)史 作者簡介
“可我這個人/除了詩/鬼、古籍和酒/什么也不信。”——楊典
作家、古琴家、畫家、編劇。主要代表作有隨筆集《孤絕花:舊版書評肆拾捌》《隨身卷子》《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與新浮生六記》《狂禪:“無門關(guān)”鏡詮》,小說集《鵝籠記》《鬼斧集》,琴論《琴殉》《琴殉續(xù)編:彈琴、吟詩與種菜》,詩集《花與反骨》《枯山水》等。
- >
月亮與六便士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回憶愛瑪儂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shí)旅程
- >
推拿
- >
大紅狗在馬戲團(tuán)-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隨園食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