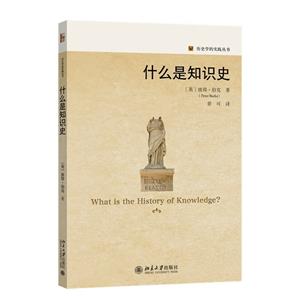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什么是知識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38735
- 條形碼:9787301338735 ; 978-7-301-33873-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什么是知識史 本書特色
本書由當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伯克撰寫,屬于史學史和史學理論方面的大家小書,也是全球范圍內專門論述知識史的*好入門書之一。伯克以簡潔生動的語言和旁征博引的方式,依次介紹了知識的類型、知識史的多個基本概念,詳細分析了知識獲取、分析、傳播和應用的過程,*后討論了知識史發展的問題以及前景。全書內容豐富,視野寬廣,論點勁道,思想深刻,極具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適合對知識史、科學史、史學史感興趣的國內高校師生和大眾讀者。
什么是知識史 內容簡介
知識的歷史是什么?這本引人入勝的小書揭示了知識史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獨特之處,以及它與科學史、思想史、知識社會學和文化史的區別。有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首先從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區(印度、東亞、歐洲、美洲和伊斯蘭世界)廣泛擷取范例,討論該領域學者*關注的核心概念,繼而梳理了"信息"轉變為"知識"的"加工"過程,*后指出了當前該學科面臨的若干重大問題,并嘗試為之提供解決的方案。本書對于所有學習歷史和人文學科的學生,以及感興趣的普通讀者來說,都是推薦閱讀的。
什么是知識史 目錄
1. 學術史
2. 什么是知識?
3. 復數的知識
4. 歷史學和它的鄰居們
第二章 基本概念
1. 權威和壟斷(Authorities and monopolies)
2. 好奇心(Curiosity)
3. 學科(Disciplines)
4. 創新(Innovation)
5. 知識分子與博學家(Intellectuals and polymaths)
6. 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7. 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8. 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
9. 知識的秩序(Orders of knowledge)
10. 實踐(Practices)
11. 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
12. 無知機制(Regimes of ignorance)
13. 情境中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
14. 思想諸方式(Styles of thought)
15. 被壓制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
16. 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
17. 知識的工具(Tools of knowledge)
18. 傳統(Traditions)
19. 翻譯知識(Translating knowledges)
第三章 過程分析
1. 客觀性的嘗試
2. 四階段
(1) 收集知識
(2) 分析知識
(3) 傳播知識
(4) 應用知識
第四章 問題與前景
1. 問題
(1) 內部與外部之爭
(2) 連續性與變革之爭
(3) 時代誤植
(4) 相對主義
(5) 勝利主義
(6) 建構主義
(7) 個體與體系
(8) 性別
2. 前景
進一步閱讀書目
什么是知識史 節選
著眼當下,如果說“知識史”還不存在的話,那么就很有必要將它發明出來,尤其是為了將*近的“數字化革命”放在一個長時段變革的視野中加以定位。在漫長的過去的某些時間點上,人類已經歷過知識體系的重大變革,這都有賴于新技術的出現:比如書寫行為的*初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或是其他地方;又比如印刷術的發明,尤其是東亞的雕版印刷和西方的活字印刷;還有當代,在我們有生之年的記憶里,計算機的出現,尤其是個人電腦,以及互聯網的興起。類似這樣的變革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或好或壞。就像我們對互聯網這個例子都很有感受,這種新式的交流媒介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希望,也提出了挑戰。在我們因身處知識體系的重建期而尋找方向時,幸虧有了全球化和新技術,我們有充分條件去回溯歷史。 知識史其實也是從其他類的歷史研究中逐步發展出來的,尤其是兩類。**是書籍史,在過去幾十年里,書籍史研究的重心從對書籍買賣的經濟史研究轉變為對閱讀的社會史研究和對信息傳播的文化史研究。第二是科學史,而科學史之所以轉向更為廣闊的知識史,則是來源于三個挑戰。
**個挑戰是,人們開始意識到,現代意義上的“科學”(science)這個術語其實是一個 19 世紀的概念,所以用這個概念去研究更早時代的知識創制行為就會導致一種“時代誤植”,而后者是歷史學家*忌諱的。第二個挑戰則來自學術界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包括那些手工藝、醫療術等實踐性的知識。第三個同時也是*關鍵的挑戰是“全球史”的興起,人們需要去認識和討論那些非西方文化的智識成就。這些成就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西方的“科學” 范型,但它們毫無疑問是對知識的貢獻。 即使是在某個特定的文化之內,也會有不同種類的知識:理論的和實踐的、抽象的和具體的、顯性的和隱性的、學術化的和大眾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地方性的和普遍的,知道“如何做某事”和知道“某事是什么”也有不同。 不同種類的知識之間的沖突經常會出現,比如,15 世紀初當意大利米蘭大教堂開始修建時,當地熟練的石匠們和主管工程的法國設計師之間就發生了爭論,爭論點實際上就是實踐知識(ars)和理論知識(scientia)——尤其是幾何學,究竟哪個更重要。在 17 世紀,職業醫生們熱衷于嘲諷那些助產士和民間醫士們的實踐知識。而在18 世紀晚期,有位法國的磨坊主出版了一本小書,批評那些“博士們”(也就是 savants),整日傲慢自大地想指點磨坊工和面包師們怎么做他們的本行。 正如今日的記憶研究已經擴展到了它互補的對立面——對“遺忘” 的研究,知識研究也正在試圖去涵蓋另一面——對“無知”的研究,這包括那些失落的或被有意拒斥的知識(本書第二章會討論)。無需多言,本書作者也深受“無知”之苦。我對于“知識”的認知只能說是極為有限。相比于對西方的了解,我對西方以外世界的了解要薄弱許多;相比對學院知識的了解,我對大學以外知識的掌握很是可憐;當然,相比對人文學科,我對自然科學的了解只能說極少。盡管有這些局限,本書還是試圖將知識歷史的多樣性展示出來。我們將從關鍵概念開始,接著考察信息如何被轉化為知識——進而廣為傳播、被各種意圖所用——的整個過程,*后我們討論這個領域里時常會出現的問題,以及將來的前景。 近期,知識研究進展迅速,知識史研究也在蓬勃發展,這導致新的概念不斷出現。實際上,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整套新語言,甚至可以說是“行話”,所以編制術語表一類的東西就變得很有必要。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只是這個方向工作的**步,我們會討論一些術語,這將會有助于我們閱讀和書寫知識史,甚至是對它進行反思。由于是術語表,我們將按照單詞首字母的順序展開敘述。 對于好奇心,中世紀的哲人們一直在亞里士多德的正面看法和奧古斯丁的負面看法之間游移。直到文藝復興時代,亞里士多德式的看法占據上風,好奇心迎來了自己的“名譽恢復”,培根提出了“認知是人類基本權利”的說法。盡管如此,浮士德博士向魔鬼出賣自己靈魂以換取知識(及其他東西)的故事,提醒我們對好奇心的負面認識依然如影隨形。可能遲至啟蒙運動時代,正面看法才開始真正成為主流,康德提出“要敢于認識”(sapere aude,引自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箴言,成為標志性的象征。 知識的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即使這種變化的速率并不快。當印刷書興起的時候,歐洲大學對此的反應是逐步漸進的,并非一日變天,而時至今日,課堂講授仍然是傳播學術知識的主要方式。在北美,各種研究機構之間的勢力平衡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 19 世紀末期,大學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變得“絕對重要”,但一個世紀之后,卻在逐漸衰落,因為各種公立或私立的研究所或“智庫”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和地域,信息的秩序可能是由占主流地位的傳播方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或是數字的,當一種新的媒介產生時,它并不是直接替代舊的,而是與先前所有舊的媒介共存一段時間。媒介之間的競爭,*終是以勞動分工的方式穩定下來,我們舉近代早期歐洲的手寫與印刷為例,當印刷出現后,手寫文書依然重要,不僅是為了私下的秘密交流,很多貴族的詩作和論著也同樣以手寫方式流傳,因為他們鄙視印刷作為商業活動所帶的銅臭味。 知識實踐同樣還包括獲取知識、將知識歸類、驗證知識這樣一些多少比較正式的環節,比如說解剖尸體、用望遠鏡觀察星象、進行實驗操作等等。其中有些帶有特定學科的獨特性(比如醫學當中的診斷),有些則是很多門學科的共同問題(比如比較)。然而,還有其他(比如說記錄)屬于更加“非正式”的實踐,但同樣常見。這每一種實踐形式都有自己的歷史,也就是說,它們在長時段當中都在變化。科學方法經常——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從這些“非正式的”日常實踐當中發展出來的,這是我們應該將科學史研究置于更廣大的知識史中來考察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為了避免種族中心主義和時代誤植的謬誤。 所謂的接觸也包括征服,在殖民的情境下,不同知識盡管共存,但彼此間并不平等。征服者的知識占據統治地位,而地方性知識就成為“被壓制的”。這些被壓制的知識往往會被遺忘,或者至少不被統治集團的人們所看重,就像歷史上西方的學者在書寫或者描繪非西方世界時,很少會談他們從本地人那里學到了什么。 英國對印度的知識生產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共同過程,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對話的結果,“盡管各方之間并沒有被等量觀之”。在此我們可以引入“文化協商”(cultural negotiation)的概念來思考這種情況。“協商”可能是一個比較難把握的詞匯,但在此可以指一種半有意識的、對另一個人或團體觀念的反應,一種對觀念部分性的采納和吸收。在這種意義上,“協商”應該和另一種主動有意識的行為區分開來,比如傳教士們和印度本土學者都曾有意識地將西方科學和印度的印度教、穆斯林傳統調和起來。 人們經常討論知識的傳播、轉變和擴散,過去的學者們常常認為,在這傳播過程中,從一處到另一處,從某人到他人,知識或多或少保持不變。今日學界的看法則大相徑庭,占據主流的觀點是相反的,即傳播的起點和終點之間在很多方面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知識傳播意味著一種調解。某種知識為了達成旅行,必須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但在一種語言中核心的概念,并不一定在另一語言里具備。例如,當基督教傳教士到了中國,嘗試將基督教的“上帝” 概念翻譯成中文時,就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因此“協商”就變得很有必要。確實,人們可以說,翻譯就是一種協商,同時,協商也是一種翻譯。 從獲取知識到使用知識有很長的過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四個主要階段:收集、分析、傳播和應用。當然,各階段還可再細分,后文將述及。無需多言,這四個范疇本身也不是全然固定的,相互間會產生流動。舉例而言,“觀察”不僅僅是一種理解事物的方法,觀察行動需要有“前理解”才能更有效。我們可以設想下,假如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英格蘭人來到了今日的倫敦,他很難理解所看到的大部分事物。 隨著各種需被貯藏的知識蜂擁而至,如何將它們安全妥帖地保存便成了問題,而檔案的出現成為一種解決之道。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公務員們經常在自己家中工作,其結果就是,他們把政府公文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使他們的繼任者很難取得。從高效行政的角度去看,這是種極大的不便利。1567 年,伊麗莎白女王給法院主事官寫信時就抱怨道:“我們整個法庭的記錄,居然都收藏于個人之手,這是非常不合適的。”因此,當時的政府紛紛仿效這方面居于先驅的羅馬教廷和威尼斯公國,開始建檔案館,設立看守和準予進入閱覽的規章。到了 19 世紀,檔案館逐步向公眾開放,而“檔案館員”也成為新興的職業。有時,對于政府希望銷毀的文件,檔案館員則會竭盡所能將其保存下來,比如在 1851 年英國的人口普查后,英國公共記錄辦公室(Engl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任主任帕爾格雷夫(Francis Palgrave)就是如此。然而,只有到了近期,歷史學家們——尤其是知識史的研究者們才把檔案本身看作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而不是僅將它用作研究其他歷史的原始材料而已,有關檔案研究的論著到*近才開始多見。 在*近幾十年,百科全書開始轉到互聯網線上。《大英百科全書》在線版的規模并不比“維基百科”(Wikipedia,2001 年上線)要小,這也昭示著人們搜索信息方式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讓某位學者感嘆,我們現今生活在“搜索引擎社會”。互聯網在線搜索,和在圖書館里檢索一樣,都需要特定的技巧。我們所說的“在線搜索能力” 已經逐漸取代了舊時代的閱讀能力。一方面這代表著我們的很多問題都能得到豐富答案,另一方面,人們也要認識到,搜索引擎也存在著某種內置的偏差,這往往是商業廣告宣傳帶來的。 人類對書寫文本的信任,也經歷了很長的過程。12 世紀早期,在英王亨利一世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次爭論中,國王的支持者們把羅馬教宗寫給大主教表示支持的一封信看成“只是一塊羊皮上邊畫著些墨水而已”,根本不能與“三位主教的證言”相提并論。同樣地,11 世紀的一位穆斯林旅行家比魯尼(al-Beruni)在談到他不寫書的原因時,引用了蘇格拉底的話,“我不想把知識從活生生的人類心靈轉移到死沉沉的羊皮之上”。盡管如此,自 17 世紀以后,口頭證詞在各種情境中的價值反而不斷降低。社會中上階層的人會把口頭證詞與底層民眾的無知聯系在一起,18 世紀學者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在《美洲史》中就表達了這種不信任態度:“這些對過去事情的記憶并不能保持長久,它們也無法被納入忠實可靠的傳統。”僅僅在 19 世紀的民俗學研究者或 20 世紀的口述史學者那里,在口頭材料被加以批判地研究的特定條件下,口頭傳統的價值才慢慢得到恢復。 不論歷史還是當下,所謂的“復興”當中,新的“敘事”相比舊的在很多關鍵方面都有所不同。對以往的歷史敘事來說,歷史學家們站在遙遠的距離外俯視那些事件,仿佛奧林匹斯山的眾神那般,與典型 19 世紀小說中的那些“全能敘事者”很接近。與之不同的是,新的“敘事”往往會展現多樣化的聲音和觀點,其模式有些類似于 1950 年的電影《羅生門》。這部著名的電影是日本導演黑澤明執導的,基于 20 世紀初期的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兩個短篇小說,描述的是對同一個謀殺事件的不同版本敘事。不論芥川或者黑澤明原來的意圖為何,“羅生門效應”這個詞現在被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廣為使用,指通過對故事的考察來重建講述者的態度和意義,也就是說,將不同敘述的沖突轉變為對這些沖突的敘述。 我認為可以把“文人共和國”的歷史一直延伸到當下,按照交流傳播模式的轉變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個階段就是從1500 年到 1800 年,這是一個由馬拉動的“共和國”,不論是書籍、信函還是學者本人,都需要搭乘馬拉動的交通工具在陸地上遠行,或者是乘船遠渡重洋。第二個階段從 1800 年到 1950 年,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蒸汽共和國”,蒸汽印刷機的出現使書籍的價格變得低廉,而召開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則因火車和蒸汽輪船變得普遍,學者們能夠更方便地交流訊息。第三個階段大概是從 1950 年到 1990 年,航空旅行快速發展,舒適度也大為提高,各種小型的、專門性的國際討論會得以蓬勃開展。而今日我們生活在第四個階段,也就是“數字共和國”。“文人共和國”永遠是虛擬的或者說想象的共同體,但是,傳播的不斷加速——通過電子郵件、在線會議、各種群體性的網上連線研究——使共和國的成員們相比以前更習慣于遠距離的互動,從而給“看不見的學院”這個古老的觀念注入了新的涵義。 獲取知識的權利長期以來就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對于那些創造知識、保存知識的機構(如大學、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而言。在歷史上,許多人都試圖擴大擁有此類權利人士的范圍。在五百年前,印刷術的發明為這種嘗試提供了很好的工具,然而,印刷術本身并無法增多知識擁有者的數量,其間還需要克服兩個主要的障礙:文盲和拉丁文。所以,當時社會掀起的文化運動,或者可以說“戰役”,目標主要有二,其一是普及識字率,其二是將知識用各國國語進行表述。 無論如何,人類對知識的占有并不這么容易。在過去和當下,構成阻礙的主要有三點因素。**點或許也是*不易被人察覺的,就是知識的專門化。就人類整體而言,我們所知的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但就個體而言,要把握人類知識的整體圖景變得越來越難。第二點,政治體制依然會對知識的共有產生威脅。其中消極的形式就是審查制度,而積極的形式就是有關知識的保密制度,盡管這些在極權國家較為常見,但其實各國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第三點則是一種“私人化”的潮流。知識的“所有權”這一觀念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發明,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各種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確實推動了知識私有化的進程。舉例而言,制藥公司正試圖把一些傳統的地方知識申請專利,比如印度人用姜黃殺菌的技術。 人們很自然會發問:對誰有用?為什么有用?不同的知識很顯然是由于不同的意圖而被應用。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學習古典修辭術在法律和政治實踐中是大有用處的。當時各帝國如果沒有對地形和相關資源的認知,幾乎很難生存下來。當然,戰爭中也要用到大量的地理知識。比如拿破侖的軍隊中就有大量地形學的專家,他們對奧地利、意大利、俄國等地都進行了調查和制圖。到了19 世紀,掌握主動的是普魯士人,1870 年至 1871 年普法戰爭中,按照一名地理學家的說法,“對勝利而言,地圖和武器一樣重要”。至于到 1990 年至 1991 年的海灣戰爭,美國軍隊開始配備了新的地理信息系統。
和戰場一樣,在商場上,獲知競爭對手的計劃和技術,同時又要保證自己的計劃和技術不被對手知曉,兩者同等重要。簡而言之,應用知識的過程也是控制的過程,我們在此再次引用福柯的著名論斷:“知識往往會引發權力的運作”。 無論如何,即使作為整體的人類在今天掌握的知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對于個體的人而言就未必如此。我們的記憶能力并沒有提高,我們也沒有比先祖花更長的時間學習,所以,就算我們知曉一些他們不了解的東西,反過來也一樣。既而,知識史的研究還必須關注無知、知識的障礙以及知識之間的爭斗。歷史上曾有很多被認為是知識的東西,*后被拋棄和拒斥,比如煉金術、顱相學等,這些同樣不能被忽視。 在知識史內部,我認為在未來幾十年里有三個取向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一是全球史的取向,二是社會取向,三是對更長時段的關注。
和整體上的歷史學一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全球轉向正在發生,它試圖超越對地球上某個特定部分的研究——比如印度或中國,它主要圍繞的問題不是西方知識的傳播或者殖民主義(這是較近的話題),而是相遇、碰撞、轉譯和雜化。近期有些研究聚焦的是“移動中的知識”——通常是長距離的移動。和知識史以往的變化一樣,這一次又是科學史家們引領風氣,當然,史學史的研究者們同樣不甘其后。相隔遙遠的不同文化間的比較,比如古希臘和古代中國,某種程度上也符合這一潮流。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個社會轉向,這其中就包括新的自下而上的知識史,比如說,相較于關注政府,它更關注被統治的人們如何利用信息,或者是以特定的方式選舉,或者是組織抗議,甚至發起革命。社會取向的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今日很常見的傾向,就是對日常生活知識更為關注,包括我們在第二章中討論過的默會知識,這一取向不僅關注諸如金屬制品之類的手工業,還包括外交、貿易、行業鑒定、管理、體育運動等各種領域。舉體育運動為例,有的人類學家研究拳擊和巴西戰舞(capoeira 卡波耶拉舞),而其田野工作就是接受相關運動的訓練,無疑這能給歷史學家帶來很多啟示。教練如何把默會型知識轉變成可供言傳的明晰知識,這樣一些問題或許在將來會成為學者新的關注。
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也許會看到更多學者從超長的時段來研究 “人性”,更多人試圖去回答“大歷史”的倡導者們提出的問題:“知識的收集和分享究竟是如何造成了長時段的變化,從而將人類的歷史與其他相近物種的歷史區分開來?”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曾經論述過一個綱要,比如他說過,人口越來越密集的定居點會帶來農耕的發展,進而導致“更頻繁的觀念交流”,如今的挑戰就在于,如何把這綱要填補得更為豐滿。一種應對挑戰的方式可以被稱為“認知的歷史”(cognitive history)。“認知的歷史”聽上去就像是“集體心態史”換了一個名字,但它關心的是一個比法國年鑒學派的“長時段”更為綿長的時間段,要用“千年”來衡量,而不是“世紀”。在這個方向上,歷史學家們要有所創見,就需要考古學家的幫助,這就是字面意義上的“知識的考古學”(不是福柯那個意義上的)。考古學家們一直以來就對重建史前時代的知識很感興趣,那是在書寫系統發明之前,研究者們利用的是物質遺存資料。他們當然關注那些轉折時刻,比如人們開始運用語言、開始繪畫或者雕刻、開始在精心制造的墓穴中埋葬死者遺體等。在他們試圖重建史前世界的知識和思維方式的過程中,考古學家們開始采取一種智識上的“減法”,也就是說,把晚近的知識“排除出去”。 歷史學家喜歡說的話是:關于未來只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它會和當前所有的預測都不一樣。盡管如此,無論知識史研究在未來幾十年里會產生哪些新潮流,我們這個“知識社會”里的人們對于知識史本身的興趣仍將不斷增大。
什么是知識史 作者簡介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國歷史學家,當代著名新文化史家。曾執教蘇塞克斯大學、劍橋大學,現為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及伊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研究員。著有《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制造路易十四》《知識社會史》《圖像證史》《什么是文化史》《近代早期歐洲的語言和共同體》等。
章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概念史、知識史等,著有《中國“人文主義”的概念史,1901—1932》,主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等書,出版譯著多種。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莉莉和章魚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山海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姑媽的寶刀
- >
我與地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