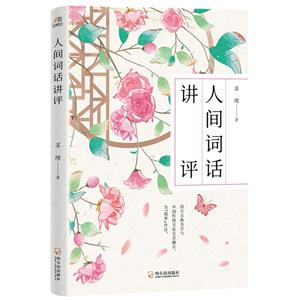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人間詞話講評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807537793
- 條形碼:9787807537793 ; 978-7-80753-779-3
- 裝幀:暫無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間詞話講評 內(nèi)容簡介
《人間詞話》是國學(xué)大師王國維的代表作,全書*重要的概念為“境界"二字。倚馬千言,縱橫開闔,皆從“境界”出發(fā)。《人間詞話講評》由知名作家蘇纓執(zhí)筆,可以說,他讀懂了王國維的心思,寫透了其詞話之精華。為了幫助讀者較為全面地了解這部經(jīng)典著作,本書收錄了許多王國維的經(jīng)典詞話,以幫助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和品讀《人間詞話講評》。此次出版,再次修訂,供讀者品讀欣賞。
人間詞話講評 目錄
一 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
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1
二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
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于理想故也。/12
三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立耳。/16
四 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yōu)美,一宏壯也。/26
五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guān)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xué)及美術(shù)中也,必遺其關(guān)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gòu)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gòu)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32
六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境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36
七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39
八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yōu)劣。“細雨魚兒出,微風(fēng)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fēng)蕭蕭”。“寶簾閑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43
九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 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 [ 月 ]、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fù)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49
十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fēng)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guān)千古登臨之口。后世惟范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57
十一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余謂:此四字惟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艷 [ 妙 ] 絕人”,差近之耳。/66
十二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弦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 /86
十三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fēng)愁起綠波間”,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91
人間詞話講評 節(jié)選
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人間詞話》才一開篇,便拋出了一個可謂全書*重要的概念:境界。但*大的麻煩也在這里,因為學(xué)者們每提出一個概念,總要給這個概念賦予定義,王國維卻一點都沒有解釋他所謂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等《人間詞話》成了經(jīng)典,“境界”一詞便被不斷地深挖廣證,結(jié)果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恐怕主要是王國維在學(xué)術(shù)史上的地位所致。在文藝理論研究上,《人間詞話》正處在新舊鼎革的交界線上,正是從近代學(xué)術(shù)邁向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一步,既有其現(xiàn)代性的一面,也有其傳統(tǒng)性的一面,而概念的模糊性正是傳統(tǒng)文論的一大特點。 古人談詩論藝,說的話往往比較玄,比如神韻、風(fēng)骨什么的,大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王國維雖然在《人間詞話》里明確批判了這些玄而又玄的古典神秘主義色彩,但自己畢竟是在這種氛圍里長大的,要想完全擺脫并不容易。所以,“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許*好的辦法就是把整部《人間詞話》梳理下來,那時候大約就可以會然于心了。 但是,歸納法和演繹法或許可以并行不悖。在這里,我先把“境界”一詞的來歷和影響力簡單講講,然后再發(fā)掘根源,*后再去給它下一個定義。 古人談詩論藝,*常用也*經(jīng)典的一個概念是“意境”,這是唐代詩人王昌齡所著的《詩格》中*早用起來的一個詞。“境界”看上去和“意境”有幾分相似,而學(xué)者們一般會說“境界”完全是一個外來詞語,是佛經(jīng)里的概念。 的確,“境界”一詞在大乘、小乘經(jīng)典里都很常見。佛經(jīng)里用到“境界”,意思非常普通,即“疆界”,*大的引申也就是“范疇”了,并不存在什么深刻含義。但這是不是一個外來語呢?恐怕未必,因為本土的傳統(tǒng)典籍里也常用的。比如《列子》說,“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后漢書》說,“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也都是把“境界”當“疆界”來用。從這個源頭來理解,王國維所謂詞的境界,應(yīng)該就是說詞所營造出來的一個獨立的藝術(shù)空間。 如果這樣理解,的確可以應(yīng)付《人間詞話》里的大多數(shù)問題,但王國維說,“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這就意味著有些詞是沒有境界的。也就是說,這樣的一些詞并沒能營造出一個屬于自己的藝術(shù)空間。這似乎就難于理解了。因為一般來說,任何詞作都有自己的藝術(shù)空間,只是高下有別罷了。我們只能說陽春白雪境界高,下里巴人境界低,但不能說陽春白雪有境界,下里巴人沒有境界。 這問題不好解釋,但越是不好解釋,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人來作解釋。這就和經(jīng)學(xué)的狀況很相似了: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在為經(jīng)典作闡釋,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借舊瓶裝新酒,敷衍出自家的一套理論。比如馮友蘭就以哲學(xué)家的眼光認定,所謂境界,就是人對宇宙人生的覺解程度。我想,這句話應(yīng)該是*容易被大家接受的。那么,“詞以境界為*上”也就意味著判斷一首詞的高下,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作者對宇宙人生的覺解。如果找個例子來說,歐陽修的“人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guān)風(fēng)與月”應(yīng)該比柳永的“針線閑拈伴伊坐”更有境界,而它們都比不上蘇軾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 另外的一條理解道路是從康德和叔本華出發(fā),因為王國維對這兩位西方大哲的作品浸淫極深,他的一大劃時代的工作就是拿西哲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xué),《紅樓夢評論》就是這樣的一部名作。至于《人間詞話》是否也是西哲的底子,眾說不一。有人以為王國維的做法不過是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西方的一些概念只是被拿來作為一種便于說明問題的工具罷了。如果我們采信這種說法,無疑會輕松很多,因為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必為了理解短短的一部《人間詞話》而去硬啃康德和叔本華那些令人生畏的作品。但是,如果這種看法是錯的呢? 到底誰是誰非,似乎很難論清,但反方的意見也許更有道理:《人間詞話》深深扎根于康德和叔本華(尤其是叔本華)的哲學(xué)和美學(xué)理論,即便不能說它完全有著西學(xué)的底子,至少也得承認它是一部中西合璧的作品。那么,我們就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要想進入《人間詞話》,硬著頭皮走一遭康德和叔本華的荊棘路還是大有必要的。 從這條道路尋去,就會發(fā)現(xiàn)王的“境界”說很有可能源于叔本華的美學(xué)理論。學(xué)者們討論王的境界說,議論萬千,言人人殊,多是從《人間詞話》本身或自家的美學(xué)經(jīng)驗出發(fā),所以不能切中要害。在我看來,整部《人間詞話》就是在用叔本華的哲學(xué)和美學(xué)體系來分析中國古典詩詞,所以貫通叔本華則可以貫通《人間詞話》。對王國維在開篇**節(jié)就提綱挈領(lǐng)的“境界”概念,應(yīng)該直接從叔本華的美學(xué)體系里尋找解釋,而我以為這個解釋就是叔本華的“直觀”概念。 簡而言之,叔本華提倡一種“直觀”的審美方式——我們有好幾種方式可以感受和認識這個世界。比如我們看到了兩盤蘋果,一盤10個,一盤5個,我們就可以從中抽象出10和5這兩個數(shù)字,然后算出10+5=15,我有15個蘋果可以吃——這個簡單的觀察和思考過程就包括了抽象和推理這兩種認知方式。但審美不能用這些,而應(yīng)該用直觀:你突然間看到了這些蘋果,這些明媚的、嬌艷的蘋果。在這一刻,沒有抽象,沒有推理,剩下的只有一種東西:直觀。 二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于理想故也。 這一節(jié)看上去并不很難理解。“造境”的詞人是“理想派”,“寫境”的詞人是“寫實派”,但寫實不可能完全脫離理想,理想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現(xiàn)實。研究者們一般認為,這一節(jié)是*早把“寫實”和“理想”這兩個文學(xué)流派的劃分從西方引入中國的,我們現(xiàn)在習(xí)慣性地把文藝作品分為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兩大流派,源頭就在這里。 我們會用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這兩個標簽定義古往今來的文學(xué)家們,比如李白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杜甫則是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這已經(jīng)不用再作任何解釋了。但是,再怎么浪漫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現(xiàn)實。李白寫“飛流直下三千尺”,再大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變“直下”為“直上”;寫“白發(fā)三千丈”,再大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變“白發(fā)”為“綠發(fā)”。這就像好萊塢拍電影,一會兒地球毀滅,一會兒星際大戰(zhàn),全是不靠譜的主題。但是,人性還是固有的人性,斗爭也還是固有的斗爭,把“幫助小貓的孩子的故事”換一個場景、換一套包裝,就可以改編成“拯救地球的超人的故事”。 這問題如果放到哲學(xué)范疇里來看,根源是在休謨那里:我們的想象力不可能達到我們的經(jīng)驗以外。我們沒見過六翼天使,那么六翼天使的形象是怎么來的呢,是用人的身體嫁接上鳥的翅膀組成的;我們沒見過藍色的貓,那么藍色的貓的形象是怎么來的呢,是用藍色這種顏色染到貓的形體上而成的。我們所有能想象到的東西,分解下來都不會超出我們所經(jīng)驗過的東西。 浪漫主義不可能完全脫離現(xiàn)實。同樣,現(xiàn)實主義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理想而做到所謂的“客觀再現(xiàn)”,因為再客觀的觀察和描寫也是人作出的,只要是人作的,就脫離不了主觀性。拍一張照片算不算客觀再現(xiàn)呢?也不能算,因為你為什么拍這里而不拍那里,為什么這個時間拍而不是那個時間拍,這都是主觀的。人的一切觀察、一切敘述,都脫離不了主觀性。這問題如果放到哲學(xué)范疇里來看,就是唯心主義哲學(xué)家貝克萊所謂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叔本華認為這是一個來自古代印度的真理,在歐洲被貝克萊重新發(fā)現(xiàn)。) 試想我們要拍一部新聞紀錄片,我們的目標是:客觀、真實。但是,紀錄片不可能保留這個新聞事件的所有素材,必須對素材有所取舍,這個時候,不同人的不同取舍就會給這部片子帶來完全不同的個人色彩。那么,這部片子還稱得上客觀、真實嗎?史書的編纂也是一樣的道理,選擇就是判斷,而判斷自然就是主觀的。
人間詞話講評 作者簡介
蘇纓,學(xué)者。著有《納蘭詞典評》《一生最愛納蘭詞》《人間詞話講評》等文學(xué)評論著作,文風(fēng)極美,學(xué)識淵博。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經(jīng)典常談
- >
名家?guī)阕x魯迅:故事新編
- >
詩經(jīng)-先民的歌唱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史學(xué)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