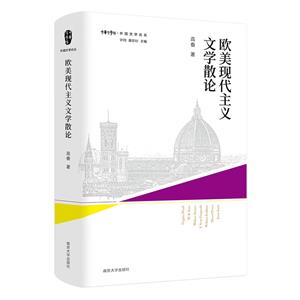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精)/外國文學論叢/中華譯學館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49341
- 條形碼:9787305249341 ; 978-7-305-24934-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精)/外國文學論叢/中華譯學館 內容簡介
本書從“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現代主義作品論”和“現代主義作家的全球視野”三個視角切入,論析歐美現代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葉芝、華萊士·史蒂文斯、菲茨杰拉德、普魯斯特、威廉·福克納、詹姆斯·喬伊斯、蒂莉·奧爾森等歐美經典作家的作品,并通過弗吉尼亞·伍爾夫、葉芝、湯婷婷、霍加斯出版社等的作品探討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并透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眼睛考察并揭示古希臘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美國文學和現代小說的特性。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精)/外國文學論叢/中華譯學館 目錄
**篇 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
003 現代主義:東西方文化融合的藝術表現
——《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序
022 走向生命詩學研究
——《走向生命詩學:弗吉尼亞?伍爾夫小說理論研究》序
039 論新時代中國外國文學批評的立場、導向和方法
060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倫理選擇與中國之道
——論《達洛維夫人》
083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中國眼睛”
106 湯亭亭的跨民族視野——讀《女勇士》
119 葉芝與中國詩學——論《天青石雕》
W. B. Yeats’s“Lapis Lazuli”and Chinese Poetics
150 華萊士?史蒂文斯的理想境界與中國古典畫——讀《雪人》
Wallace Stevens’ Ideal State of Mind and Chinese Classical Paintings
163 霍加斯出版社與英國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篇 現代主義作家作品論
179 美國大都市的文化標志
——論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197 現代主義小說的古希臘神韻
——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雅各的房間》
219 生命形神的藝術表現——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海浪》
240 詹姆斯?喬伊斯的美學思想及創作實踐
253 母性、現實與天性——讀蒂莉?奧爾森的《我站在這兒熨燙》
263 意識流小說藝術創新論
279 時間長河里的航標——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292 象征的天空——讀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301 情愛的悲劇——讀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
第三篇 現代主義作家論歐美文學
315 論古希臘文學——弗吉尼亞?伍爾夫隨筆論析之一
331 論英國文學——弗吉尼亞?伍爾夫隨筆論析之二
362 論法國文學——弗吉尼亞?伍爾夫隨筆論析之三
376 論美國文學——弗吉尼亞?伍爾夫隨筆論析之四
395 論俄羅斯文學——弗吉尼亞?伍爾夫隨筆論析之五
420 論現代小說——弗吉尼亞?伍爾夫隨筆論析之六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精)/外國文學論叢/中華譯學館 節選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中國眼睛” 弗吉尼亞?伍爾夫對中國文化的表現與大多數歐美作家一樣,主要有兩種形式。首先,“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扇子等富有東方情調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中國人散落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抒發想象中的中國意象和中國形象”;其次,基于創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藝術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體現對中國思想的領悟,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作層面,隱在或顯在地表現出基于中西方美學交融之上的全新創意”。出現在伍爾夫作品中的直觀中國意象包括中國寶塔、千層盒、茶具、瓷器、瓦罐、旗袍、燈籠等,它們散落在她的小說和隨筆之中,喻示著中國文化物品已成為英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伍爾夫的深層次理解基于她對有關東方文化的文學作品和視覺藝術的領悟和洞見,在創作中表現為全新的創作心境、人物性情和審美視野,其顯著標志是她作品中三個人物的“中國眼睛”。他們分別是:隨筆《輕率》(Indiscretions, 1924)中的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小說《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 1925)中的伊麗莎白?達洛維和小說《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中的麗莉?布里斯科。這三位典型歐洲人的臉上突兀地長出“中國眼睛”,這與其說是隨意之筆,不如說是獨具匠心。 英美學者已經關注到伍爾夫的“中國眼睛”,并嘗試闡釋其內涵。帕特麗莎?勞倫斯(Patricia Laurence)曾撰寫《伍爾夫與東方》(“Virginia Woolf and the East”, 1995)一文,指出伍爾夫賦予其人物以“中國眼睛”,旨在以“東方”元素突顯人物的“新”意。此后勞倫斯在專著《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2003)中,通過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透視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詩社之間的對話和交往,回顧和總結英國人認識、接受和融合中國文化的歷史、途徑及表現形式。她指出麗莉的“中國眼睛”,“不僅喻示了英國藝術家對中國審美觀的包容,而且暗示了歐洲現代主義者乃至當代學者對自己的文化和審美范疇或其普適性的質疑”,代表著英國現代主義的“新感知模式”。不過她的研究聚焦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重在提煉英國現代主義的普遍理念,并未深入探討伍爾夫的“中國眼睛”的淵源和意蘊。另外厄米拉?塞沙吉瑞(Urmila Seshagiri)比較籠統地指出,伍爾夫的《到燈塔去》“批判了20世紀初期英帝國獨斷式的敘述方式,用麗莉?布里斯科的眼睛所象征的東方視角擔當戰后貧瘠世界的意義仲裁者”。 那么,伍爾夫的“中國眼睛”緣何而來?其深層意蘊是什么?這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一、 東方文化與“中國眼睛” 伍爾夫筆下的三雙“中國眼睛”集中出現在她發表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即隨筆《輕率》(1924)、《達洛維夫人》(1925)、《到燈塔去》(1927),這與她對中國文藝的感悟過程及中國風在英國的流行程度相關。像大多數歐美人一樣,她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初是從東方文化中提煉的,不過當她*終在作品中啟用“中國眼睛”一詞時,它背后的中國詩學意蘊是明晰的。 她感知和了解中國和東方其他國家的主要途徑之一是她的親朋好友的旅游見聞、譯介,以及她本人與中國朋友的通信交流。1905年她的閨密瓦厄萊特?迪金森去日本旅游,其間曾給她寫信描述日本的異國風情,伍爾夫隨后撰寫隨筆《友誼長廊》(Friendships Gallery,1907),以幽默奇幻的筆觸虛構了迪金森在日本的游覽經歷。1910年和1913年,她的朋友、劍橋大學講師高?洛?狄更生兩次訪問中國,他在出訪中國之前已出版《中國人約翰的來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3),諷刺英國人在中國的暴行。1912年,弗吉尼亞與倫納德?伍爾夫結婚,后者此前曾在錫蘭工作6年,回國后撰寫并出版了《東方的故事》(Stories of the East,1921)。1918年至1939年,她的朋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繼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6)的七卷本《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和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之后,翻譯和撰寫了十余部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文史哲著作,包括《170首中國詩歌》(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更多中國詩歌》(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1919)、《中國繪畫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 1923)等,韋利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源氏物語》(The Tale of Genji, 1925—1933)、《道德經研究及其重要性》(The Way of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 1934)、《孔子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8)、《中國古代三種思維》(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39)等。伍爾夫曾在小說《奧蘭多》前言中感謝韋利的“中國知識”對她的重要性。1920年伍爾夫的朋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回國后出版《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一書,論述他對中國文明的領悟和建議。1925年她的密友、藝術批評家羅杰?弗萊,選編出版了《中國藝術:繪畫、瓷器、紡織品、青銅器、雕塑、玉器導論》(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to Painting, Sculpture,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 Minor Arts,1925),并撰寫序言《論中國藝術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rt”),詳述他對中國視覺藝術的理解。1928年她的另一位密友、傳記作家利頓?斯特拉奇,出版一部關于中國皇帝和皇太后慈禧的諷刺傳奇劇《天子》(Son of Heaven,1928)。1935—1937年,伍爾夫的外甥朱利安?貝爾到國立武漢大學教書,不斷寫信給她,介紹中國文化和他喜愛的中國畫家凌叔華。1938年,朱利安在西班牙戰死后,伍爾夫與凌叔華直接通信,探討文學、文化與生活,并在信中鼓勵、指導和修改凌叔華的小說《古韻》。上述人員都是伍爾夫所在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成員,該文化圈堅持了30余年的定期活動,他們對中、日等國文化的深入了解和主動接納對伍爾夫的影響深遠。他們有關中國文化的作品基本出版于20世紀20年代,這與伍爾夫20年代作品中出現三雙中國眼睛相應和。 伍爾夫對中國和東方文化的深層領悟源于她對相關文藝作品的閱讀。20世紀初期,英國漢學研究有了很大發展,一方面理雅各、翟理斯、韋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翻譯的中國典籍和文藝作品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量出版;另一方面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于1916年成立,閱讀英譯中國作品或學習漢語變得便利。中國藝術在20世紀初期的英國社會受到熱捧,一位出版商曾在前言中概括這一態勢:“對中國藝術的興趣和領悟正在日益增強,近二三十年中,有關這一專題的著作大量出版便是明證。”他在該書中列出了20世紀頭30年有關中國藝術的出版書目,其中以“中國藝術”為題目的專題論著多達40余本。伍爾夫的藏書中有阿瑟?韋利的《170首中國詩歌》、翟理斯的《佛國記》(The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1923)和《動蕩的中國》(Chaos in China,1924)、奇蒂的《中國見聞》(Things Seen in China,1922)等書籍,同時伍爾夫夫婦共同經營的霍加斯出版社曾出版2部有關中國的著作,《今日中國》(The China of Today, 1927)和《中國壁櫥及其他詩歌》(The China Cupboard and Other Poems,1929)。伍爾夫究竟閱讀過多少有關中國的書籍已很難考證,從她撰寫的隨筆看,她曾閱讀一些英美作家撰寫的東方小說,也閱讀過中、日原著的英譯本。她不僅積極領悟人與自然共感共通的東方思維模式,而且青睞東方人溫和寧靜的性情。 她對東方審美的領悟大致聚焦在人與自然共感共通的思維模式中。 她體驗了以“心”感“物”的直覺感知。在隨筆《東方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East”,1907)中,她評論英國作家夏洛特?羅利梅(Charlotte Lorrimer)的小說,贊同小說家的觀點,“我們已經遺忘了東方人當前依然擁有的珍貴感知,雖然我們能夠回憶并默默地渴望它。我們失去了‘享受簡單的事物——享受中午時分樹下的蔭涼和夏日夜晚昆蟲的鳴叫’的能力”。她認為“這是歐洲文化走近神秘的中國和日本時常有的精神狀態;它賦予語詞某種感傷;他們能欣賞,卻不能理解”。雖然該小說僅描述了一位西方婦女目睹日本母親平靜地接受喪子之痛的困惑和費解,伍爾夫對它的評價卻很高,認為“這些在別處看來極其細微的差異正是打開東方神秘的鑰匙”。 她深深迷戀于人與自然共通的審美思維。她曾撰寫隨筆《心靈之光》(“The Inward Light”,1908)和《一種永恒》(“One Immortality”, 1909),評論英國作家菲爾丁?豪(Harold Fielding Hall,1859—1917)的兩部同名小說。她在隨筆中大段摘錄小說中的東方生命意象: 世界萬物鮮活美麗,周圍的草木花鳥都與它一樣是有靈魂的,正是這些相通的靈魂構成了和諧而完整的世界。 生命是河流,是清風;生命是陽光,由色彩不同的獨立光束組合而成,它們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指令某一色彩的光束在燈盞中閃爍而另一色彩的光束在爐火中燃燒。生命是潮汐,它以不同方式流動,其本質卻相同,它穿越每一種生命體,穿越植物、動物和人類,他們自身并不完整,只有當無數個體融合起來時才構成整體。 她認為這些東方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那些“枯燥而正式”的信仰,充分表現了生命體與大自然的共感與應和。她這樣評價這部小說: 的確,本書給人的印象是一種特別的寧靜,同時也有一種特別的單調,部分可能出自無意識。那些不斷用來表達其哲學思想的隱喻,取自風、光、一連串水影和其他持久之力,它們將所有個體之力和所有非常規之力,均解釋為平和的溪流。它是智慧的、和諧的,美得簡單而率真,但是如果宗教誠如豪先生所定義的那樣,是“看世界的一種方式”,那么它是*豐富的方式嗎?是否需要更高的信念,以便讓人確信,*大限度地發展這種力量是正確的? 雖然伍爾夫的點評表現出一種霧里看花的困惑,不過她對物我共通的東方思想的領悟是深刻的。她感悟到,作品的“智慧”“和諧”與“美”是通過隱喻(均取自自然持久之力)來表現的,而隱藏在“物象—心靈”隱喻模式之下的,是東方哲學的基本思想,即自然持久之力與生命個體之力是共通的,均可以解釋為“平和的溪流”。她的點評,從某種程度上應和中國傳統的共通思想,比如王夫之的“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之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間,幾與為通,而浡然興矣”。身外的天化與身內的心靈之間存在著一個共通的結構模式(“相值而相取”),當個體生命在天地之間悠然而行之際,心靈與物象的通道忽然開通,審美意象油然而生。難能可貴的是,伍爾夫在贊嘆“所有人的靈魂都是永生的世界靈魂的組成部分”的東方思想之時,已經自覺地領悟到東方藝術之美在于物我共通的哲學理念及其表現方式。 在閱讀中國原著英譯本時,她感受到中國文學真中有幻、虛實相生的創作風格。她曾撰寫隨筆《中國故事》(“Chinese Stories”,1913),專題評論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她覺得《聊齋志異》的故事就如“夢境”一般,不斷“從一個世界跳躍到另一個世界,從生轉入死”,毫無理路且總是出人意料,令她疑惑它們究竟是奇幻的“童話”還是散漫的“兒童故事”。雖然一頭霧水,但她還是從中捕捉到了藝術之美感:“它們同樣頗具幻想和靈性……有時會帶來真正的美感,而且這種美感因陌生的環境和精致的衣裙的渲染而被大大增強。”其英文原文是:“The true artist strives to give real beauty to the things which men actually use and to give to them the shapes which tradition has ordained.” 正是基于這一啟示,她在隨后的創作中不斷思考生活之真與藝術之幻的關系問題,不斷提問:“何謂真,何謂幻……柳樹、河流和沿岸錯落有致的一座座花園,因為霧的籠罩而變得迷蒙,但是在陽光下它們又顯出金色和紅色,哪個是真,哪個是幻?”她的答案是,文學之真從本質上說是生命之真與藝術之幻的平衡,“*完美的小說家必定是能夠平衡兩種力量并使它們相得益彰的人”。她的真幻平衡說與中國明清時期小說家們的“真幻說”相通,比如幔亭過客稱贊《西游記》“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脂硯齋評《紅樓夢》“其事并不真實,其情理則真”;閑齋老人稱頌《儒林外史》“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這些均揭示了對文學藝術虛實相生本質的自覺意識。 她從日本古典名作《源氏物語》(The Tale of Genji,1925)英譯本中感悟到了東方藝術形式美的奧秘。她從這部錯綜復雜的宮廷小說中看到的不是日本女子凄婉的命運,而是東方藝術之美。她指出,作品的美表現在“雅致而奇妙的、裝飾著仙鶴和菊花”的物品描寫中,其根基是創作者紫式部的審美信念,即“真正的藝術家‘努力將真正的美賦予實際使用的物件,并依照傳統賦形’”,由此藝術之美才可能無處不在,滲透在人物的呼吸、身邊的鮮花等每一個瞬間中。伍爾夫對紫式部藝術思想的推崇與領悟,在一定程度上貼近中國審美“平淡自然”的境界,比如司空圖的“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或蘇軾的“隨物賦形,盡水之變”。這里,司空圖與蘇軾將隨物賦形視為創作的*高境界,強調藝術之真在于外在之形與生命之真的自然契合,不刻意雕琢,無人工之痕。伍爾夫從紫式部的作品中感悟到的也正是隨物賦形的創作理念。 除了物我共感共通的審美思維之外,她另一個關于中國文化的深刻印象是中國人寧靜、恬淡、寬容的性情。她曾評論美國小說家赫爾吉海姆的兩部小說《爪哇岬》(Java Head,1919)和《琳達?康頓》(Linda Condon,1920)。她在隨筆《爪哇岬》中生動描述了出身高貴、個性恬淡的中國女子桃云,她嫁到美國后,對鄰里無事生非的飛短流長淡然處之,對道德敗壞人士的挑逗誘惑不為所動,但*終因環境所迫吞下鴉片藥丸,在睡夢中安靜死去。在隨筆《美的追蹤》中,她列出了兩尊遠古的美的雕像,“一尊是灰綠色的中國菩薩,另一尊是潔白的古希臘勝利女神”,指出小說主人公琳達?康頓早年的生活是由灰綠色的中國菩薩主宰的,“她的表情意味深長且寧靜,蔑視欲望與享受”。 這便是伍爾夫的中國和東方印象。雖然零碎,但從每一個碎片中,她都讀出了中國和東方其他國家的思維之美與性情之和,以及它們與歐美文藝的不同。 單純依靠這些文字碎片,很難獲得對中國思維和性情的整體理解,幸運的是,她從20世紀初在英國廣泛流行的“中國風”(Chinoiserise)物品上所繪制的中國風景圖案中獲取了直觀的視覺印象。這些簡單而寧靜的中國圖像頻繁出現在瓷器、屏風、折扇、壁紙、畫卷、絲綢、玉器之上,展現在倫敦中國藝術展和大英博物館東方藝術部中,或者以建筑物的形式矗立在英國國土上(比如坐落在倫敦皇家植物園邱園中的中國寶塔,修建于1761—1762年)。這其中,*廣為人知并給人深刻印象的是源自中國的垂柳圖案青花瓷盤(willow pattern blue plate)。 *初這些青花瓷盤是由傳教士和商人從中國帶到歐洲的。17、18世紀在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易活動推動下,青花瓷盤開始從中國大量銷入歐洲各國。英國人從17世紀開始仿制中國青花瓷,到18世紀已經建立了較大規模的陶瓷生產廠家。他們不僅模仿中國青花瓷盤的圖案,而且采用轉印圖案技術,將復雜圖案做成瓷胚,用機械方式大量重復印制,同時他們還賦予垂柳圖案以凄美的中國愛情故事。這些青花瓷故事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報刊、書籍、戲劇、小說中被不斷演繹,將一個帶著濃郁中國風情的故事慢慢定型,在英國社會家喻戶曉,成為英國人遙望中國文化的一扇視窗。 青花瓷盤上的基本圖案是這樣的:瓷盤中心是一顆大柳樹,柳枝隨風飄揚;柳樹的左邊矗立著亭臺樓閣,四周環繞著桃樹、玉蘭樹等,樹下扎著可愛的籬笆;柳樹的右邊有一座小橋,橋上行走著三個人。小橋的前方是湖泊,不遠處有一條遮篷船,船夫正站在船頭撐篙,更遠處是一座小島,上面有農舍、寶塔和樹木。柳樹的正上方飛翔著一對斑鳩,四目相對,含情脈脈。 圖案的背后流傳著一則古老的中國愛情故事:很久以前,在中國杭州,一位官吏的女兒愛上了父親的文書,但父親逼迫女兒嫁入豪門,于是那對情侶只能私奔。橋上的三個人正是出逃中的女兒和她的戀人,后面緊緊追趕的是手執皮鞭的父親。女兒和戀人渡船逃到小島上生活了多年,后來被人發現后被燒死。他們的靈魂化作斑鳩,飛翔在當初定情的柳樹上空,形影不離。 這一青花瓷傳說有很多版本,以童謠、兒童故事、戲劇、小說乃至電影等方式不斷在英國重復演繹。比如,1865年,在利物浦的威爾士王子劇院上演了戲劇《垂柳瓷盤的中國原創盛典》(An Original Chinese Extravaganza Entitled the Willow Pattern Plate);1927年由美國人詹森執導,所有角色均由中國人扮演的古裝默片《青花瓷盤的傳說》(The Legend of Willow-Pattern Plate)在倫敦首映,英國女王陛下出席了首映儀式。 這種瓷盤與傳說同步且長期傳播的方式,幾乎將垂柳圖作為中國的象征印入幾代英國人的心中。瓷盤中所展現的中國審美方式既困擾了英國人(尤其是早期英國人),也在潛移默化中讓英國人默認了這一表現方式,乃至視其為理解中國思想的參照物。 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823年點評青花瓷盤圖案時所表達的不解,代表了早期英國人對東方思維的困惑。蘭姆認為它是“小小的、毫無章法的、蔚藍而令人迷醉的奇形怪狀的圖案”,那上面有女子邁著碎步走向停泊在寧靜的小河彼岸的輕舟,而“更遠處——如果他們世界中的遠和近還可以估計的話——可以看見馬群、樹林和寶塔”。蘭姆既不習慣畫面中的遠近距離,因為完全不符合透視法的布局,也不習慣將人物非常渺小地置于自然風景之中的表現方式,它與西方繪畫聚焦人物而隱去自然風景的傳統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對20世紀初期的伍爾夫而言,這一視像卻為她理解令人費解的中國文字故事提供了參照物。她閱讀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志怪故事后,覺得“那些氛圍古怪且顛三倒四的小故事,讀了三五則后,讓人覺得好像行走在垂柳圖案青花瓷盤里那座小橋上一般”。可以看出,伍爾夫對垂柳圖案比較熟悉,她嘗試用它來理解蒲松齡的故事在人、獸、鬼之間的快速變形,理解那些“夢境”一般的無厘頭敘述。 至此,我們已經追蹤了伍爾夫的“中國眼睛”與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之間的淵源關聯。作為20世紀初期渴望了解并熱情接納中國文化的英國作家,伍爾夫不僅從大量閱讀中感受東方人的思維模式和性情,而且將東方人直觀感應昆蟲、河流、陽光、清風、人獸鬼幻變,以及中國女子的恬淡、中國菩薩的寧靜無欲等點點滴滴均注入垂柳圖案青花瓷盤之中。整個東方便異常生動地呈現在她的面前。中國青花瓷盤所發揮的作用就如“眼睛”一般,將一種全新的觀察世界和理解生命的方式展現在她面前。正是透過“中國眼睛”,伍爾夫重新審視并拓展了英國人的生命故事。 ……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精)/外國文學論叢/中華譯學館 作者簡介
高奮 浙江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英國文學研究分會常務理事、浙江省外文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作協會員。任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學者(2006—2007)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訪問學者(1995—1996)。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對英美現代主義經典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華萊士?史蒂文斯、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與東方文化的關系做深入研究。迄今已出版學術著作十余部,主要包括:《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及其文學創作實踐研究》(2021)、《走向生命詩學——弗吉尼亞?伍爾夫小說理論研究》(2016)、《小說、詩歌與戲劇探尋之旅:英語文學導讀》(2013)、《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2012)、《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源與流》(2000)等。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70余篇。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弗吉尼亞?伍爾夫小說理論研究”(2009)、“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及其文學創作實踐研究”(2014)。 獲教育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2019)和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多項。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姑媽的寶刀
- >
月亮虎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自卑與超越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