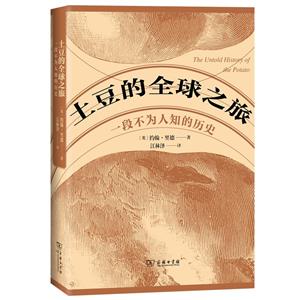-
>
上海花園動植物指南
-
>
世界鳥類百科圖鑒:亞洲鳥類/歐洲鳥類/非洲鳥類/澳洲鳥類(全五冊)
-
>
科壇趣話:科學、科學家與科學家精神
-
>
愛因斯坦在路上:科學偶像的旅行日記
-
>
不可思議的科學史
-
>
動物生活史
-
>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全新修訂版)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98738
- 條形碼:9787100198738 ; 978-7-100-19873-8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普通大眾土豆,改寫了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歷史。 一顆土豆的全球之旅,一部人類文明的變遷史。 ² 英國倫敦大學名譽研究員歷時多年搜集資料,探尋土豆的傳奇歷史。 ² 文章從土豆發源地開始,跨越歐洲、美洲*后來到中國,以土豆為引,為你講述一場有趣的世界歷史課。 ² 本書參考大量文獻,趣味之外增添嚴謹考究。 ² 本書作者有超過40年拍攝經驗,親自拍攝珍貴影像,極具收藏價值。 ² 植物、歷史愛好者必不可少的手邊讀物! 從安迪斯山脈的自給食物到歐洲的產業化商品,土豆的社會、經濟、歷史變遷跨越了3個世紀! 大約8000年前,安第斯山區的前印加人將土豆馴化。16世紀末,土豆和其他西班牙征服南美得戰利品一起被帶到歐洲,歷經歐洲各國王位繼承戰爭、拿破侖戰爭、工業革命等,土豆種植范圍擴大,*終19世紀完全確立了其在歐洲家庭中的主食地位。 土豆為引,為你講述一場妙趣橫生的世界歷史課,從獨特視角出發,看人類文明發展軌跡。 你可曾想象到,我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土豆曾掌握著世界走向? 一顆土豆,竟然是兩個國家開戰的導火索? 一顆土豆,還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的象征? 一顆土豆,控制著一個新西蘭毛利人的人口數量? 一顆土豆,甚至導致了《谷物法》的廢除? 你能想象沒有土豆的生活嗎? 16世紀的歐洲北部,土豆曾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必需品,如果沒有土豆,那世界將會變成什么樣? 作者從南美洲出發,跨越歐洲再走向全世界,詳細描繪了土豆的起源、變遷和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影響。從大航海時代探尋新大陸,到新時代求索之路,觀察土豆貿易遷移現象,反映了人類在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上都有極其重要的發展。從一顆土豆的全球之旅,看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 珍貴影像記錄,一年半的實地考察,力求還原真實的土豆遷移過程,帶來極致閱讀體驗! 本書作者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歷時多年搜集,先后曾多次到訪國際土豆中心、萬卡約研究中心、蘇格蘭作物研究所和英國皇家園藝學會進行學術研究。同時,作者還在愛爾蘭西海岸的康納馬拉地區進行了長達18個月的實地考察,拍攝珍貴影像。 伴隨大量文獻和資料,珍貴影印和實地紀實,讓本書科學嚴謹,又不失風趣,力求為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土豆環球歷史。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內容簡介
從秘魯庫斯科太陽神廟里的黃金土豆,到生長在愛爾蘭泥地中的同類作物;從如今中國大量種植以制作麥當勞薯條的食材,再到對其基因組的全面測序,比頓夫人、查爾斯?達爾文、列寧等名人故事點綴其間,土豆的歷史既引人入勝,又令人直呼過癮。在人類文明史的燦爛畫卷中,約翰?里德成功鉤沉出土豆故事的整體脈絡:從起源到進化,再到進入食譜乃至成為整個人類社會有機組成部分的神秘歐洲之旅。時至今日,隨著優選人口的迅速膨脹,人類生存環境穩定性的重要程度日益凸顯,在這本對我們往往視而不見的食物進行研究的著作中,里德生動形象、通俗易懂地向我們展示了土豆仍然可能發揮的作用。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目錄
引言 ...1
致謝 ...5
圖片列表 ...8
第1部分 南美洲
第1章 從安第斯山脈到火星...3
第2章 土豆究竟是什么...31
第3章 馴化...43
第4章 來自何方...61
第5章 美味佳肴...95
第2部分 歐洲
第6章 寂然的狂喜...119
第7章 昔日時光...145
第8章 令人沮喪的食物...171
第9章 土豆生長之地...203
第10章 饑荒的種子...235
第11章 亞當的子孫...259
第3部分 世界
第12章 致命的疾病...289
第13章 利用科學...321
第14章 肩負使命之人...345
第15章 環球之旅...359
第16章 發展中國家...375
第17章 蘋果的價格...391
參考文獻 ...402
索引 ...414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節選
第1章 從安第斯山脈到火星 當宇航員走出地球軌道,去進行殖民火星的冒險時,新鮮收獲的土豆將成為他們日常飲食中的一大特色。由于地球與火星之間的往返旅行需要耗時三年,攜帶足夠的現成食物不切實際,得益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簡稱NASA)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開發的“生物再生生命支持系統”(Bioregenerative Life Support System,簡稱BLSS),機組人員可以自己種植蔬菜。 “BLSS”是一種自我維持系統,它可以將一季農作物的收獲循環利用于下一季農作物的生產之中;同時,它也可以為宇航員供應蘿卜、洋蔥、生菜、西紅柿、辣椒和草莓,使其能夠享用名副其實的新鮮沙拉。但不管在太空還是在火星,土豆都會是至關重要的菜譜主角。無論谷物還是豆制品都比不上它的慷慨大方:土豆是目前人類已知的全部營養成分的*好集合。 提供食物還不是土豆能夠給予人類星球探險家的全部。在太空中,持續的氧氣供應同樣必不可少,因此,生長中的植物能夠進行吸收二氧化碳并釋放氧氣的光合作用,更使土豆成為無價之寶。土豆的這種雙重作用的確是一種巧合:在宇宙飛船的封閉環境中,一片面積足以供應宇航員日常食用所需的土豆田,同樣能夠在釋放維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足夠氧氣的同時,清除他們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 土豆具有能夠在太空中和火星上保持人類生存和健康的潛力,這在NASA的示范中得到了證明,但對于那些對土豆了如指掌的人來說,這只不過是土豆的非凡價值與靈活用處的又一范例。這些司空見慣卻腳踏實地的植物塊莖理應成為人類太空冒險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對其價值的崇高表彰。數萬億美元和數十億工時的花費是否空擲,以及人類*具雄心和*為復雜的事業能否成功,*終將取決于宇航員種植土豆的能力。 如果說土豆的未來可能會延伸到火星,那么它的起源則牢牢根植于安第斯山脈。地球上*古老的土豆品種在那里肆意生長—數以百計,卻又雜亂無章、無法辨識,尤其難以發現其食用價值:土豆的枝葉不能食用,因為其中充滿了毒性強烈的糖苷生物堿—龍葵素,大多數土豆品種的塊莖不但同樣具有毒性,而且體積很小。所以我們很難想象,*初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夠鼓勵人類去嘗試改良土豆。然而,人類*終還是進行了這樣的試驗。考古證據顯示,早在8000多年前,可供食用的栽培土豆即已出現。從那時起,安第斯山脈的農民已經培育了數百個可供食用的土豆品種—事實上,他們已經為日常栽種的不同種類的土豆取了超過1000個名字,每個品種多以其優異的生產率、可口性、耐溫性、抗病蟲害能力和貯藏質量而得名。盡管許多品種的名字具有相同含義,但人們普遍認為,安第斯地區目前至少種植了400個截然不同的土豆品種。 根據適合生長的不同海拔高度,安第斯山脈的土豆品種可以被劃分為三類。在海拔3000米到3500米之間,降水和溫度相得益彰,被命名為“papamaway”的土豆品種往往能夠獲取不錯的產量;在海拔3500米到4000米之間,是相對耐寒的土豆品種“papapuna”的生長空間;如果海拔超過4000米,則只有抗霜性極強的“papa ruki”能夠保持茁壯成長。 沒有一個農民家庭能夠種植全部400種的土豆,每個家庭通常會從當地常見的30種、40種或者50種土豆品種中來挑選合適的種類,這種選擇往往會隨個人喜好而變化。每個農民都對不同種類的土豆有堅定不移的頑固看法—在特定環境中,哪些品種可以期待高產、哪些可以抵御霜凍和病害、哪些可以保存時間*長、哪些易于烹飪,而哪些又*為可口。每個農民家庭的成員都可以隨機從商店中挑選25個土豆品種,然后輕而易舉地說出其中每一種類的名稱與特征。這并不像聽起來那么難,因為當地所謂“原生土豆”(native potatoes)和我們平時所熟知的土豆大不一樣。它們普遍有著各種各樣的形狀和顏色:形狀包括長而細、矮而胖、錐形、球形、腎臟形和六角風琴形;顏色則涉及從白到黑的全部維度,包括各式色調的紅色、黃色和藍色;其花紋同樣形形色色,包括圓點、條紋、濺花、眼鏡狀斑紋和密布的斑點。 ………… 第15章 環球之旅 2003年1月下旬,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西部高山上的一個村莊里,蘇萬庫希特(So Wan Kusit)和她的鄰居們對于眼前發生的一切感到不知所措。她們的土豆一直欣欣向榮,現在卻逐漸枯萎—整片農田的每株作物都在短短幾天內被摧毀。曾經充滿希望的田野,現在呈現一貧如洗的丑陋景象;曾經對于美好明天的憧憬,如今卻變成了確鑿無疑的苦難歲月。在意識到無望拯救自己的作物之后,村民們干脆將其連根拔起,沿路擺成一排—就像遭遇了一場未知瘟疫而陷入深沉哀傷的受害者們一樣。蘇萬庫希特說:“莊稼就這么死了,我不知道為什么。” 在500英里以外的首都莫爾茲比港(Port Moresby),出現了有關此事的簡短新聞,這很難不讓人聯想起150多年前倫敦收到的來自愛爾蘭的零星報道,但這一次,受災地區更容易獲取相關信息和援助。巴布亞新幾內亞國家農業研究所的研究負責人塞爾吉??邦(Sergi Bang)博士帶著不祥的預感來到了這個偏遠的村莊。經過簡單檢查之后,他*擔心的事情得到了證實:晚疫病。巴布亞新幾內亞此前從未遭遇這種病害,現在卻席卷了整個國家,不僅完全摧毀了本應養活蘇萬庫希特和無數個類似家庭的糧食作物,并且使得年輕但繁榮的土豆栽培產業(年產值已經達到1100萬美元)徹底垮臺。1970年代,援助人員才把土豆引入了這片高地,盡管姍姍來遲,但土豆迅速在當地農村經濟中占據了重要地位。而在經過近30年的順利擴張之后,遭人唾罵的土豆寄生蟲—致病疫霉—還是突破了這個*后的堡壘。 邦博士可以猜到病害是如何發生的。幾乎可以肯定,病害孢子是從鄰近的印度尼西亞伊里安查亞(Irian Jaya)地區隨風飄進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成千上萬來自印度尼西亞各地的難民被強行安置在這片靠近邊境的土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難民來自晚疫病流行的地區,他們隨身攜帶的種薯已經感染了病害。盡管這些難民掌握了在栽培過程中控制病害的方法,但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對此還一無所知。從寄生蟲的視角來看,巴布亞新幾內亞及其土豆簡直是一片全無防備的處女地。邦博士告訴蘇萬庫希特和村民們,把連根拔出的作物埋掉,幾年之內不要再種土豆,“這樣一來,致病疫霉就會死掉”。 這個國家的面積比加利福尼亞州略大一些,但鋪設公路的總長度還不到500英里;這個國家的地形復雜多變,只有1.9%的土地適合種植作物,在這種情況下,土豆始終是一種非常珍貴的作物,特別對于全國540萬人口中85%需要依靠自給自足的以農業生產為生的農民來說更是如此。這個國家的高地極為適合種植土豆,相對較高的海拔緩和了赤道地區太陽的熱量,一年到頭的雨季更滋潤了肥沃的土壤。在這種涼爽而潮濕的環境中,農民全年都可以種植土豆。尤其在沒有病蟲害威脅的情況下,農民可以放心大膽地追求*高產量,不必考慮土豆是否具有抗性。然而不幸的是,這種有益于土豆成長的環境,同樣適合滋生致病菌。一旦晚疫病從伊里安查亞越過邊境,它很快就在整個巴布亞新幾內亞蔓延開來。 到了2003年5月,全國土豆已被病害摧毀。巴布亞新幾內亞山區的農民可能是全世界*后一批享受到土豆好處的人,也是*后一批暫時不必與其邪惡寄生蟲展開斗爭的人。現在他們也成了受害者,但是,農民們至少可以尋求一個由關心民眾福祉和土豆發展的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組成的國際組織的援助。當蘇萬庫希特和其他農民依靠替代作物艱難求生時,城市消費者也只能用比本土產品高2到3倍的價格購買進口土豆,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府呼吁國際社會的援助。在幾周時間里,來自澳大利亞和利馬國際土豆中心(CIP)的科學家就訪問了這個島國,并制定了一個旨在解決當前問題的研究和開發項目。 國際土豆中心的建立初衷之一,就是在發展中國家維護糧食安全和減少貧困發生,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農民所處的困境立刻引發了國際土豆中心科學家的關注。但是對于巴布亞新幾內亞內陸山區的民眾來說,來自外界的關注是一種頗為新鮮的事物。事實上,直到1930年代,當探索未經勘探的河谷的澳大利亞淘金者遭遇了一群此前聞所未聞的當地居民時,這片人口稠密之地才首次為世人所知。淘金者之一邁克爾??萊希(Michael Leahy)在其作品《被時間遺忘的土地》(The Land that Time Forgot)(1937年出版)中寫道,這些土著體格十分健壯,頭上裝飾著鳥的翅膀,串串貝殼掛在穿透鼻子的飾物上。許多人刺有紋身,隨身攜帶著弓箭和鋒利如刀的石斧。他們并不歡迎外人造訪。淘金者的營地遭到了襲擊,搬運工人慘遭殺害,萊希本人也被石斧照頭砍了一刀,左耳轟鳴不止,但是他的決心并未動搖。由于堅信內陸藏有更多的秘密(和黃金),萊希進行了2次偵察飛行,為一次由礦業財團資助的大型探險做好準備。他寫道: 在兩座高聳的山脈之間,我們看到了一個廣闊而平坦的山谷,寬約20英里,長度難以判斷,一條非常曲折的河流從中蜿蜒流過……在我們的下方,就是肥沃土壤和稠密人口存在的證據—像棋盤一樣整齊的方格土地中分布著一串錯落有致的花園,四五個一組的長方形草屋密密麻麻地點綴在周圍的景色中。除了這些草屋,下面的風光就像比利時的小塊田野……這個人口眾多的島嶼被群山緊緊包圍著,整個世界甚至都沒有意識到其存在。 ………… 據估計,在我訪問高地時,整個巴布亞新幾內亞只種植了不到200公頃的土豆。我在城里吃到了土豆,也在市場上看到有人售賣很好的土豆,但沒有一塊土豆田曾經引起我的注意,只有婦女在隨處可見的紅薯堆上辛勤勞作。從那時起,土豆栽培實現了引人注目的增長,以至于迅速成為家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從中不難得出結論:土豆一定也為當時農村人口發生的大量增長做出了顯著貢獻。從1980年起的20年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和離開這片土地的人數增長超過70%。令人驚訝的是,高地的耕地面積幾乎沒有增長,也就是說,只有集約化生產或種植新作物才能使糧食產量與人口增長保持同步,這顯然支持了土豆一直是人口增加的“罪魁禍首”的觀點,就像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和巴布亞新幾內亞類似。1960年代以來,土豆已經成為世界傳播速度*快的主要糧食作物。如今,在聯合國192個成員國d中,已有148個國家種植土豆,比除了玉米之外的其他任何作物都要多。這一偉大的環球之旅真正開始于17世紀,當時歐洲的先驅航海家們認定,土豆會是他們儲備中的一種有用之物—既作為航海食物,也作為栽培在未知大陸之上的作物,盡管在從南美洲引入歐洲一個世紀之后,警惕的家庭主婦仍然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土豆。英國、法國、德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隊把土豆運往世界各地的貿易港口、捕魚站和捕鯨站。 歷史記錄顯示,早在1603年,荷蘭殖民者就已經把土豆帶到了位于臺灣海峽的澎湖列島。1650年,根據一名游客的記錄,比利時和法國的傳教士又將其引入了臺灣。很快,這種作物就傳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并在那里獲得了諸如“地豆”、“土果”和“豐產塊莖”之類的名字。土豆另外一條傳入中國的線路,則是從東歐出發,翻越烏拉爾山脈,直抵東亞的草原地區——事實證明,這是適合土豆生長的完美環境。在近東地區,作為19世紀早期英國駐奧斯曼帝國和波斯王朝的外交代表,約翰??馬爾科姆(John Malcolm)爵士是推廣土豆的忠實擁護者。確切地說,當地甚至把土豆稱作“馬爾科姆的李子”。 在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土豆的俗名都反映了殖民統治者的國籍。在西爪哇(Java),1794年引進的土豆被稱為“荷蘭土豆”。1897年,土豆進入越南,民眾稱之為“法國塊莖”。英國東印度公司把土豆沿著貿易路線送入喜馬拉雅山脈,無怪乎夏爾巴人(Sherpas)會將其稱作“英國土豆”。據說早在18世紀,佛教的僧侶就已經開始在不丹和尼泊爾的寺院里栽培土豆,然后就像在歐洲一樣,這種全新的高產作物帶來了人口的急劇膨脹。但是,巍峨的喜馬拉雅山區缺乏足夠的生存空間,這片土地的子女無法像歐洲同類那樣移民國外或者涌入城市,只能被迫出家成為僧侶。而在另外一方面,土豆的杰出產量又給了當地天賦異稟之人以充足的時間,使其得以從容創作這片地區享有盛譽的建筑、繪畫、織物和雕塑。 1770年代(實際時間無疑還要更早),好望角已經出現了種植土豆的記錄,其不僅成為當地民眾的主食,而且為前往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船只提供補給。但是,在部分傳教士1830年代進入巴蘇陀蘭(Basutoland)(現在的萊索托)和1880年代進入東非之前,非洲的其他地區對于土豆一無所知。 總體而言,在大多數情況下,土豆在一個全新國家*初出現和種植的相關記錄都是含混不清的,但新西蘭是個例外,在異乎尋常的勤勉作用下,相關信息被高度整合。新西蘭對土豆的接受值得關注,一方面由于這是歐洲土豆運輸的*遠地點;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新西蘭是地球上*后一片被發現和殖民的適合居住的大陸。當地的**批定居者可能是來自馬克薩斯群島(Marquesas)的波利尼西亞人,他們于10世紀時抵達,自稱毛利人。毛利人來到這里靠的是獨木舟,除了航海和捕魚技術、賴以建立獨立社區的足夠人口和知識之外,他們沒有忘記帶上傳統主食紅薯——被稱為“庫馬拉”(kumara)的幼苗。 ………… 1769年,當詹姆斯??庫克船長**次太平洋航行時,曾經到過新西蘭附近;而在法國人和毛利人發生沖突時,庫克船長剛剛離開英格蘭,準備開始第二次航行。至于他對法國探險隊和“暗殺灣”事件了解多少,我們只能猜測。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他從好望角把一些土豆帶上了船,并打算栽培到新西蘭。1773年5月,庫克船長在北島的夏洛特皇后灣(Queen Charlotte’s Sound)拋錨,并指示船員在沿岸的幾個地方種植土豆與其他來自歐洲的蔬菜和谷物。4年之后,當再次來到夏洛特皇后灣時,他沮喪地發現,“菜園存在的痕跡已被全然抹去”,而且“盡管新西蘭人很喜歡這種塊根作物,但很明顯,他們沒有付出任何努力去栽培土豆”。 然而,毛利人對庫克的說法提出了質疑。毛利人通常認為,確實是庫克將土豆引入了新西蘭,根據1807年的一份報告,當時土豆不僅是一種珍貴食物,而且是重要的貿易商品: 盡管當地土著非常喜歡這種塊根,但是他們吃得很少;因為在和涉足這片海岸的歐洲船只交換鐵器時,土豆價值不菲。這種金屬的作用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特別是做成鎬頭、刮刀和短斧,土著幾乎寧愿忍受任何饑餓與困難,也要獲得鐵器。因此,當地的土豆往往被小心翼翼地儲存起來,以備遠航船只的到來。 和毛利人做生意的船只不僅來自歐洲一地。美國的捕鯨船同樣在這片水域活動,這甚至可能是土豆進入新西蘭的另外一條途徑,因為一些毛利傳統土豆和秘魯原生土豆相似程度極為驚人:多節、深眼、布滿斑點、表皮發暗、紫色果肉。眾所周知,美國捕鯨船經常在秘魯的卡亞俄(Callao)進行補給,他們很可能把秘魯土豆帶到新西蘭(值得注意的是,其船員中不乏非洲裔美國人),這從毛利人給一種深紫色外皮的細長土豆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來:黑鬼的陰莖。 但是,無論其源頭究竟為何,毛利人普遍而愉快地接受了土豆。19世紀早期,面積達到50公頃的土豆田已不再罕見。到了1850年代,根據文獻記載,僅僅兩個地方栽培的土豆面積就超過3000英畝。當時,積極進取的毛利人種植了大量土豆,以賣給奧克蘭和惠靈頓快速增長的歐洲人口。1834年,一名海軍軍官在一個沿海村莊中發現了整整4000包土豆(估計重達100噸)。1835年,部分毛利家庭前往無人居住的查塔姆群島(Chatham Islands)拓殖,而在其準備的物資中,就包括了接近80噸種薯。在隨后的20年時間里,這些家庭生產了“數百噸”土豆,其中大部分出口到了澳大利亞。 土豆在新西蘭快速發展的優勢在于,其非常易于融入毛利人現存的農業體系之中,較之傳統作物紅薯,土豆不僅產量更高,而且儲存時間更長。土豆可以使用和紅薯相同的栽培工具,也和紅薯一樣適合成為慶祝種植和豐收典禮的供品。此外,土豆不僅美味可口,而且可以產出可靠的盈余,并且能在人們打算定居的任何地方生根發芽。無論海拔高度如何,土豆都能茁壯生長,特別在紅薯難以生長的南島南部地區,土豆受到了特別歡迎。但是正如人類學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在1929年所指出的,如此普遍而熱情地接受一種全新的優質主食,必然會對整個毛利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土豆進入新西蘭的結果清楚地表明,一種全新的農業生產方式足以影響當地的經濟生活甚至環境變遷。土豆的適應能力如此之強,以至于可以種植在所有地區;此外,土豆產量極高,投入的勞動力可以換取豐厚的回報。因此,土豆不僅迅速占領了那些之前沒有栽培作物的地區,而且可能在其他地區取代紅薯的地位。 弗思相信,由于較之傳統作物,土豆需要的時間和關注更少,人們可以有更多的閑暇從事其他活動。1996年發表的一篇權威文章甚至進一步指出,19世紀早期,毛利部落之間開展的所謂“火槍戰爭”,其更準確的名字應當是“土豆戰爭”。作者認為,新西蘭當時種植土豆的面積已經相當可觀,大量的土豆被用來交換火槍,此外,既然栽培土豆所需勞動力相對較少,就有更多的戰士可以投入戰爭。正如拿破侖所指出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毛利人的戰爭中,土豆可能扮演了和火槍同樣重要的角色。 土豆同樣對毛利人的人口規模產生了重大影響,就像在南美洲和整個歐洲所產生的影響一樣。庫克船長估計,1769年,毛利人約有10萬人。由于庫克沒有看到人口可能更為稠密的內陸地區,這一數字幾乎可以肯定被低估了,但到了70年后的1840年,當英國宣稱對新西蘭擁有主權時,當地已經有了大約20萬毛利人,其人口增長速度仍然極為驚人。此后,在殖民統治、土地戰爭、經濟邊緣化、疾病和大規模社會動蕩等因素的影響下,毛利人的數量大幅下降。 但是,人口學家可能會問,毛利人此前已經在外來影響和疾病中暴露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而在世界其他地區,這些因素曾經導致大量土著人口急劇死亡,那么,為什么毛利人的增長率沒有更早下降呢?土豆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盡管沒有像歐洲和其他地區那樣留有詳細的人口普查或洗禮記錄以確認人口增長率的快速增加,但仍然有間接證據表明,在土豆引入之后,毛利人的生育率顯著上升,足以補償外國影響造成的損失。 作為一種特產,具有獨特外觀和特性的毛利土豆和“現代”土豆一起生存至今,不僅作為食物,而且具有更珍貴的寓意:一件祖先的禮物。毛利人將種植這些傳統土豆視為一種責任。有些家庭年復一年地種植同一品種,已經堅持了八九代人。他們認為,毛利土豆是傳統延續和集體認同的象征,主人會自豪地向客人提供這種象征。對于那些種植傳統土豆的農民而言,無論通過市場還是路邊攤販,這種土豆都極為暢銷(而且售價通常比“現代”土豆要高得多),但是傳統土豆產量相對較小,種植面積也不大——1905年晚疫病到來時,正是這一特點幫助古老的傳統土豆幸存下來,當時新西蘭大規模商業土豆生產完全被毀。 諷刺的是,由于疫情導致歐洲土豆暫時一掃而空,新西蘭迅速恢復了紅薯這一毛利人的傳統飲食。政府從美洲進口了高產的紅薯品種發放給農民,希望能夠借此降低國家對土豆的依賴,但這一趨勢僅僅維持到抗病性更強的土豆引入之前。同時,新西蘭也很快接受了由深受晚疫病打擊的歐美土豆種植者所制定的作物管理方法和農藥噴灑策略。土豆一旦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人們就絕對不會心甘情愿地放棄。無論何時何地,土豆提供的好處都要遠遠超過其不足。 時至今日,新西蘭每年生產50多萬噸土豆,其中大部分用于國內消費,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出口海外。事實上,土豆是新西蘭價值*高的出口作物。對于這樣一個經濟主要依靠農業的國家而言,國際市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西蘭希望可以生產物美價昂的土豆,因之在保證土豆質量標準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近的一項支出是為一家國際合作組織提供了3600萬美元資金,該組織的目標是在2010年之前對土豆基因組進行全面測序。這筆投資將使新西蘭提前獲得能夠用于培育新的改良品種和提升產品價值的關鍵信息——典型的發達國家戰略:高科技,高投入。 與此同時,為了尋找提高發展中國家土豆價值的方法,同樣耗費了大量資金和資源。和發達國家不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來說,土豆的價值更多在于維生而非賺錢,廉價和低端才是這里的重點。因此,在21世紀,有兩股截然不同的力量,裹挾著土豆不斷向前:其一,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養活吃不飽飯的人民;其二,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追求土豆商業潛力的*大化。
土豆的全球之旅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作者簡介
約翰??里德(John Reader),英國作家,一位有超過40年經驗的攝影記者,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系名譽研究員,除本書外,作品還包括《生命金字塔》(Pyramids of Life)、《消失的線索:尋找最早的人類》(Missing Links: The Hunt for Earliest Man)、《乞力馬扎羅》(Kilimanjaro)、《生命的崛起》(The Rise of Life)、《大地上的人》(Man on Earth)、《肯尼亞山》(Mount Kenya)、《非洲:一塊大陸的傳記》(Africa: A Biography of the Continent)和《城市的故事》(Cities)。 譯者簡介: 江林澤,男,1989年生,山東青島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煙與鏡
- >
隨園食單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唐代進士錄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