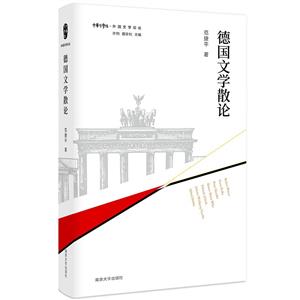-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guó)”系列(珍藏版全四冊(cè))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jiǎn)⒊視?shū)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guó)大家筆下的父母
德國(guó)文學(xué)散論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305245107
- 條形碼:9787305245107 ; 978-7-305-24510-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cè)數(shù):暫無(wú)
- 重量:暫無(wú)
- 所屬分類:>
德國(guó)文學(xué)散論 本書(shū)特色
本書(shū)匯集了范捷平教授關(guān)于德語(yǔ)文學(xué)研究的主要論文20余篇,其中主要涉及德國(guó)古典時(shí)期的作家歌德、席勒、荷爾德林、讓·保爾和德語(yǔ)國(guó)家現(xiàn)當(dāng)代重要作家卡夫卡、施尼茨勒、瓦爾澤、德布林、本雅明、耶利內(nèi)克、漢德克、霍利曼、韋伯等。全書(shū)結(jié)構(gòu)完整,行文流暢,具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水平和出版價(jià)值,反映了作者對(duì)德國(guó)古典時(shí)期的作家和現(xiàn)當(dāng)代德語(yǔ)文學(xué)作家、作品的廣泛關(guān)注與探索研究。 本書(shū)的大多數(shù)論文從文化人類學(xué)和文學(xué)互文性的視角出發(fā),對(duì)上述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做出了文學(xué)闡釋研究和生成傳播研究,也有一些論文探討了中外文學(xué)關(guān)系問(wèn)題,另外,還有若干篇論文具有一定的隨筆和反思特點(diǎn)。
德國(guó)文學(xué)散論 內(nèi)容簡(jiǎn)介
本書(shū)匯集了范捷平教授關(guān)于德語(yǔ)文學(xué)研究的主要論文20余篇,其中主要涉及德國(guó)古典時(shí)期的作家歌德、席勒、荷爾德林、讓·保爾和德語(yǔ)國(guó)家現(xiàn)當(dāng)代重要作家卡夫卡、施尼茨勒、瓦爾澤、德布林、本雅明、耶利內(nèi)克、漢德克、霍利曼、韋伯等。本文集的大多數(shù)論文從文化人類學(xué)和文學(xué)互文性的視角出發(fā),對(duì)上述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做出了文學(xué)闡釋研究和生成傳播研究,也有一些論文探討了中外文學(xué)關(guān)系問(wèn)題,另外還有若干篇論文具有一定的隨筆和反思特點(diǎn)。
德國(guó)文學(xué)散論 目錄
目錄
001 命運(yùn)如雪的詩(shī)人
——羅伯特??瓦爾澤
017 文本編織中的歷史記憶
——讀托馬斯??霍利曼的家族小說(shuō)
032 關(guān)于卡夫卡《變形記》的生成背景
039 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中的“物”之美
——里爾克、瓦爾澤的“物人間性”解讀
057 葉雋先生《文史田野與俾斯麥時(shí)代——德國(guó)文學(xué)、
思想與政治的互動(dòng)史研究》的序
060 胡一帆女士《魔鬼合約與救贖》的序
066 身體行進(jìn)中的文學(xué)書(shū)寫
——論羅伯特??瓦爾澤的散步詩(shī)學(xué)
084 真作假時(shí)假亦真
——德國(guó)戲劇對(duì)中國(guó)的開(kāi)放性接受研究
108 論瓦爾澤與卡夫卡的文學(xué)關(guān)系
125 文學(xué)經(jīng)典影片《埃爾澤小姐》中的反蒙太奇及女性形象研究
144 羅伯特??瓦爾澤《強(qiáng)盜》小說(shuō)手稿中“Eros”情結(jié)
159 語(yǔ)言的搖滾
——論彼得??韋伯小說(shuō)《沒(méi)有旋律的年代》中的聽(tīng)覺(jué)性
173 漂浮的大象
——評(píng)漢德克的默劇《在我們彼此陌生的時(shí)候》
182 《奧地利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前言
187 論耶利內(nèi)克與瓦爾澤的文學(xué)主體觀
202 歌德的自然觀解讀
216 文化學(xué)轉(zhuǎn)向中的學(xué)者主體意識(shí)
227 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的文學(xué)大師德布林
254 談?wù)劦虏剂值闹袊?guó)小說(shuō)《王倫三躍》
271 文學(xué)儀式和面具的掩飾功能
——兼論異域文學(xué)中的“東方形象”
296 瑞士當(dāng)代小說(shuō)譯叢總序
308 瑞士德語(yǔ)文學(xué)面面觀
331 《耳朵沒(méi)有眼瞼》譯序
339 圖像書(shū)寫與圖像描寫
——論羅伯特??瓦爾澤的圖像詩(shī)學(xué)
359 荒蕪的語(yǔ)言
——《雅各布??馮??貢騰》語(yǔ)言的文學(xué)性
367 “班雅曼塔學(xué)校”的符號(hào)和象征意義辨考
374 談?wù)劦抡Z(yǔ)文學(xué)中的“回家”母題
383 在紙面上散步:再讀瓦爾澤的《散步》
德國(guó)文學(xué)散論 節(jié)選
命運(yùn)如雪的詩(shī)人——羅伯特??瓦爾澤 假如瓦爾澤擁有千萬(wàn)個(gè)讀者, 世界就會(huì)安寧得多…… ——赫爾曼??黑塞 瑞士德語(yǔ)作家羅伯特??瓦爾澤(Robert Walser)的命運(yùn)與阿爾卑斯山皚皚白雪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白雪意味著遼闊和淡泊,寧?kù)o與質(zhì)樸,它意味著與任何其他色彩的格格不入。瓦爾澤就像一片輕盈的雪花那樣,飄落到了沉重的大地上,又悄悄地融入大地。直到瓦爾澤去世多年后,這位卓有才華的作家才引起國(guó)際文壇的普遍關(guān)注。說(shuō)瓦爾澤是一塊久藏在阿爾卑斯山麓白雪之中的瑰寶,也許對(duì)熟知瓦爾澤一生和其創(chuàng)作的人來(lái)說(shuō)并不過(guò)分。因?yàn)橥郀枬珊退h永的文學(xué)風(fēng)格既把人帶進(jìn)一種類似東方王摩詰的高遠(yuǎn)和陶淵明的超凡脫俗般的美學(xué)意境,同時(shí)又置人于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審美情趣之中。 瓦爾澤的文本語(yǔ)言像竊竊私語(yǔ),他寫下的小說(shuō)、詩(shī)歌以及2000多篇小品文更像輕輕飄落的雪花,在平靜中給人以無(wú)限的遐想。瓦爾澤遠(yuǎn)遠(yuǎn)算不上歐洲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但仍不失為文人的楷模,現(xiàn)代著名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卡夫卡不過(guò)是瓦爾澤人格的一個(gè)特殊側(cè)面而已。據(jù)穆齊爾稱,瓦爾澤是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開(kāi)山鼻祖之一,當(dāng)今瑞士德語(yǔ)作家的身上或多或少帶有瓦爾澤的烙印,瓦爾澤是德語(yǔ)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象征。 那是1956年的圣誕節(jié),瓦爾澤在瑞士赫利薩精神病院美美地吃了一頓午餐,酸菜豬排香腸加甜點(diǎn)心,比往常豐盛得多。飯后,這位患了二十七年精神分裂癥的作家與往常一樣獨(dú)自出門散步,這已是他幾十年來(lái)養(yǎng)成的習(xí)慣。與德語(yǔ)文學(xué)史上另一位患精神病的著名詩(shī)人荷爾德林一樣,瓦爾澤在精神病院的床榻下也是一堆因散步而走破了的舊皮鞋。散步在瓦爾澤的生命中的重要程度似乎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本書(shū)收入的《散步》版本是寫于1917年年初的單行本**版,是一部中篇小說(shuō),也有人把它歸類為散文。 瓦爾澤的一生幾乎可以用“散步”兩個(gè)字來(lái)概括,這也是我將這部瓦爾澤文學(xué)作品集取名為《散步》的原因。因?yàn)橥郀枬傻奈膶W(xué)作品與“散步”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現(xiàn)長(zhǎng)途跋涉的漫游者,以陌生人的身份穿越陌生地帶,并且用漫游者的視角不斷去游戲文字、游戲文本,反諷作為作家的自身,其實(shí)這是瓦爾澤的一種詩(shī)學(xué)風(fēng)格。 阿爾卑斯山的冬天是雪的世界,瓦爾澤在寂靜的雪地里走著走著。他走過(guò)火車站,穿過(guò)一片樹(shù)林,走向那堆廢墟,那是他想去的地方。他一步一步向廢墟走去,步伐是穩(wěn)健的,他甚至沒(méi)有去扶一下路邊的欄桿,或許是怕碰落欄桿上潔白的積雪。忽然他身子一斜,仰面倒下,滑行了兩三米,不再起來(lái)。若干時(shí)間以后,雪地里的瓦爾澤被一只獵狗發(fā)覺(jué),接著是附近的農(nóng)民,然后是整個(gè)世界。 一、 “失而復(fù)得的兒子” 羅伯特??瓦爾澤于1878年4月15日出生在瑞士寧?kù)o的小城比爾,一個(gè)開(kāi)文具店的小商人家庭,他父親是虔誠(chéng)的新教徒,母親是溫柔麗質(zhì)的女性,多愁善感,患有抑郁癥,這可能是瓦爾澤家族的遺傳性疾病。1894年,瓦爾澤母親去世。根據(jù)瑞士日耳曼學(xué)者馬特(Peter von Matt)的研究,瓦爾澤對(duì)其母親的依賴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瓦爾澤在八個(gè)孩子中排行第七,總想從終日操勞的母親和不茍言笑的父親那兒多得到一點(diǎn)愛(ài),然而父母似乎并不偏愛(ài)羅伯特??瓦爾澤,每當(dāng)兄弟姐妹中有誰(shuí)病了,都能得到母親加倍的疼愛(ài),羅伯特卻從不生病,因而得不到那份特殊的憐愛(ài),心里總覺(jué)得父母有點(diǎn)嫌棄他。 “夏日的一天,一個(gè)小男孩決計(jì)試探一下父母對(duì)他的愛(ài)心,他獨(dú)自來(lái)到池塘邊,脫光衣褲,將它們掛在池塘邊的小樹(shù)上,將小涼帽扔進(jìn)池塘,自己卻爬上高高的菩提樹(shù),一會(huì)兒男孩的姐妹們來(lái)池塘邊玩耍,看見(jiàn)這一情形,誤以為男孩已溺水而亡,大聲哭喊,哭報(bào)母親,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父母悲痛之極,悔恨未給兒子多一點(diǎn)愛(ài)憐,若再給一次機(jī)會(huì),一定加倍疼愛(ài)失去的兒子。男孩在菩提樹(shù)上看清了這一切,便下得樹(shù)來(lái),躺在池塘邊上,望著藍(lán)天白云,遐想回到母親懷抱里的溫暖。傍晚時(shí)分,男孩回到家中,全家人喜出望外,失而復(fù)得的兒子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寵愛(ài)……” 然而這個(gè)故事并非真人實(shí)事,而是瓦爾澤十五歲時(shí)寫下的**篇習(xí)作中的情節(jié),瓦爾澤將它取名為《池塘??小景》。“失而復(fù)得的兒子”的故事出自《新約全書(shū)》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有關(guān)失去的羔羊和失去的兒子的章節(jié),《圣經(jīng)》中描述了兩個(gè)兒子,小兒子從父親那兒要了他的那份財(cái)產(chǎn),出門遠(yuǎn)游,財(cái)盡囊空后回到家中,父親非但沒(méi)有責(zé)怪他,反而為他殺豬宰羊,盛情款待。大兒子從地里干活回來(lái),看到這一情景,憤憤不平,覺(jué)得他替兄弟盡了兒子的責(zé)任,卻從未得到過(guò)如此厚愛(ài)。父親勸大兒子,你一直在我身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你弟弟在我心目中已經(jīng)死去,失而復(fù)得的兒子怎能不讓人高興?在《圣經(jīng)》中這一故事是為建構(gòu)基督教倫理而服務(wù)的,在于肯定“浪子回頭”的價(jià)值。 瓦爾澤采用這一題材則不是復(fù)制《圣經(jīng)》所表述的公正和寬容,恰恰相反,瓦爾澤著意強(qiáng)調(diào)沒(méi)有失去的兒子同樣應(yīng)當(dāng)?shù)玫綈?ài)和公正。這一思想同樣體現(xiàn)在瓦爾澤日后創(chuàng)作的散文《失去的兒子的故事》之中。在這篇作品中,瓦爾澤完全采用《圣經(jīng)》的情節(jié),所不同的是瓦爾澤利用敘述者來(lái)表示自己強(qiáng)烈的傾向性,即對(duì)《圣經(jīng)》中的大兒子寄予同情。在《失去的兒子的故事》中,瓦爾澤將敘述重心移置到大兒子身上,在與失而復(fù)得的小兒子得寵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下更顯出應(yīng)得寵而未得寵的大兒子的不滿情緒。這便是瓦爾澤童年留下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與卡夫卡的父子情結(jié)十分相像。在德語(yǔ)文學(xué)研究中,瓦爾澤與卡夫卡文學(xué)風(fēng)格的脈絡(luò)關(guān)系已成定論。卡夫卡也曾寫過(guò)一篇取材于《圣經(jīng)》中失而復(fù)得的兒子的短文。德國(guó)文學(xué)理論家齊默曼(Hans Dieter Zimmermann)在20世紀(jì)80年代曾寫過(guò)《巴比倫的翻譯——論瓦爾澤和卡夫卡》一書(shū),對(duì)瓦爾澤和卡夫卡的作品進(jìn)行了細(xì)致地對(duì)比研究,齊默曼在這兩個(gè)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看到了瓦爾澤和卡夫卡的文學(xué)作品及人格中的相通之處,即將個(gè)人的主觀感受處理成人的普遍情感,在寫作文本的過(guò)程中完成從個(gè)別到一般的世界觀轉(zhuǎn)變。 1892年,瓦爾澤遵照父命前往比爾,去一家銀行當(dāng)學(xué)徒,但其實(shí)他內(nèi)心向往成為一名話劇演員,童年時(shí)他喜歡看比爾劇院時(shí)常上演的席勒不朽之作《強(qiáng)盜》,在席勒的戲劇中,瓦爾澤萌發(fā)了對(duì)文學(xué)的偏愛(ài)和對(duì)語(yǔ)言的敏銳感覺(jué)。1895年,瓦爾澤到了斯圖加特,想在那兒學(xué)藝當(dāng)演員,不過(guò)這一夢(mèng)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生性內(nèi)向的瓦爾澤不得不承認(rèn)自己并不具備表演才華。1896年,瓦爾澤正式受蘇黎世一家保險(xiǎn)公司聘用。不久,他轉(zhuǎn)入一家銀行當(dāng)職員。這期間瓦爾澤開(kāi)始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1897至1898年間寫下的詩(shī)歌《在辦公室》就是他當(dāng)時(shí)生活的寫照,詩(shī)中“月亮是黑夜的傷口/鮮血滴滴竟是滿天星星”膾炙人口。 起初,瓦爾澤只是在伯爾尼的《聯(lián)盟日?qǐng)?bào)》和慕尼黑著名文學(xué)雜志《島嶼》上發(fā)表一些散文、小品文和詩(shī)歌,后來(lái)這些作品分別于1904年和1909年被收入《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和《詩(shī)歌集》中出版。盡管當(dāng)時(shí)瓦爾澤初出茅廬,但其文學(xué)才華得到著名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如維德曼(Joseph Victor Widmann)和布萊(Franz Blei)等的青睞,不過(guò)此時(shí)他只是區(qū)區(qū)一名文學(xué)青年,并未得到大多數(shù)讀者和圖書(shū)商的重視。在此期間,瓦爾澤結(jié)識(shí)了維德金德(Franz Wedekind)、道騰代(Max Dauthendey)、比爾鮑姆(Otto Julius Bierbaum)等青年維也納圈子里的作家,這讓他直接體驗(yàn)到了維也納現(xiàn)代派的文學(xué)價(jià)值取向。 事業(yè)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落魄幾乎伴隨著瓦爾澤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生涯。直到日后瓦爾澤成為職業(yè)作家,他仍然被這種失意感困擾。這也許與他的生不逢時(shí)有關(guān),因?yàn)橥瑫r(shí)期的瑞士作家黑塞無(wú)論在名望和成就上都蓋過(guò)了他,瓦爾澤無(wú)法走出黑塞的陰影。1904年,在瓦爾澤的《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出版的同時(shí),黑塞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彼得??卡門青》(一譯《鄉(xiāng)愁》),盡管黑塞一生非常推崇瓦爾澤,并于1917年在《新蘇黎世日?qǐng)?bào)》上大聲疾呼:“假如像瓦爾澤那樣的詩(shī)人加入我們時(shí)代的精英中來(lái),那就不會(huì)有戰(zhàn)爭(zhēng),假如瓦爾澤擁有千萬(wàn)名讀者,世界就會(huì)安寧得多。”而事實(shí)上黑塞已是當(dāng)時(shí)德語(yǔ)文壇的新星,成了蘇黎世文學(xué)沙龍里文人雅士高談闊論的中心。相比之下,瓦爾澤新銳的文學(xué)則顯得黯然失色。1943年,瓦爾澤回憶當(dāng)時(shí)的情形時(shí)說(shuō):“蘇黎世的讀者根本沒(méi)有將我的作品放在眼里,他們狂熱地追隨黑塞,把我看得一錢不值。” 瓦爾澤抱怨蘇黎世讀者的狹隘,批評(píng)他們只接受黑塞的一種文學(xué)方式,排斥其他風(fēng)格。當(dāng)時(shí)甚至有一位女演員買了一本《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寄還給瓦爾澤,上面寫了“要寫書(shū)先學(xué)學(xué)德語(yǔ)”之類的譏諷。這也許正好說(shuō)明了瓦爾澤文學(xué)作品的超時(shí)代性,猶如處在康定斯基所說(shuō)的藝術(shù)金字塔的**,它只有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方能被后來(lái)者所理解。 二、 主仆關(guān)系 1903年至1904年間,瓦爾澤前往蘇黎世近郊威登斯維爾一個(gè)叫卡爾??杜布勒的工程師和發(fā)明家事務(wù)所當(dāng)幫工,但不久這家事務(wù)所就倒閉了。接著的一段時(shí)間,瓦爾澤在蘇黎世的一個(gè)猶太貴夫人家中當(dāng)侍者,這段經(jīng)歷成了他日后撰寫《助手》《唐納兄妹》等作品的素材。1906年,他應(yīng)在柏林的哥哥卡爾??瓦爾澤之邀來(lái)到德意志帝國(guó)首都柏林。卡爾當(dāng)時(shí)已是柏林小有名氣的畫(huà)家,專門為一些書(shū)報(bào)雜志畫(huà)插圖和舞臺(tái)布景。卡爾有意讓弟弟前來(lái)帝國(guó)首都,接受世紀(jì)風(fēng)的熏陶。在那里,瓦爾澤曾短期在柏林分離派(Berliner Secession)藝術(shù)家協(xié)會(huì)當(dāng)秘書(shū),并有機(jī)會(huì)結(jié)識(shí)著名的出版商費(fèi)舍爾(Samuel Fischer)和卡西爾(Bruno Cassirer)。然而,在柏林的那些日子里,瓦爾澤似乎是局外人,他深居簡(jiǎn)出,出版的三部小說(shuō)并沒(méi)有獲得期待中的巨大成功,因此生活上逐漸捉襟見(jiàn)肘,主要靠卡爾的接濟(jì)度日。不過(guò),他的作品雖然沒(méi)有被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讀者接受,但獲得文學(xué)界精英人物如穆齊爾、圖霍夫斯基的高度肯定。黑塞和卡夫卡甚至將瓦爾澤視為自己*喜愛(ài)的作家之一。據(jù)說(shuō)瓦爾澤在此期間不時(shí)受到一位女富豪的資助,在瓦爾澤的傳記中,這位女富豪一直是個(gè)謎,我們無(wú)從了解她的姓名、生平以及她與瓦爾澤的關(guān)系。 1905年9月,瓦爾澤曾在柏林的一家仆人學(xué)校接受侍者訓(xùn)練,接著他又在上西里西亞的一個(gè)貴族宮殿里當(dāng)過(guò)三個(gè)月的服務(wù)生。這段經(jīng)歷日后出現(xiàn)在他多部文學(xué)作品中,本書(shū)收入的作品《西蒙》《托波特》都是反映主仆關(guān)系的名篇,謙虛和謙卑是瓦爾澤作品的一貫風(fēng)格,這種風(fēng)格在長(zhǎng)篇日記體小說(shuō)《雅各布??馮??貢騰》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這部小說(shuō)中,“現(xiàn)實(shí)世界”蛻變成令人無(wú)法把握和理解的巨大怪物,這個(gè)巨大的怪物則是由讀者耳熟能詳?shù)娜粘I瞵嵤陆?gòu)而成,但恰恰因此而變成一個(gè)個(gè)難解的謎團(tuán)。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也有同樣的功能,這樣看來(lái),卡夫卡特別喜歡瓦爾澤這個(gè)時(shí)期的作品也就不難理解了。1913年,瓦爾澤因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的失落和接濟(jì)他的女富豪去世而離開(kāi)柏林,這樣瓦爾澤在柏林前后共生活了七年。這七年是瓦爾澤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重要時(shí)期,其間他先后寫下了三部著名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幫手》《唐納兄妹》和《雅各布??馮??貢滕》,史稱“柏林三部曲”。這三部小說(shuō)當(dāng)年均在布魯諾??卡西爾出版社得以出版,責(zé)任編輯為文學(xué)評(píng)論家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in)。 除了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之外,瓦爾澤在柏林期間還寫下了許多小品文,在這些小品文中,瓦爾澤不僅游戲語(yǔ)言,而且還塑造了“閑逛者”角色。他從閑逛者視角出發(fā),描寫了許多柏林大眾聚集地場(chǎng)景,如柏林著名的站立式啤酒廣場(chǎng)“阿欣格爾”、游藝場(chǎng)等。值得一提的是,瓦爾澤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和小品文在出版之前均發(fā)表在當(dāng)時(shí)著名的文學(xué)刊物上,或者在這些刊物上連載,如專門刊登話劇劇本和批評(píng)的文學(xué)周刊《大舞臺(tái)》、歐洲*古老的文學(xué)雜志《新觀察》《未來(lái)》、文藝月刊《萊茵大地》,以及《新蘇黎世日?qǐng)?bào)》和魏瑪共和國(guó)時(shí)期重要的文學(xué)刊物《新墨丘利》等。 “柏林三部曲”的共同特點(diǎn)表現(xiàn)在自傳性上,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瓦爾澤三次當(dāng)仆人和打零工、做幫工的經(jīng)歷。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部小說(shuō)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主仆關(guān)系,主人公都是以小人物的身份出現(xiàn)的,與塞萬(wàn)提斯《堂吉訶德》中的主仆關(guān)系不同,在瓦爾澤的作品中,主仆關(guān)系是一種辯證的生活觀,它客觀地反映了瓦爾澤的人生價(jià)值取向。 從表面上看,瓦爾澤文學(xué)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很多都是任人支使的仆人,仆人的職業(yè)規(guī)范便是絕對(duì)地服從,然而對(duì)瓦爾澤小說(shuō)人物的理解不應(yīng)停留在這個(gè)表象上。首先,瓦爾澤的主仆關(guān)系可以從宗教層面來(lái)理解,瓦爾澤是新教徒,他反對(duì)將上帝偶像化,反對(duì)教會(huì)對(duì)宗教的教條化,反對(duì)教堂取代宗教的傾向。在他看來(lái),無(wú)論是受支使的人,還是支使人的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其次,從哲學(xué)辯證法的角度來(lái)看,主仆的關(guān)系是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就像黑格爾說(shuō)的那樣,主與仆是相互依賴的。在自然界,人戰(zhàn)勝自然的主人力量的同時(shí)又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顯得蒼白無(wú)力。再者,從社會(huì)心理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主仆雖然是一種社會(huì)關(guān)系,是一定的社會(huì)存在對(duì)個(gè)體在群體中的社會(huì)位置的限定,但是在心理上主仆關(guān)系往往具有逆向性。這三點(diǎn)在瓦爾澤柏林時(shí)期的三部小說(shuō)中是顯而易見(jiàn)的。 三、 巨大的小世界 “國(guó)王其實(shí)是叫花子,叫花子有時(shí)勝過(guò)國(guó)王。”瓦爾澤曾想在戲劇舞臺(tái)上將這一思想傳遞給貪得無(wú)厭的世人。然而,他在1913年3月回到比爾后親自實(shí)踐了這一辯證法。他在比爾一家名叫“藍(lán)十字”的簡(jiǎn)陋旅館里租了一間房,在那兒度過(guò)了七年時(shí)間。在**次世界大戰(zhàn)中,瓦爾澤在柏林存下的一些錢變成了一堆廢紙,這時(shí)他只能寫些小文章維持生計(jì)。 1914年夏天,瓦爾澤以萊茵河地區(qū)婦女聯(lián)合會(huì)的名義出版了《散文集》,因而獲得婦女聯(lián)合會(huì)的萊茵河地區(qū)優(yōu)秀文學(xué)家獎(jiǎng)。但這筆錢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只是杯水車薪,他很快又陷入窘迫的境地。冬天他竟無(wú)錢買煤取暖,只能穿上自己用舊衣服縫制的棉鞋,身上緊緊地裹著1914年秋天在軍隊(duì)服役時(shí)穿過(guò)的舊軍大衣,才能得以繼續(xù)寫作。當(dāng)沉浸在文字和想象中時(shí),瓦爾澤充分地得到了人生的滿足。或許他在生活的陰影中得到的比在光明中得到的更多,就像他自己說(shuō)的那樣,在柏林的仆人學(xué)校,他不只是學(xué)會(huì)了“如何清洗地毯,如何打掃衣櫥,如何將銀器擦拭得錚亮,如何接主人的禮帽和大衣,而更多的是學(xué)會(huì)了將自我變得非常渺小”。 將自我變得渺小不僅是瓦爾澤作品中的靈魂,同時(shí)也是瓦爾澤一生的生活準(zhǔn)則。對(duì)于他來(lái)說(shuō),放棄功名便是一種功名,然而當(dāng)他不得不扮演叫花子的“角色”時(shí),他并沒(méi)有像國(guó)王那樣瀟灑。在這段時(shí)間里,他常常為了一塊面包、一塊奶酪或一塊黃油向女友梅爾美特(Frieda Mermet)低三下四地乞討。1914年年初,瓦爾澤的父親去世,接著他的兩個(gè)兄弟接連死去,一個(gè)死于精神病,另一個(gè)也因抑郁癥自殺身亡。在柏林的哥哥卡爾與瓦爾澤關(guān)系一向不錯(cuò),在柏林時(shí)曾給瓦爾澤的許多散文集和小說(shuō)畫(huà)過(guò)封面和插圖,兩人在20世紀(jì)初的柏林分離派舞臺(tái)上曾熱鬧過(guò)一陣,不過(guò)卡爾婚后與弟弟的關(guān)系日漸疏遠(yuǎn),其原因是卡爾的妻子總是瞧不起這個(gè)不中用的窮弟弟。隨著卡爾的聲名鵲起,他們兄弟之間關(guān)系也終于破裂。 1920年11月,瓦爾澤收到蘇黎世一個(gè)名叫“讀書(shū)俱樂(lè)部”的文學(xué)團(tuán)體的邀請(qǐng),請(qǐng)他前去朗讀文學(xué)作品。盡管瓦爾澤深知自己不善辭令、樸訥誠(chéng)篤,一想到要在大庭廣眾下大聲朗讀自己的作品就覺(jué)得舌頭發(fā)麻,但他還是答應(yīng)了下來(lái)。畢竟蘇黎世是他初出茅廬的地方,在那兒他開(kāi)始了自己的飄浮生涯和只顧播種、不計(jì)收獲的文學(xué)耕耘。那兒有他一段美好的回憶。然而,這個(gè)決定似乎是一個(gè)命中注定的錯(cuò)誤。瓦爾澤清楚地知道,在文學(xué)已經(jīng)成為消費(fèi)商品的現(xiàn)代社會(huì),這些商品的制作者若要成功,就必須具備敢在大庭廣眾之下脫下褲子,并且有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本領(lǐng),因?yàn)槭紫戎廊绾问圪u自己的人,才是能售賣自己產(chǎn)品的人,但這不是瓦爾澤的特長(zhǎng)。 阿爾卑斯山的初冬早已是一片白雪茫茫,瓦爾澤帶著幾頁(yè)詩(shī)歌和小品文手稿上路了。和往常一樣,他喜歡在雪地里漫游。經(jīng)過(guò)幾天的長(zhǎng)途跋涉,瓦爾澤來(lái)到了蘇黎世。在朗讀會(huì)之前,他反復(fù)地練習(xí),朗讀自己那些其實(shí)不太適宜大聲朗讀的文字,瓦爾澤的文學(xué)文本似乎只能輕輕地吟誦,細(xì)細(xì)地品味。一旦經(jīng)人大聲朗讀,那些蘊(yùn)藏在字里行間的趣味便會(huì)蕩然無(wú)存。不過(guò)現(xiàn)在一切都太晚了,朗讀會(huì)的主持人找到瓦爾澤,請(qǐng)他試讀一番,試讀的結(jié)果叫人失望。瓦爾澤根本不具備人們想象中的朗讀才華,經(jīng)過(guò)一番爭(zhēng)論后,主持人仍然決定由別人來(lái)替瓦爾澤朗讀。瓦爾澤出于酬金的原因,只得委曲求全。朗讀會(huì)的那天晚上,臺(tái)上宣布瓦爾澤因病不能出席朗讀會(huì),而事實(shí)上,瓦爾澤像一名普通聽(tīng)眾那樣,坐在下面和其他聽(tīng)眾一起為自己鼓掌。 四、 “捉迷藏” 對(duì)于瓦爾澤來(lái)說(shuō),寫作具有雙重意義,即在用語(yǔ)言表達(dá)的同時(shí),在語(yǔ)言中隱藏所要表達(dá)的東西。但是這種隱藏是一種類似兒童捉迷藏游戲,隱藏的目的*終是為了被尋找、被發(fā)現(xiàn)。因此,談?wù)搶懽鳌⒄務(wù)撟骷乙彩峭郀枬傻奈膶W(xué)特色之一。本書(shū)收入的《有關(guān)寫作》《意大利小說(shuō)》《微微的敬意》等都屬于這一類。可以說(shuō),瓦爾澤慣于將自我隱藏在語(yǔ)言的森林之中。瓦爾澤擅長(zhǎng)在那種不緊不慢、娓娓道來(lái)的節(jié)奏中,在紛亂無(wú)序的幻覺(jué)和夢(mèng)境中,在有悖常理的荒誕不經(jīng)中,在掩蓋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的“浪漫主義反諷”中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文學(xué)價(jià)值觀,《雅各布??馮??貢滕》《散步》《西蒙》等作品便是瓦爾澤運(yùn)用“浪漫主義反諷”的典型例子。《雅各布??馮??貢滕》這部日記小說(shuō)可以說(shuō)是瓦爾澤的人生價(jià)值觀的自白,不過(guò)這個(gè)自白只是被“浪漫主義反諷”的外套裹住,不輕易被人察覺(jué)罷了。 …… …… 五、 融入白雪 1933年,游戲終于結(jié)束了。瓦爾澤不再繼續(xù)在語(yǔ)言的森林中玩“捉迷藏”了,而是轉(zhuǎn)入故鄉(xiāng)比爾的赫利薩精神病院。根據(jù)瑞士法律,像瓦爾澤那樣的窮人,醫(yī)療福利由原籍所在地政府負(fù)擔(dān),這樣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盡管赫里薩精神病療養(yǎng)院院長(zhǎng)辛利希森(Otto Hinrichsen)也是一名作家,他給瓦爾澤專門提供了一間寫作室,讓他可以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但瓦爾澤仍然放棄了寫作。他說(shuō)自己不是來(lái)這里寫書(shū)的,而是來(lái)發(fā)瘋的,要寫書(shū)就不來(lái)這里了。瓦爾澤過(guò)著平靜的生活,一種在生活的世界大門外面的生活。每天上午幫助打掃衛(wèi)生,下午做一些折錫箔紙、糊紙袋信封之類的手工勞動(dòng)。由于放棄了文學(xué)寫作,他已斷絕了一切經(jīng)濟(jì)來(lái)源,只能吃病院里*低檔的伙食,但他除了有幾次自殺的念頭外,對(duì)生活沒(méi)有任何苛求,就像他在小品文中寫過(guò)的那樣,人就這么活下去。文壇上對(duì)他的作品的褒貶揚(yáng)抑對(duì)他已經(jīng)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對(duì)于他來(lái)說(shuō),寫字的瓦爾澤已不復(fù)存在,對(duì)一個(gè)不存在的人的評(píng)價(jià)又有什么實(shí)際價(jià)值呢?瓦爾澤漸漸地被人遺忘了。 只有一個(gè)人從1936年起開(kāi)始尋找瓦爾澤的真實(shí)價(jià)值,并一直陪伴著瓦爾澤走完生命的旅途。他便是瑞士出版家、作家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卡爾??塞里希(Carl Seelig)。塞里希定期去赫利薩精神病院看望瓦爾澤,與他一起散步交談,日后發(fā)表了著名的日記《與羅伯特??瓦爾澤一起漫步》,書(shū)中記載了他與瓦爾澤持續(xù)了二十年的談話。在那漫長(zhǎng)的散步途中,塞里希走入了久已沉默的詩(shī)人瓦爾澤的內(nèi)心,瓦爾澤重新開(kāi)始傾吐對(duì)人生和文學(xué)的真知灼見(jiàn)。盡管瓦爾澤看上去是個(gè)患精神分裂癥的病人,西服的紐扣常常扣錯(cuò),但他的思維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正常的。塞里希為了使瓦爾澤的生活能得到一些改善,積極奔走,為他出版了散文集《巨大的小世界》,并在德語(yǔ)文學(xué)界到處征集捐款。黑塞領(lǐng)導(dǎo)的瑞士作家協(xié)會(huì)也撥款資助,這樣才使瓦爾澤避免了因交不起精神病院的飯錢而被驅(qū)到貧民救濟(jì)院去的命運(yùn)。瓦爾澤的姐姐麗莎于1944年去世后,塞里希便正式成為瓦爾澤的監(jiān)護(hù)人并獲得了一部分原在麗莎手中的手稿。瓦爾澤去世后,精神病院將瓦爾澤的遺物轉(zhuǎn)交給了塞里希,那是一只舊皮鞋盒,里面裝著五百二十六張寫滿密密麻麻鉛筆小字的手稿,這些鉛筆手稿上的字跡小的不到1毫米,大的也只有1至2毫米,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手稿竟全部是寫在一些廢紙上,如車票、日歷、明信片、卷煙殼等。1944年至1953年,塞里希整理、收集了瓦爾澤部分可辨認(rèn)的手稿和散見(jiàn)于報(bào)紙、刊物的作品,編輯出版了瓦爾澤《詩(shī)歌與散文》(五卷本),但塞里希認(rèn)為,瓦爾澤的大多數(shù)手稿是精神病人的涂鴉,無(wú)法解讀。青年學(xué)者格萊文博士(Jochen Greven)則認(rèn)為,瓦爾澤的手稿是一種特殊的書(shū)寫方式,完全可以釋讀。格萊文與塞里希在瓦爾澤的遺稿問(wèn)題上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并為此而對(duì)簿公堂。 1960年塞里希死于車禍,在瑞士羅伯特??瓦爾澤基金會(huì)的支持下,格萊文開(kāi)始瓦爾澤密碼般的手稿研究和作品出版工作。在1966年至1975年期間,格萊文解讀并編撰出版的二十卷《瓦爾澤全集》震驚了歐美文學(xué)界,特別是在1985年至2000年的十五年里,瑞士瓦爾澤檔案館的埃希特(Berhard Echte)和毛朗(Werner Morlang)解碼并編撰出版了六卷本《來(lái)自鉛筆領(lǐng)域》。瓦爾澤的這些手稿原件時(shí)隔半個(gè)多世紀(jì)重見(jiàn)天日,再次震驚了歐美文學(xué)界,也震驚了歐美知識(shí)界。 自2008年起,由瑞士國(guó)家基金會(huì)支持的6部48卷的《羅伯特??瓦爾澤全集》(學(xué)術(shù)版KWA)編撰工作正在積極推進(jìn)之中,其中已有20卷問(wèn)世。此項(xiàng)瑞士國(guó)家工程計(jì)劃將囊括羅伯特??瓦爾澤的全部已發(fā)表的和歷年新發(fā)現(xiàn)的文學(xué)作品、手稿(原件圖像復(fù)制)、日記、書(shū)信以及其他文獻(xiàn),并以數(shù)碼電子和紙質(zhì)書(shū)籍兩種方式奉獻(xiàn)給全世界讀者。中國(guó)的瓦爾澤翻譯則尚未真正起步,2002年我翻譯了這個(gè)集子,這次再版又增添了若干篇小品文和瓦爾特??本雅明關(guān)于瓦爾澤的一篇文學(xué)評(píng)論文章,希望本書(shū)的再版能為羅伯特??瓦爾澤在中國(guó)的傳播略盡綿薄之力。
德國(guó)文學(xué)散論 作者簡(jiǎn)介
范捷平 二級(jí)教授,浙江大學(xué)德國(guó)文化研究所所長(zhǎng),博士生導(dǎo)師,浙江省翻譯協(xi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廈門大學(xué)講座教授。出版學(xué)術(shù)著作、教材、譯著30余種,發(fā)表國(guó)際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論文70余篇。2012年榮獲德國(guó)柏林工業(yè)大學(xué)杰出貢獻(xiàn)銀質(zhì)獎(jiǎng)?wù)隆U軐W(xué)譯著《過(guò)時(shí)的人》(第一、第二卷)獲浙江省第16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優(yōu)秀成果獎(jiǎng)二等獎(jiǎng),學(xué)術(shù)代表作《羅伯特·瓦爾澤與主體話語(yǔ)批評(píng)》獲浙江省第17屆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優(yōu)秀成果獎(jiǎng)一等獎(jiǎng)。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姑媽的寶刀
- >
回憶愛(ài)瑪儂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cè)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shū)
- >
中國(guó)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xué)概述
- >
中國(guó)歷史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