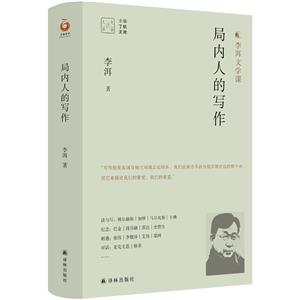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大家讀大家系列:局內人的寫作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87079
- 條形碼:9787544787079 ; 978-7-5447-8707-9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家讀大家系列:局內人的寫作 本書特色
1.李洱親選文學講稿,文學觀、創作觀的一次集中呈現 “我講述了我對人與事、文學與時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樣的一些看法,決定了我為什么會寫出那些作品,也決定了作品的成功與失敗。” 2.一堂高水準的經典文學閱讀課。不論東方與東方,還是東方與西方之間,不論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多少不同,仍然能夠互相欣賞彼此間文化的差異 博爾赫斯、加繆、馬爾克斯、卡佛、巴金、錢谷融、雷達、史鐵生、張煒、李敬澤、格非、艾偉、梁鴻……李洱說,“我的看法還是應該讀經典,一部書在成為經典的過程中,這本書原有的諸多意義上,又被不同的解釋賦予了更多的意義。這本書已經不屬于作者本人了,囊括、吸納了更多人的智慧。” 3.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大家讀大家”第四輯作品之一:鐵凝、閻連科、格非、李洱、邱華棟,重量級作家陣容的文學鑒賞課 “大家讀大家”是知名人文大家為大眾撰寫的一套介紹文化大家及經典名著的導讀性通識讀物。叢書第四輯收錄作品五部,鐵凝《隱匿的大師》、閻連科《作家們的作家》、格非《文明的邊界》、李洱《局內人的寫作》、邱華棟《大師創作的世界》,這是一套國內重量級作家陣容的文學鑒賞課,他們首度公開私人書單,學理與趣味兼備,知人與說文結合,“大家們”抽絲剝繭,與“大家”分享他們的閱讀心路、文學歷程。
大家讀大家系列:局內人的寫作 內容簡介
《局內人的寫作》是李洱的文學閱讀筆記。全書分五輯:“讀與寫”談論博爾赫斯、加繆、卡佛等對當代文學的啟迪;“紀念”追憶巴金、錢谷融、雷達、史鐵生等已故名家的文學成就;“相遇”回溯與張煒、格非、梁鴻等當代作家的交往;“由作品說開去”從《紅樓夢》等典型文本出發,探討文學的藝術性、道德感、價值觀等基本問題;“對話”是作者與學者、評論家、媒體記者的對談實錄。“我講述了我對人與事、文學與時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樣的一些看法,決定了我為什么會寫出那些作品,也決定了作品的成功與失敗。”本書是作者文學觀、創作觀的一次集中呈現,也是一堂高水準的經典文學閱讀課。
大家讀大家系列:局內人的寫作 目錄
局內人的寫作——讀加繆
它來到我們中間尋找騎手
博爾赫斯的意義
卡佛的玫瑰與香檳
文學的本土性與交流
——在中德作家論壇上的演講
輯二 紀念
巴金的提醒
生前是傳奇,身后是傳說——記錢谷融先生
作為一個讀者紀念史鐵生
——史鐵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活動上的發言
送別雷達
輯三 相遇
高眼慈心李敬澤
說格非——在格非創作三十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漢語寫作的榮幸——談張煒
梁鴻之鴻
說艾偉
輯四 由作品說開去
賈寶玉長大之后怎么辦
小說家的道德承諾——讀張大春《小說稗類》
讀《朝霞》
時間、語言、舌頭、價值觀與寫作
——在徐兆壽長篇小說《鳩摩羅什》研討會
上的發言
為什么寫,寫什么,怎么寫
——二○○五年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講壇”上的演講
先鋒小說與“羊雙腸”
輯五 對話
現代寫作與中國傳統——與作家格非對話
大眾媒體時代的虛構敘事
——與麥克尤恩、格非對話
文學是一種義務性的工作——答阿倫
寫作可以讓每個人變成知識分子——答傅小平
知言行三者統一,是我的一個期許——答舒晉瑜
大家讀大家系列:局內人的寫作 節選
局內人的寫作 ——讀加繆 今年早些時候,我又重讀了加繆的《局外人》。因為寫作一篇小說的緣故,這次我*關心的是作者的肺病和寫作的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肺結核一直是文學的潛在主題。從來沒有哪種疾病像肺結核那樣和文學那么親近,它活像文學的結發妻子和情人。用一枚書簽隨意挑開世界文學史脆黃的冊頁,我們幾乎都能從中看到結核病患者那艷若桃花的形象。我沒有說出“癆病鬼”這個詞,是因為考慮到魯迅、郁達夫、瞿秋白、盧梭、卡夫卡、契訶夫、加繆等人都屬于結核病一族;而托馬斯.·.曼筆下的肺病患者的集散地魔山風景宜人,小仲馬的茶花女和曹雪芹的林黛玉,都能使人茶飯不思。如果我說沒有肺結核,整個世界文學史就得重寫,這話似乎并不為過。看來,決定世界文學史目前格局的,與其說是文學大師的辛勞,倒不如說是由于小小的結核病菌的過于勤勉。結核病患者臉上的紅云,就是文學天空中的朝霞和夕陽。 加繆**次被發現患有肺病是在一九三○年,其右肺呈現干酪樣結核。在對結核病癥狀的描述上,除了經常提到的咳嗽和咯血令人感到不適之外,所用的詞語大都帶著某種優雅、溫暖的氣質,此處的“干酪”一詞就是個例證。那年他十七歲,是哲學班的學生,兼一支業余足球隊的守門員。檢查出其肺病的是一家貧民區醫院,這與肺病發生的境況相適宜,因為肺病的發生通常與貧窮聯系在一起,就像現在的艾滋病總是被人看成飽暖思淫欲的后果。它使加繆**次體驗到了荒謬——生命的大幕剛剛拉開,死神就降臨了。是的,在青霉素出現之前,肺病就是一種不治之癥。你無法求助于醫生,因為醫生只能給你帶來更為致命的疾病:膽怯、懦弱、輕信和對死亡的恐懼。《圣經.·.申命記》里說,在形形色色的疾病中,上帝曾挑選肺結核來懲罰人類,可見其功效等同于洪水。在早于《局外人》寫成的《婚禮》一書中,加繆寫道,一個年輕人“還不曾琢磨過死亡和虛空,但他卻品嘗到了它所帶來的可怖的滋味”,“沒有比疾病更可鄙的事物了,這是對付死亡的良藥,它為死亡做著準備。它創造了一種見習過程,在這個見習階段要學會自我憐憫。它支持著人為擺脫必死的命運所做的努力”。從他*早的言談中,我或可聽到與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相似的聲音。四年之后,結核病菌再次光顧新婚不久的加繆的左肺。如果說加繆以前的自我療養等同于西緒弗斯推巨石上山的話,那么此刻,巨石再次從山頂滾了下來,那些散亂的碎石子像結核病菌一樣四下飛竄。 在蘇珊.·.桑塔格所著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她引證《牛津英語詞典》說明,肺結核的同義詞即“耗損”:血量減少,緊接著是耗損和銷蝕。詞源學表明,肺結核曾被認為是一種反常的擠壓,“結核”一詞源于拉丁文tuberculum,即小詞綴tuber(隆起、脹起)。“耗損”一詞給人一種慢死的假象,它使得病人在時間的流程中不得不接受這種命運的安排,并不斷滋生求生的欲望。我可以理解鼓脹所帶給人的那種硬塊的感覺,它在無限的虛空中凝聚為一種堅硬和柔軟相并存的存在經驗,有如一塊霉變著的麥芽糖。一九三七年,即加繆開始構思并寫作《局外人》的那一年的八月,他作為巴黎的一名局外人來到了巴黎。他對巴黎的印象似乎是美好的:“這里充滿溫情,感動人心。貓,孩子們,還有悠閑的市民。到處都是灰色,天空亦如此。那一排排的石頭建筑,那些隨處可見的水塘。”到了一九四○年,即《局外人》完稿的那一年,當他來到巴黎謀生的時候,同樣的景色卻在他的筆下換了個模樣:“巴黎像是雨中的一團巨大的霧氣,大地上鼓起不成形的灰包。”成團的霧氣和鼓起的灰包,與其說是陽光被云層阻隔的結果,毋寧說是結核病力量的對象化。在托爾斯泰著名的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中,腎走游帶給官場中主人公伊凡.·.伊里奇一種疑懼體驗,他仿佛能摸到它走游時的步履:“他竭力在想象中捕捉這個腎臟,不讓它游走,把它固定下來。”而在《局外人》中,因為作者病體的緣故,我們也可時時感受到主人公默爾索——這個名字的發音給人一種沉寂的感覺,又像水洗布一樣爽凈、堅實、耐臟——那種像水淹螞蟻窩式的絕望和慢吞吞的死亡,之所以慢吞吞地死去,是為了在沉默中驗明自身的真實處境。 在多種不治之癥中,肺結核是少有的可以讓病人知道其病情發展的疾病之一。在《魔山》里,托馬斯.·.曼的病人們口袋里裝著X光玻璃照片,在風景宜人的療養院里,談情說愛,一邊消磨時間,一邊討論時間的玄妙,并在隆冬時分賞雪,看著雪地里的太陽怎樣如同一個荏弱的煙球(它形似加繆筆下騰空而起的灰包),雖給難以辨認的萬物的景色添上了一抹生機,但其中也夾雜著朦朧的、幽靈似的色彩。結核病患者大都先是清醒地活著,然后清醒地死去。他們可從咯血、咳嗽、虛弱的程度上,約略知道自己病情的狀況。“久病成醫”這個詞用在結核病病人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默爾索的死就是久病之后的醫生的死。就像哮喘病人知道自己應該躲避花粉一樣,所有的結核病人都知道,自己的茍延殘喘有賴于躲開濕氣和污濁,在陽光照耀下丈量自己的身影,在魔山上多吸上幾口清新的空氣——當然,魯迅筆下的那個吃人血饅頭的華小栓是個例外。這樣做,仿佛是要以靈魂對付肉體,雖然靈魂必敗,但不妨一試。加繆終其一生都是地中海陽光的頌禱者,而卡夫卡只要身體稍有不適,一塊疥癬、一個雞眼、一只癤子,都會促成他的一次遠足,或者泛舟、游泳。作為醫學的門外漢,我不知道青霉素里面是否有陽光的因素,但我可以認定,陽光和清新的空氣確實為病人提供了*微弱的反抗力量,有如透過玻璃觀賞玫瑰的葉片在凋零的季節舒展的一瞬。但是一個人享受多少陽光,他就得忍受多少陰影。在這樣的背景下,患者和疾病的對抗雖然無力,卻又顯得莊嚴和神圣——以瀆神者名目出現的默爾索的反抗,同樣具有如此的性質。 我想再一次提到“玻璃”,事實上這是加繆在闡述荒謬時要用到的一個關鍵詞。加繆把那個X光玻璃照片從醫療儀器上取出,轉手就放進了《西緒弗斯神話》中,就像拿著一張IC卡接通了西緒弗斯的電話。在《西緒弗斯神話》中,加繆寫道:“一個人在玻璃隔板后面打電話,別人可以看到他的手勢,卻不明其意。人們不禁會自問,這個人為什么活著?”在薩特寫的那篇《論〈局外人〉》當中,薩特把這個與玻璃有關的動作挑了出來:“加繆的手法就在于此:在他所談及的人物和讀者之間,他插入了一層玻璃隔板。還有什么比玻璃隔板后面的人更荒誕呢?似乎,這層玻璃隔板任憑所有東西通過,它只擋住了一樣東西,即人的手勢的意義。有待做的就是選用玻璃隔板,而這便是局外人的意識。”但來源于X光照片的“玻璃隔板”還應該具備另外的意義。印在上面的圖像一目了然,同時又如水中的月亮、鏡中的花朵。它與其說是一種可以觸摸到的實物,不如說是一種可以觸摸到的精神現實。 事實上,肺結核給人的印象就是一種精神化的病癥。按照桑塔格的說法,癌癥可以發生于身體的任何器官,肺只是它賴以誕生的諸多土壤之一,這使它具有某種不便言及的特征。比如,前列腺癌、直腸癌、乳腺癌,至于新興的艾滋病,它首先使人聯想到生殖器官的病變。而肺病卻只產生于人的上半部,那里距心臟*近,就像心臟的孿生姐妹,離頭腦也不算太遠,而且咯出的血首先要染紅舌頭,使味蕾得以品嘗到它的滋味。說癌癥和艾滋病更多地給人一種僅僅是器官性疾病的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它們更加速效,就像疾病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百米賽跑,缺少足夠的時間流程。雖然肺結核還被人看成某種液體特征的疾病,用黏痰、虛汗、血來塑造自身形象,但和那兩種要命的病比起來,它頂多只算是時有間歇的噴泉,而它們卻要算是瀑布了。如果說癌癥是警句和格言,那么肺病就是小說和論文。據說,在英語和法語中,結核病都是“疾馳”的。但實際上,這個詞用于癌癥和艾滋病,可能更為合適。當一個人被宣布患上這兩種疾病的時候,死神其實已經擰住了你的耳朵。肺病對人卻稍微慷慨一些,它給人提供了較多的時間的土壤,使病人可以把它培育成精神的花圃——如果說癌癥是強扭的瓜,那么肺結核就是瓜熟蒂落。在這方面,卡夫卡在寫給情人密倫娜的信中,直接地說:“肺病,這只不過是精神病的漫溢而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卡夫卡寫道:“結核病的居所并不在肺部,舉例來說,就像世界大戰的起因并不在*后通牒一樣。”從嗓子眼里咯出的那一團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精神的蓓蕾。托馬斯.·.曼在《魔山》里,將結核病看成“被掩飾起來的愛情力量的宣示;疾病是一種變形的愛情”。說到愛情,許多作家曾經把*美麗的女性拉進結核病一族。茶花女的美貌使巴黎上層社會為之心曠神怡,林黛玉一皺起細眉,那個叫作賈寶玉的情種就把大觀園看成了迷宮,多年前看曹禺先生的《日出》,如果陳白露不出場,那段戲就可以略過不看。許多患有結核病的女性被寫得性感迷人,那尤物仿佛不是來自塵世,而是來自天國。作家對那些尤物的描寫,使人想到沙漠中的旅人對葡萄的想象,不光是酸的,而且還分外多汁,分外甜。她們每咳嗽一下,作家的胸脯都會隨著起伏;她們咯出的血絲還沒抵達素潔的手帕,作家的淚水就已經打濕了衣襟。這當中有多少自我憐憫的情愫在悄悄發酵,豈是批評家們所能夠說清的;萬千情愁,又怎忍交由那幾個概念去生搬硬套。當批評家批判那些交際花的奢靡生活的時候,作家本人盡管口頭上認同,但心里卻像挨著針扎。讓我們想一想現實生活中的林徽因的美吧,她的美使徐志摩神魂顛倒,并使一個邏輯學家金岳霖不合邏輯地終身未娶,其表現就像一個有潔癖的孩子摸過了糖果卻再也不愿洗手。只因為能與林徽因擦肩而過,我本人就愿意生活在那個年代。徐志摩愛戀的另一個女作家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也是結核病患者,她的早逝有如一縷青煙繞梁不絕。我曾看過加繆本人的一張照片,在草地、兒童的映襯下,那種男人的美能使好萊塢明星顯得愈加俗不可耐。觀看契訶夫本人的照片,你會發現隨著肺病的加深,痞子氣是怎樣一點點地消失,而美是怎樣一點點地從他的夾鼻眼鏡后面被培育起來的。在各種幽靈似的人物當中,如果選擇一個幽靈作為他們的形象大使,那么卡夫卡就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沒有哪些作家比肺病作家更清醒、更美、更復雜、更有魅力,也更難以捉摸的了。在這方面,抓鬮似的隨便拉來一個人都是現成的例子。所以,當紀德在《背德者》的題記中引用《詩篇》里的詩句,說“天主啊,我頌揚你,是你把我造就成如此卓異之人”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覺得他矯情,因為那實在是恰如其分。 默爾索就是《詩篇》中提到的“如此卓異之人”之一。他*后的獨白,是我讀到的*感人的篇章。他部分地實現了加繆的夢想:自由、反抗和激情。用加繆的話來說,“自由只有一種,與死亡攜手共赴純凈之境”。或許是因肺病作家*后都脫離了貧困,所以,他們筆下的主人公死時,大都與臟亂差無關,顯得體面優雅。耗損的結果是作者的身體像書籍一樣單薄,靈魂浸潤在那些文字之中,像穿花蛺蝶一樣飛出。蛺蝶的翅膀與他們的身體也有某種相似性:透明,輕盈,緋紅,像盛開在泉邊的花朵上的葉脈。結核病患者盧梭說:“死亡和疾病常常是美麗的,就像肺癆的紅光。”這樣一種將肺病美學化的言談,似乎要給人這樣一種荒謬的印象,即那時刻都會降臨的滅頂之災,帶給他們的倒像是某種令人欽羨的恩惠。 但是,輕松地談論肺病作家不能不說是一種罪過,因為這容易忽略殘酷而真實的另一面。肺病作家的作品首先是一種痛苦的質疑性表達。如果它呈現出來的是憂郁,那是因為作者獨上高樓之時,已將欄桿拍遍。如果它是一次慈航,那首先是苦海無邊,回頭無岸。如果主人公已經服罪,那是因為罪早已深入骨髓。如果有誰要反抗,那是因為西緒弗斯虛空的內心*需要石頭的重量。茶花女之所以夜夜笙歌,那是因為她內心舉目無親。 是的,我不想讓輕松的談論掩蓋住命運的傷口。這樣的傷口放到一個人身上,比如,放到卡夫卡《鄉村醫生》里面的那個少年的臀部,就“比碗口還要大”。那樣一個傷口之所以能夠出現在那個少年的臀部,是因為它首先出現在卡夫卡的肺葉。在一篇日記中,卡夫卡寫到了這個傷口:“如果真像你所斷言的,肺部的傷口是一個象征,傷口的象征,F. (菲利斯)是它的炎癥,辯護是它的深處,那么醫生的建議(光線,空氣,太陽,安靜)就也是象征了。正視這個象征吧。”我們從肺結核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創傷性記憶,以及各種復雜的悖論關系。魯迅終其一生都糾纏在激進與保守、遺忘與記憶、存在與虛妄、中心與邊緣的巨大旋渦之中,這當中的每一次選擇,都永劫不復地帶來更大的創傷性記憶。“目光雖有,卻無路可循;我們謂之路者,不過是彷徨而已。”如果誰對我說,這是魯迅的言論我肯定不會懷疑,但這話卻是摘自卡夫卡的《對罪愆、苦難、希望和真正道路的觀察》。當一只小獸從陽光下的雪地里走過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注意它留下的花朵般的蹄印,還應該注意到那蹄印中的血跡。默爾索(法文:Meursault)這個名字中的Meur與“謀殺”為同一詞根。這個名字是從加繆的另一篇小說《幸福的死亡》中的梅爾索變化而來的。而梅爾索(Mersault)這個名字又可分解為Mer(海)和sault,sault發音近似太陽。僅從名字上,我們就可以約略知道《局外人》的主題。在《局外人》中,有一個關于人和狗關系的段落,這個段落頗能表示小說是如何植根于某種創傷性記憶的:一個名叫薩拉瑪諾的老人一直在尋找他丟失的一條狗,在狗還很小的時候,老人像喂嬰兒似的拿著奶瓶給它喂奶,現在它丟掉了,老人的魂也就丟失了。這個老人年輕的時候,本來打算做話劇演員,這與加繆一生對話劇的癡迷是合拍的。小說用較大的篇幅來寫人與狗的關系,對加繆來說并不奇怪。加繆總是愿意擠出篇幅,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讓位給人與自然的關系,就像把秋收時的繁忙景象讓給秋后廣袤的原野。當他在人與人和人與狗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當然要選擇人與狗:“那一身漂亮的皮毛,真是天下無敵。”我上面曾提到,肺病患者總是喜歡陽光和清新的空氣,并說那是一種*微弱的反抗力量的源泉,但急于奔向陽光和空氣的舉動,在肺病患者那里其實首先是對創傷的注腳。加繆對陽光和沙灘,對物的描寫,與后來的法國新小說之間有著某種扯不斷的親緣關系。在《懷疑的時代》一文中,薩洛特在加繆的“客觀描寫”中,看到了復雜的心理因素:“加繆的境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李爾王被女兒中*失寵的那一個所收留的情景。他曾細致入微地設法鏟除這種‘心理剖析’(是嗎?李注),但它卻像黑麥草一樣到處生長。” 肺病因為拖時較長,所以*親近的人也容易產生厭倦情緒,如果患者是一位老人,那么床前無孝子幾乎是可以斷定的。患者是一位年輕人又會怎么樣呢?加繆在隨筆中曾經寫下他患病之后他母親的態度。雖然母親在見到他咯血之后,頓感不安,但她并沒有照料他,而是把他送到了舅舅那里。送是遣送,也是*早的流放。而當他們相遇的時候,“她便默不作聲,兩人面對面,絞盡腦汁找些話來說,有人告訴他(加繆)曾見她哭過,但是,他對此將信將疑。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不曾有責備她的想法。某種默契把他們聯系在一起了”。這樣的描寫,不能不使人想起《局外人》中的默爾索的奔喪。法官、神父可以指責默爾索的冷漠,但他們絕不會指責默爾索死去的母親。與卡夫卡的父與子之間的強烈沖突不同,加繆筆下的母與子,在沉默的時候其實帶著某種溫情:“當母親在家時,總是靜悄悄地望著我。”那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和解,而是認識到了存在的困境,以及解脫的不能。在《局外人》的結尾,默爾索在夜間醒來時,看見頭頂上滿天星斗,“我又聽到了郊區的聲音。夜晚的氣息,土地和鹽的氣息,清醒了我的頭腦……汽笛響了起來,它宣告有些人走進一個永遠不再和我有任何聯系的世界。很久以來,我又一次想起了母親”。想到母親臨死,他反而感到了解放,想重新過一種生活。如果說,卡夫卡的“父親”是某種權力、專制的象征物的話,那么,加繆卻寧愿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普通的倫理關系上來,并從那里表達他對世界的體認。我這樣說,似乎是要強調《局外人》的自傳因素。是的,又有誰能否認所有偉大的作品首先是作家的靈與肉的自傳。 “他的熱情之多一如他的苦難之大。”在講述西緒弗斯這個荒謬英雄的故事時,加繆這樣寫道。與推巨石上山的故事相比,我倒更喜歡發生在這個英雄身上的另一個小小的插曲,正是由于這個插曲,西緒弗斯才會去推那個巨石,他踏著沉重的步伐,永遠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自己的苦難——據說,作為凡人的西緒弗斯臨死的時候,決定考驗一下妻子對自己的愛情。他叫她把他的尸體扔到廣場上。西緒弗斯從冥間醒來,卻對妻子的順從感到惱火。于是他又再次來到人間,欲懲罰妻子。他又見到了溫暖的石頭、金色的沙灘、閃爍的海水,以及海灣那優美的曲線,并深深地迷戀于此,連冥王的召喚也被他當成了耳旁風。他膽大妄為地在人間又活了幾年,惹得神祇們不得不對他進行處罰。他們逮住了他,攫去了他的歡樂,把他扭送到了下界。在那里,一塊巨石正等著他推向山頂。除了贏得那荒謬英雄的美名外,他似乎別無選擇。是的,除了“肺結核”三個字沒有出現之外,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所有肺病作家的宿命: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反抗,他們的激情。
大家讀大家系列:局內人的寫作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濟源,1987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著有長篇小說《應物兄》《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入圍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應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主要作品被譯為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韓語等。 主編簡介 丁帆,1952年5月出生于江蘇蘇州。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自1979年始,已發表論文、散文及論著近1000萬字。 王堯,1960年4月出生于江蘇東臺。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月亮與六便士
- >
回憶愛瑪儂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姑媽的寶刀
- >
唐代進士錄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李白與唐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