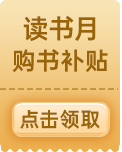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何不認真來悲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462466
- 條形碼:9787559462466 ; 978-7-5594-6246-6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何不認真來悲傷 本書特色
★斬獲多項大獎、臺灣實力派作家郭強生散文代表作。白先勇、席慕蓉、王德威、駱以軍等誠摯推薦!堪稱《斷代》之后沖擊人心的誠懇之作。
★《何不認真來悲傷》榮獲多項文學大獎。某瓣評分高達8.6。尚未出版,已火遍文學粉絲圈。
l 第40屆金鼎獎·文學圖書獎;
l 2015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年度好書;
l 2016臺灣文學金典獎。
★被譽為“華語當代文學創作書寫的新頁”,讀者感嘆“這是我繼張愛玲之后看過的至為誠實的寫作者”。這是一場對自我、原生家庭、孤獨與愛的一場私人化獻祭,因其自剖的姿態坦誠無私。關于背叛與自強、離棄與守護,關于親人的衰老和離世,關于浮世過往與將來之種種,真相只有一個——悲傷。是私人回憶,也像是無數家庭的群像縮影。
★這是作者靈魂和真相搏斗后所留下的文字。家本該是*好的港灣,他卻成為汪洋中僅剩的漂流木。一個分崩離析的家,一個近乎破碎的自己,他用一支筆,一字一字,繪出重生的父子關系。寫到盡頭,終于和家人和解。
★并非得到了愛才讓我們成為一個幸福或完整的人,更重要的其實是,在發現自己被愛蒙蔽或失去了愛之后,我們成為了一個什么樣的人。
何不認真來悲傷 內容簡介
當濃濃的愛意閃爍著星火,無從抽離的心境歡樂如昨時,原本溫暖的家庭在紛繁的壓迫與糾葛中展開了一場令人撕裂的對決:遠走他鄉的哥哥,溘然長逝的母親,晚年罹患阿爾茲海默癥、被騙光所有錢的父親,而他則開始了一段無法停止的兩地奔波的歲月……
這是郭強生對自我、孤獨、原生家庭與愛的一場私人化的獻祭,記錄人生滄桑之中的陣痛與印記、掙扎與困頓。因其自剖的姿態坦誠無私,故在一年內不但寫出了五十年的故事,甚而將其曬干晾透成了斑斑印痕,動人心肺于無形中。寥寥數語,揉碎傷痛,在幽深的筆觸里散發出溫柔的氣息。
何不認真來悲傷 目錄
春余:今生一場聚散已足夠
何不認真來悲傷
你不知道我記得
總是相欠債
家,有時就不見了
請帶我走
四十四
一個人面對就好
夏暮:我的一生獻給你,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母親不像月亮,像太陽
一個外省家庭的由來
他們是怎樣長大的?
失去的預感
婚姻的傷感
生死發膚
媽媽,我在湖南了
搖到外婆橋
冬噩:為什么總是家人,傷我*深
微溫陰影
誰在燈火闌珊處?
獨角戲
說不出口的晚安
關于痛苦的后見之明
霧起:不過是陌生人
放不下
兒子與弟子
流離
一廂情愿的幸福
償還
有一天我們都會老
霜降:青春讓人惆悵
相逢不恨晚
過眼煙云
一段琴
消失的圣誕樹
電影散場
歲月的塵埃
清明:所有的堅強都是不得已
誰配當親愛的?
沒那么簡單
我不過是假裝堅強
如果可以不再有后悔
悲傷是記憶的光
后記
悲傷,我全力以赴
何不認真來悲傷 節選
何不認真來悲傷 面對過往的幸福,對我而言,遠比回憶悲傷更需要勇氣。
逼視曾讓我受傷的記憶,至少證明我不再懼怕面對。就算偶有暗影反撲,也只像是遙望對岸的濃霧。
在悲傷的回憶中,我才能保持一種戰斗的姿勢,在空滅頹亡來臨前。
幸福的記憶卻讓我感覺軟弱,因為發現自己曾經對生命的流逝毫無警覺,總要等到它成為記憶后才懂得,那就是快樂,而當下只道是尋常。
中年后不敢多想那些無憂的過去。無憂源自無知,不知道煩惱有父母在頂著,不知道何為生老病死,不懂得無人共享的快樂其實不算快樂……
也因此,快樂的回憶只能點到為止,否則就要驚動了失落與遺憾。
偏偏總有久遠的往事偷渡登岸。
翻開了堆放已久的積灰相簿,企圖捕捉那其實已很遙遠的、我們曾經一起去拍的全家福,那是種什么樣的感覺。
那時,我們總是為了拍全家福專門跑去照相館。除了其中一次是因為哥嫂帶著初生的女兒首次回臺,連年近九十的外公都出動了,其他去照相館拍照的動機背景我已一概模糊。
或許都只是臨時起意。那總有個提議的人吧?如果要我猜,準是母親。
母親喜歡玩相機,或許說,她喜歡記錄家人的生活。臺灣**家彩色沖印照相館到底是哪間?這些年出現各說各話的情形。但據母親告訴我的,真正的**家是早在一九五幾年的名為“虹影”的照相館。母親是他們當時招考錄取的**位員工,擔任會計職務。老相簿里還有攝影師為母親拍的沙龍照。那時的母親真是美。
繼續翻閱相簿,發現都是母親掌鏡的時候居多。記憶中家里的**臺相機頗難操作,要將一個長方匣捧在胸前,從上往下看進匣里對焦,光圈和速度全靠手調,只有母親會用。家里其他三個男生愛笑那是老古董,該丟了。等到父親接觸到拍電影的工作,有一天回家告訴我們,劇照師都還是用這一款,說是比起后來的單反,它的畫質好太多,那時我們才知那相機是屬于“專業人士用”的,從此對它刮目相看。
想必是我們懶于學習操作,才會忽略了該讓母親多當模特兒而非總在掌鏡。是不是因為這樣,母親才總會興起去照相館留影的念頭呢?
* * *
不僅拍照總是母親的工作,連全家旅游也向來是母親在規劃。
說起來,真正一家四口出游也就那一次,去日月潭。那年哥哥高一,我還在上幼兒園。之后哥哥就再也沒有跟我們一起去旅行了。一家人留下了難得的戶外合影,每一幀的場景時空我仍印象清晰。有一張是我們全翻滾在草坪上,將那臺專業級相機設定好自拍模式,并很有創意地傾斜放置,形成對角線的構圖。而另一張是造訪“毛王爺”時當地導游為我們拍的。除了哥哥堅持不肯外,我們全都穿戴起高山族的服裝。關于那次旅游,更深的印象是我一路暈車嘔吐,到了教師會館已手腳僵冷。偏偏都沒空房了,我們一家睡的是地下室的通鋪。
想起來還是歡樂。絕無僅有的一次合家歡。之后在溪頭、墾丁、花蓮、紐約、費城、華盛頓,總是三人行。
兩個孩子都在異地他鄉的日子,沒想到父母還是去照相館拍過幾幀二人合影。那時的母親心里在想什么呢?
* * *
小學時**次讀到《蔣碧薇回憶錄》,書里附圖中有許多是她**任畫家丈夫徐悲鴻為她畫的肖像,便以為畫家都愛為妻子或者家人畫像。但父親這輩子只為母親畫過兩張油畫像。更不用說,我和哥哥自然是沒份的。母親對此難免心有遺憾,卻總另找借口表達不滿:“一直希望你為我父親畫張像,人都死了你還是沒動過筆!”
畢竟比起照片來,畫像無疑更有紀念價值。至于母親那兩張畫像,都是完成于新婚后。一幅畫中她穿著水綠旗袍,但該畫因臺風泡水,油彩早已龜裂破損,卻仍被母親以玻璃框裱起掛在臥室。另一幅畫的則是還留著少女馬尾的她。
現在那張人像哪里去了?
我竟然這么多年都沒注意到它已下落不明。 * * *
父親盯著電視屏幕上的足球賽目不轉睛,我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打量著他。過了一會兒我也把視線移到了電視上逐球的一群小人,只是放空注目,為了打發掉父子間像這樣完全無言共處的時間。
已經六七年了,我們都早已習慣這種形式上的親情。已經很久,對于彼此都存在著不撕破臉就好的應對方式。
我仿佛知道整件事是怎么發生的,卻不愿接受。
一開始先是發現,與哥哥一同出席父親的畫展揭幕儀式,父親怎么只向眾人介紹這位“在美國當工程師”的大兒子,對于他身旁在臺灣當教授的另一個兒子卻略過不提?又有一次,忘了為什么細故爭執,扯到了他的一位學生,父親竟然對我說出了“我跟他更像父子”這樣的話。
那年,發現八十五歲的他跟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交往,我一再提醒他那女人肯定沒打什么好主意,父親竟用輕蔑的口吻回我一句:
“這是我們男女之間的事,你懂什么?”
四十四歲那年搬出了老家,把家讓給了他與那個來路不明的女人。但仍不敢住得太遠,畢竟在臺灣父親沒有任何親友,跟他“情同父子”的學生們,哪個不是拿到學位就不再出現了?
那時覺得父親仍需要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是我更需要他。母親已過世,而與我年紀相差十歲的唯一手足,從來也算不上親近。我賴在父親身邊,怕離得太遠,就會失去自己跟“家”這件事的*后聯結。
一年多前父親開始出現輕度失智的癥狀,每周日我回“家”一趟,陪他上上館子。問他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或“不記得了”,語氣卻很平靜。有時我心中會暗自懷疑(或期望),他的不記得會不會是偽裝的?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有印象,母親經常為他愛拈花惹草費神又傷心。慣愛偷吃的男人擅于偽裝、說謊與耍賴,也許老來可用來自我保護,讓他不想見的人無法靠近。
因為缺少互動,究竟失智程度是在惡化,還是藥物控制有幫助,我無法判斷。問那女人父親現在的情況如何,她總說好得很。直到過年時那女人外出,我才發現她一直在盜領父親的存款。
以前我從不過問父親的財務狀況,怕讓已有心結的父子之間,徒增了更多的不信任。但我發現父親名下已經沒有任何定存的錢了。我還發現,那女人把失智癥與高血壓的藥藏了起來,有兩個月沒給他服用。
我決定跟那女人開戰。
這回父親完全不像失智的病人,吼得雷霆萬鈞:“這就是我要的生活,你是什么人敢來干涉我的生活?”
他并非失智到認不得我是誰,但我恍然驚覺,親情與家人對他而言,會不會只是他人生中曾經走岔的一段路?
* * *
母親過世第二年,有一次我與好友餐聚,散會前她像憶起了什么趣聞似的,轉身小聲跟我說:“我一直忘了告訴你,你那時候還沒回臺任教,有一天我很意外接到你媽媽的電話,她跟我說,她很不快樂。”
我當下感覺像被突然宣判,我的母親不是死于癌癥,而是因我的疏忽意外致死。“你怎么到現在才跟我說這件事?”我激動得渾身發抖。
對方無辜地眨著眼睛說她忘了。在那之前,我并非不知母親不快樂,只是沒想到,她有那么不快樂,不快樂到會打電話給我的朋友,以為她一定會把她的心聲傳到我耳朵里。
記憶中,母親那時偶爾會在奇怪的時間打越洋電話來。臺北時間凌晨四五點,我問她怎么不睡覺,她說睡不著。母親說話總是嗓門很大,只有在那幾通電話中,我聽到她細弱如小女孩的聲音。
我只能安慰她別胡思亂想。
我考上大學那年,母親**次罹癌,身體一下子垮了,體重從以前的五十五公斤,到只剩不到三十九公斤的皮包骨(后來十幾年始終如此)。她一直都在抗病的抑郁低潮里,難得見她真正開心的時候。
除了我將啟程返臺任教的幾天前,她打來的那通電話。那次她心情極好,對著答錄機說個不停,念完了當天報紙的頭條新聞,還是等不到人的母親*后干脆對著機器唱了一首歌:“我有一簾幽夢,不知與誰能共……”
然而我終究沒能接到那通電話。
答錄機中的卡帶被我取下,裝進行李,但是還沒等到有那個心情放來重聽,母親就在我返臺次年病逝。
一直記著那留言的存在,卻也不敢再碰。
這些年我一直會幻想著,如果接到電話,跟母親可能會有怎樣的對話?會不會發現也許跟在聽答錄機時一樣,除了想哭,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我已太習慣面對那個不快樂的母親,偶爾開心的她反愈教我悲從中來。
回臺前我原本是這么打算的,至少也回來住個一兩年,不能像哥哥赴美后,三十幾年來都只是浮云過境般回來吃幾次飯就走人,連接父母去他美國的家中小住也一次都沒有過。
回臺卻成了送母親*后一程。母親第二次癌癥來得意外且兇猛,從擴散到往生,前后不到五個月。
何不認真來悲傷 作者簡介
郭強生
生于1964年。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現為臺灣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曾獲時報文學獎、金鼎獎、臺灣文學金典獎、開卷好書獎、九歌年度小說獎、金石堂年度影響力好書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等。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說集《夜行之子》,長篇小說《斷代》《惑鄉之人》《尋琴者》,散文集《就是舍不得》《我將前往的遠方》,文學論著《文學公民》等。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月亮虎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經典常談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月亮與六便士
- >
煙與鏡
- >
隨園食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