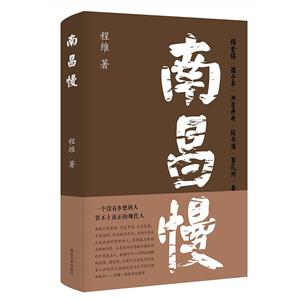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南昌慢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37249
- 條形碼:9787305237249 ; 978-7-305-23724-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南昌慢 本書特色
★ 本書穿插多幅精美照片,隨書附贈作者親繪藏書票。 ★ 穿街走巷的南昌地圖,畫盡南昌城的千年風貌。妙趣橫生,于閑筆間叩問城市的時空與鄉愁 從豫章后街到書院街,從滕王閣到百花洲,從繩金塔到杏花樓……每一個地標,每一處巷落,都是故土鄉愁。 ★ 雋永光輝的南昌城市史,追慕 古往今來的文人雅士、星宿泰斗的生命軌跡 八大山人、婁妃、利瑪竇、汪大淵……他們的名字與這座城息息相連,與它共嘆息、同孤獨。在鐫刻著南昌文人雅士的足跡與心聲的地點,一再路過,于千年后重拾他們在同一座城市的生命遺跡。 ★裝幀由屢獲“*美的書”殊榮的知名設計師周偉偉精心打造。
南昌慢 內容簡介
本書是南昌作家程維繼《南昌人》之后, 書寫南昌這座城市的又一部隨筆集, 是其“南昌三部曲” (或稱“南昌三書”) 之一。作者在歷史遺跡、老建筑、老街道、老店鋪, 乃至斷壁殘垣中回望歷史, 追溯城市記憶, 看時光流轉, 寫人事滄桑。城市是一個地理和空間的概念, 也是一個文化和時間的概念。一個“慢”字, 寫出了這座城市在物換星移中深厚的歷史積淀, 也道出了作者在穿越歲月的光影、細細梳理城市記憶的過程中涌現出的幽幽鄉愁。在這一書寫過程中, 南昌城與眾不同的魅力也慢慢浮現出來。另一方面, 《南昌慢》也顯現出程維作品貫有的詩性魅力。
南昌慢 目錄
序:時間的鄉愁
豫章繪事:跟著八大撿腳印
皇皇滕王閣
海昏之匙
孺子亭記
遺址:長春殿
洪崖夢記
投書浦:一個典故產生地的消失
繩金塔記
百花洲記
汪大淵之藍
利瑪竇之書
煙雨杏花樓
孤獨者的光芒
只有風聲穿透歲月
老街頭
橋
城與門
老校門
寺與宮
生米鎮
后記
南昌慢序:時間的鄉愁序:時間的鄉愁
南昌慢 節選
豫章繪事:跟著八大撿腳 前世 南昌*早叫豫章,且比叫南昌時間更長。現在豫章成了南昌別稱,或代指老南昌。然豫章之名,是隱秘而偉大的,這里面藏著的,是一座古城的厚重人文。 過去,外地人來南昌,都往城南跑。 跑去干什么?看八大山人,準確地說,是看他的畫。城南有個青云譜道觀,是一處南昌難得保存下來的古典小園林,這對當年頹舊、單調、乏善可陳的南昌來說,殊為罕見。據說清初的晚明遺民朱耷,自號八大山人,在這里隱居作畫,名重天下。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個叫李旦的先生考證這節來歷,發現道觀中有八大手植老桂及其墓,并有心將從民間收集到的老八大的畫,藏于道觀庫房,妥善保存起來。在常人眼里,老八大的畫無甚可觀,以丑怪著稱。殘山剩水,孤魚獨鳥,為其拿手絕活。掛堂屋,絕無吉利喜慶可言,反而有著乖張與戾氣,土財主不會喜歡,老百姓喜歡不了,能識幾個破字的人未必瞧得明白,但窮酸文人喜歡,士大夫也青眼有加。老八大身為換代之際末路王孫,一生過得顛沛且寒磣。僧人、瘋子、啞巴、怪咖,都是他在俗世的烙印,好在他能畫一手畫,他的畫如同他的身世,孤獨、桀驁、禪意道心,仿佛歪打正著,前人從沒這么畫過,是天意成全了他。但世間,畢竟大多數人不懂藝術,他故去,已三百余載矣。能有多少人看得懂八大?老實說,我至今不敢說能有多少。我家靠飯桌的墻上,就掛著一幅,由美術出版社根據八大《安晚冊》原作限量高仿印制的鱖魚圖。那年我為美術社寫了個字,該社社長很當回事,為表答謝,就把此畫送給我,說與真跡效果差不多。八大真跡自是罕見,隔玻璃我隱約見過幾幅,只能看到他筆墨中的冷逸與孤獨。八大的魚是苦澀的,和我在飯桌上吃的魚的味道顯然不一樣,那是世俗所不能容的東西。所以當年八大流落民間的畫,未必能賣大價錢,我說他是中國的凡·高。那年余光中對我說,凡·高在世時,他的畫被人用來蓋菜壇子。 由于八大山人,青云譜道觀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初期偌大個南昌城,唯一可作散心和游觀的地方。 我當年高考后為了驅散心中鳥氣,就和幾個同學,各騎一輛破自行車往城南奔,一頭扎進青云譜道院,其時已是八大山人紀念館,我先是呆呆地看畫,和絕大多數人一樣,說不出好來,沒有那種邂逅大師如遭雷擊棒喝的感覺,其實那時我已習畫有年,只是畫素描、水彩、油畫之類,當時畫《占領總統府》巨幅油畫的陳逸飛和《霸王別姬》油畫的湯沐黎,以及《西藏組畫》的陳丹青是我心目中的大師,我家里有倫勃朗畫冊,《羅丹藝術論》,卻沒有有關八大山人的片紙。說白了,我人生初次遇見八大,不是沖著他的畫去的,是去青云譜道院散心的,那里也擠滿了懷著同樣心思的人,竹篁、荷塘、曲廊、亭榭,足以給我們心頭的悶熱與浮躁帶來一些清涼。八大的畫那時仿佛與我隔著。他是個古人。即使青云譜道觀因他而引來不少游人,但他對那時來此的游人而言好像只是個出行的由頭。 我雖生在南昌,從小好繪事,但知八大也晚。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早年成長期的人文環境是與古典傳統不挨著的,崇尚的是紅色革命的宣傳藝術、政治圖式,至七十年代末期,才知道羅丹、倫勃朗,其時,油畫界出現了湯沐黎的《霸王別姬》、陳逸飛的《占領總統府》、陳丹青的《西藏組畫》、羅中立的《父親》。對中國傳統繪畫,當時的人們幾乎無聞,*多能見到的是鄭板橋的竹,還是印在掛歷上的。對外賓開放的友誼商店,有六分半體“難得糊涂”的拓片。這些書畫都配著鄭板橋那首著名的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八大是不反映民間疾苦的,他自個都苦不堪言,只有“橫涂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所以八大是在那些身為“大眾”的我們的視線以外,這不是八大的不幸,而是我們的悲哀。 在日常生活中,大師與絕大多數人壓根不挨著,若是挨著,十之八九,大家會把他視作瘋子。八大尤為典型。他當年出現在南昌街頭,哭哭笑笑,瘋瘋癲癲,就像個瘋子。然而,他是偉大和富有創造力的“中國病人”之一,他的畫也是病畫兒,這種人所患的病一半來自天生,一半來自境遇。 八大是神秘的,他的畫與身世留下諸多不解之謎,跟著八大撿腳印,因其跟別人大異,自然也就難尋些。 八大生于明天啟六年,即1626年秋,家庭背景顯赫,乃明宗室后裔,傳為明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南昌寧王府位于今日章江路省歌舞團及子固路省話劇團與省京劇團的那一大片院落。七十年代,我家與舊王府比鄰而居,從棕帽巷一翻墻就進了省歌舞團破敗而凋敝的院落,明清建筑的王府屋宇雖不存,卻遺有老墻的月亮門及高大古樹,院內恢宏的臺基上,遺有古建筑廊柱的巨大圓形石頭基座。可以想見當年王府的氣派。而從省歌舞團大院大門出去,橫著的是人聲鼎沸、污水遍地、魚腥味撲鼻的露天菜市一條街,旁邊有鐘鼓樓,上世紀二十年代南昌起義,這里是義軍指揮部,架著機槍,整個寧王府內駐的衛戍司令部隊,都在掃射范圍內。明清之際,這條路是通章江門的,那是接官送府之地,外來要人自水路而來,得從章江門碼頭登岸。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當年盤桓南昌三年,與弋陽王多有往來,交誼頗深,得到過他不少幫助。八大山人出生于末路王室之家,父親卻是個啞巴,但畫得一手好畫,他希望兒子將來成為一個藝術家。所以八大早年接受過良好的書畫訓練,至其19歲,天崩地坼,明亡清立,清朝統治者追殺明宗室,八大家破人亡,如喪家之犬,奔竄山林以求活命,先逃到南昌伏龍山藏身,在饑寒交迫中熬過數年,23歲時不得不遁入空門,到南昌以東約七十公里的進賢縣介岡燈社鶴林寺剃度為僧,拜介岡燈社主持弘敏頭陀為師,取僧名傳綮,號刃庵,從此開始了長達27年的禪林生涯。出家為僧于他而言是迫不得已,清初推行剃發令,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對晚明遺民是一道生死坎,怎么邁過去?剃光腦袋出家,不失為一途。明清之交,遺民多逃于禪,與此有關。 逃禪 一入空門萬事休,頭發光了,頂著個禿瓢,是可以打掩護的,八大也就有些殘喘工夫,得以修研佛禪,重拾繪事。介岡鶴林寺一待也就十六年光景,當其師弘敏去奉新另建耕香院,31歲的八大做了介岡燈社主持,從學者百余眾。八大在此作詩云:“茫茫聲息足林煙,猶似聞經意未眠。我與濤松俱一處,不知身在白湖邊。”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八大存世作品、十五開紙本《傳綮寫生冊》,即畫于此。弘敏卒,八大又到奉新接掌了耕香院。介岡燈社與耕香院,八大做的雖是和尚,外人眼里是高僧,他骨子里卻是不得已。戊戌年冬,朋友相邀到奉新,看了宋應星天工開物紀念館、張勛老家的大屋、百丈寺、晝錦坊后,聽說耕香院正在修繕,忙請朋友帶去看一下。冬陽下的郊野衰草金黃,從一條泥路進去,耕香院已修建得很是可觀,完全像個修身養性的園林式別墅,院子里晾曬著一地金燦燦的皇菊,皇菊已是一味養身好茶飲。就是沒有八大的影子,當地朋友把我們領到后院一處工地,指著一處仍用線圈的背山角落,告訴我們,幾年前縣里在這里開詩會,有人就此發現了“傳綮”之印,經專家鑒定,為八大在此出家時的印信之一。八大在耕香院所駐時間達二十年。 既然八大出家是為了避禍,風頭過了,自然是想還俗的。當他在奉新結識了裘璉時,肚子里就動了還俗心思。裘璉是八大的仰慕者,作過數首詩贈八大,詩中有“個也逃禪者,漂泊昔王孫”之句。“王孫”的尾巴,是八大一直要藏著的,風聲弱了,不禁又想露一點。49歲時,眼看就是天命之年了,八大看著鏡中的自己,已由一個昔日的倉皇少年變為蕭然老翁矣,不由心念一動,想把這副面貌立馬喊停片刻,那時沒有照相技術,也沒有馬克·呂布這樣精心為藝術家拍肖像的大師,他只有請好友黃安平為他畫了一幅全身像,權且留存。這就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青云譜八大山人紀念館的鎮館之寶《個山小像》,也是八大僅存于世的根據其本人面目繪制的畫像,不然我們絕對不知道八大長什么樣。應該說他的畫與他的相貌契合度還是很高的,猶如野老枯枝,精氣還在。畫中的八大不做僧人打扮,而是戴著斗笠,遮蓋了光光的腦袋,身 著寬袍,儼然林下散人。這身打扮,這幅畫像,透露了49歲八大的心思,他曾對友人饒宇樸說,我可能以后要像貫休、齊己和尚一樣,不會專注于法事了,而會旁涉詩會書畫了。貫休是唐代畫僧,唐亡后,云游四方。八大以彼自喻,是打算要放棄佛門,回歸俗世,求諸繪藝,是否娶妻生子也沒個準。研究者也一直認為八大雖為僧人,卻是一直沒有放下塵心,沒有放下性,他還想生個兒子,傳宗接代,延續其一支王孫血脈。我的一位導演朋友,就拍過一部八大山人的電影,讓一生悲涼孤凄的八大狠狠地談了一回戀愛。我去看影片時,才發現文學顧問竟赫然打著我的名字。朋友問我對片子有啥看法,我說:構思夠大膽,也算后世給八大他老人家的一種溫暖的補償吧。至今而言,《個山小像》應該說是我們走近八大的一扇重要之門,也是八大由僧界返回俗世的一道門。 前不久,八大山人紀念館的朋友約我去喝茶畫畫,我要他再帶我去看下《個山小像》,看到的卻已是復制品。雖然新建了一座真跡館,裝備著高科技現代化設施,所展真跡卻寥寥,朋友說一階段只展一幅,目的是讓八大的珍貴原作得以長留下去。這也是老八大在世時不可能想象到的厚待。懂行的,看重其藝術;外行的,看重其值錢。 當年的八大是鐵定要還俗的,他自然不知道三百年后有一座紀念館在等他,政府不惜重金修建庫房展廳,安保嚴密,蟊賊望而卻步。我的朋友是副館長,隔三岔五帶班值夜,為老八大巡邏守護,樂此不疲,如同帶刀侍衛。當時八大的僧友饒宇樸卻甚為訝異,勸說八大佛事才是正途,繪事不過是旁騖。八大在畫像上的四段自題,對勸說的僧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其一寫的是:“雪峰從來,疑個布衲。當生不生,是殺不殺。至今道絕韶陽,何異石頭路滑。這梢郎子,汝未遇人時,沒傝儑。” 進僧門,是迫不得已,出僧門已頗決然了。52歲時,八大完全是個云游的畫僧了,他一門心思去尋他的朋友裘璉談詩論畫,并結識裘璉做新昌縣令的岳父胡亦堂,成了胡亦堂的座上客。胡亦堂轉臨川知縣,邀請八大參加他主辦的夢川亭詩文盛會,八大是寫了詩的。職業畫僧的生活盡管少了空門的冷寂,多了應酬的表面熱鬧,可內心的悲苦與壓抑仍然無法排遣。在臨川胡亦堂府上為清客的兩年間,八大的情緒日益消沉,并沒有因為從寺院出來就找到了快樂,他的畫筆也是苦澀多于輕快。一日,他突然大哭大笑起來,弄得人摸不著頭腦。他扯下身上的袈裟,點火燒了起來,人攔也攔不住。他就這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會兒干號,一會兒狂笑著,走回了南昌。他瘋了,他癲了,沒有人敢挨近他。當他破破爛爛、瘋瘋癲癲出現在南昌街頭時,沒有誰知道他是昔日的王孫,只當是條可憐可嫌的徘徊于街頭巷尾與垃圾堆的喪家狗。還是他的一位遠房侄子認出了這個老叔,把他帶回家門,清洗干凈,悉心照料調養了一年多,他才漸漸恢復正常。 …………
南昌慢 作者簡介
程維,詩人、小說家。 1962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浮燈》、《皇帝不在的秋天》、《海昏:王的自述》、《雙皇》,詩集《妖嬈罪》、《他風景》、《古典中國》,詩劇《霸王》、《瀟湘圖》,散文集《畫個人》、《南昌人》、《豫章遺韻》、《水墨青云譜》等。獲中國作協“第8屆莊重文文學獎”、中華好圖書獎、首屆“滕王閣文學獎長篇小說獎”、第一屆、第三屆、第五屆“谷雨文學獎”、第二屆“陳香梅文化獎”、首屆“江西省政府優秀文藝成果獎”等,作品被譯為英、法、日、塞爾維亞等文字。現居南昌。
- >
山海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巴金-再思錄
- >
推拿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詩經-先民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