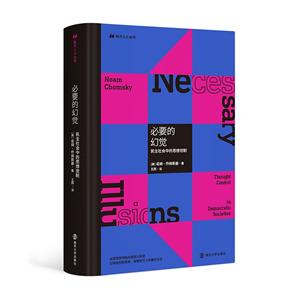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38734
- 條形碼:9787305238734 ; 978-7-305-23873-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本書特色
?★為什么我們應當關心媒體? 媒介批判在喬姆斯基逾半個世紀引人矚目的公共論辯中宛如一個支點。這不僅僅因為它揭示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在話語層面的博弈,更要緊的是,無論是談論權力之手在媒介實體中得以施展的形態,抑或思索新聞和宣傳信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切實影響,問題無不指向民主的本質。 若被偏見和無知所裹挾,則談公義將失去意義。 ★喬姆斯基有關媒體與權力關系問題的一次系統梳理。 借助梅西講座的契機,喬氏將其有關媒體問題的思考做了一次層次清晰的整理和呈現,一方面進一步闡發了成型于不久前的“宣傳模型”理論,又配以實例,條分縷析地講述了那些一脈相通又各具“巧思”的幻覺的制造術,并反思了知識分子在民主社會中應當承擔的角色。 ★追本溯源,認知信息與心理的雙重盲區。 喬姆斯基將謬誤的源頭回溯到媒體結構、新聞生產乃至受眾心理的不同環節,因而我們從中得以獲得的不僅是那些重大事件中失落的面向,還有指向其所以然的頗具啟發的解釋:遵從一個“正確的”議程所需付出的努力,顯然比與權力對抗要小得多;而在廣告之間的三分鐘間隙,或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難舉出讓人信服的觀點和證據,來表達新鮮的思想或驚人的結論。 ★尖銳而謹嚴,有如邏輯體操般充滿魅力的喬氏反諷。 強烈的立場和冷靜的論述,在喬姆斯基的論說中歷來是一組鮮明且意義重大的對照。一方面,全書以數據、事實、史料為據,事件、評論一一標示出處并詳加注釋;另一方面,譯文力求還原作者犀利冷峻的文風,保留了原文千回百轉的喬氏長句和反諷,讀之倍感酣暢。 ★那個無法回避的“永遠的異見者”。 數十年爭議傍身,但即使是不認同他的立場的人,也不得不回應他所提出的問題。正是以這種方式,他成為那個“隱藏在各式外衣之下的強權政治的zui持之以恒的批評者”;也正是因這種緣由,他的論述成為我們避免盲目、抵制偏見誘惑的一針有力的清醒劑。
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內容簡介
本書稿是上海三輝圖書“現代人小叢書”中的一種,由作者諾姆·喬姆斯基1988年在加拿大電臺發表的“梅西系列演講”講稿結集而成。喬姆斯基*知名的身份是語言學家,但他同時還是一位“誠實說出真相”的知識分子。在該書中喬姆斯基質疑了在資本主義政治系統中大眾媒介的欺騙性本質揭露其通過微妙而隱形的諸多形式實施意識形態控制手段,制造其在民主性和中立性方面的虛幻和欺騙,在保證民主形式表面上不受破壞的遮羞布下,剝奪民主政治機構的實際權力,以強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軟性遏制公眾對政府和私人權力的干涉。
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目錄
譯 序
前 言
**章 民主和媒體
第二章 遏制敵人
第三章 言論的界限
第四章 政府的幫手
第五章 解釋的功效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節選
第三章 言論的界限
... ...
制造共識首先針對的是那些自認為是“團體中富有思想的人”、“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杜魯門政府的一位官員評論說:“對普通大眾而言,一項綱領的細節是什么無足輕重,真正重要的是團體的領袖如何看待這項計劃。”一份關于大眾輿論的學術研究這樣總結:“能動員精英的人才能動員大眾。”外交歷史學家托馬斯??帕特森(Thomas Paterson)評論說,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重視并悉心設法培育的“大眾輿論”是“意見領袖”精英的觀點;是“公共外交政策”的觀點。這一點亙古正確,除了在某些時候必須解決“民主危機”,不得不動用更激烈的手段來使大眾回歸合適的位置。他們希望,在其他時候,大眾能夠滿足于消遣娛樂和定期的愛國灌輸,除非他們的領導人堅定地抵御來自各色敵人的危及生命和家園的威脅,否則,他們應滿足于對此只是嚴厲譴責。
在民主制度下,必要的幻覺不能通過武力強加給人民。相反,應該用更隱蔽的手段把它們悄無聲息地灌輸到大眾思想中。一個極權國家可能會滿足于對所需真相更低的忠誠度。人民服從就足夠了;他們想什么是次要的。但是在一個民主政治秩序中,始終存在這樣的危險,即獨立的思想可能會發展為政治行動,因此把威脅扼殺在萌芽期至關重要。
爭論無法被平息,而且,在一個正常運轉的宣傳機制中,爭論確實不應該被平息,因為如果被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的話,爭論具有強化機制的特點。因此*重要的是嚴格設定爭論的界限。只要堅持以精英共識為前提,爭論就可以澎湃地發展,而且應當在這個范圍內得到進一步鼓勵,從而有助于把這些信條確立為唯一標準,成為檢驗一種思想是否被允許的前提,而同時又強化了自由在掌握權力這樣一種信念。
簡而言之,至關重要的是設定傳播議程的權力。如果針對冷戰的爭論能夠集中在遏制蘇聯上—恰當地集合軍事、外交及其他手段—那么不管得出什么結論,這個宣傳機制已經獲取了勝利。我們早已確定了根本的假設:冷戰是兩大超級權力之間的對抗,一方咄咄逼人、四處擴張,另一方在為現狀和文明的社會準則進行防御。而不屬于議程范圍的問題包括是否要遏制美國、這個事件是否真的被正確表述,以及冷戰是否確實不是源于這樣的目的:兩個超級大國在竭力保護自己能夠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這些體系在規模上迥異,反映了財富和權力的巨大差異。蘇聯違反雅爾塔和波茨坦協議已成為眾多文獻的主題,牢牢樹立在公共意識中;我們接著進一步來討論其影響和重要性。但是,需要仔細搜索才能找到關于美國違反戰爭公約及相應后果的討論,盡管在這么多年后,當前*好的學術文件的評判是:“事實上,蘇聯對于[雅爾塔、波茨坦和其他戰爭公約]的遵守方式與美國沒有質的區別。”如果這個討論議程能夠被縮小到這樣的范圍:阿拉法特的曖昧立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桑解陣)的專權和失敗、伊朗和利比亞的恐怖活動及其他刻意陷害事件,這場游戲已基本結束了;我們不予討論的是美國和以色列的明確拒絕主義,及美國與附庸國的恐怖行為和其他罪行,這些行為不僅在規模上要大得多,而且對于有資格彌補或終止這些罪行的美國公民而言,在任何道德層面都無與倫比地更加重要。同樣的考慮適用于我們討論的任何問題。
一個貫穿歷史、成為標桿的重要思想是,這個國家處于防御立場,一直在抵抗對其秩序和高尚原則的挑戰。因此,美國總是在抵御侵略,有時是“內部侵略”。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攻打南越、保衛它的附庸國獨裁政權不被南越的侵略者推翻時,那些知名學者安慰我們說,“發起”在越南的戰爭是“為了保衛自由的人民,抵御共產主義的侵略”。我們不需要提供證據來為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辯護,事實上也沒有出現這樣的證據。一些人甚至引用這樣蒼白的證據,說1954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威脅”在印度支那“動用核武器來制止侵略”,因為在奠邊府,“法國部隊發現他們即將敗給共產黨的越盟(Viet Minh)”—即那些攻打我們法國盟友的侵略者,而法國軍隊正在保衛印度支那(抵御自己的人民) 。知識分子精英輿論基本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個立場。因此,從邏輯上絕對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即人們會反對美國的侵略—這是一個不存在的概念。無論批評者采取什么托詞,他們都一定是“河內的游擊隊”或“共產主義的辯護者”,為“侵略者”狡辯,也許還試圖隱藏他們的“秘密議程”。
另一個相關的思想是,“渴望看到美國式的民主在全球復制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懈主題”—在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武力鎮壓海地的選舉后,《紐約時報》的一位外交記者如是宣稱,而上述行為則是美國支持的軍政府上臺后人們普遍預測的可能結果。這位記者評論說,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是“*新的警告,提醒美國決策者在別的國家推行他們的意愿時—無論是多么仁慈的意愿—將面臨的困難”。這些信條不需論據,也無視如山的反證。偶爾的,謊言會露出明顯的荒謬,站不住腳,這時就可以承認我們在過去也不總是這么仁慈,或像現在一樣全心全意投身民主。多年來我們不時地利用“路線的改變”這個合宜的技巧,這不會引發嘲諷,只會帶來對我們無窮善心的歌頌,因為我們馬上會開始新的運動來“捍衛民主”。
我們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將蘇聯入侵阿富汗視為野蠻的侵略行徑,盡管許多人不肯把阿富汗游擊隊描述成“民主的抵抗力量”[《新共和》編輯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當受控于美國軍隊的拉美式恐怖國家無法再用武力控制國內人民時,美國對南越的入侵卻不會被如實看待。千真萬確,美國部隊直接參與了大規模的轟炸,并使用了“脫葉劑”化學武器,目的是將大量人口趕入集中營,從而“保護”他們不受敵人迫害—而這些敵人,美國不得不勉強承認,是人民樂于支持的。同樣千真萬確的是,大量的美國遠征軍隨后入侵并蹂躪這個國家及其鄰國,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摧毀這個顯然是唯一的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政治力量,消除各方都孜孜以求的政治和解這種危險。但是自始至終,美國都在為追求民主而抵御侵略。美國培植兇殘的吳庭艷(Diem)獨裁政權,其目的是暗中破壞日內瓦協議,阻撓允諾的選舉—因為不親美的一方有望勝出,這些行為都是為了保衛民主。《紐約時報》報道說,“這個國家分裂成了共產黨統治的北方和擁有民主政府的南方”,并指責“共產黨的越盟正從紅色中國‘耀武揚威地’進口槍炮和士兵”……威脅到了“自由的越南”。其后的幾年,因為“對民主的保衛”出了些岔子,鷹派和鴿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鷹派認為,只要有足夠的付出,敵人就會被消滅;鴿派則擔心訴諸武力來達到我們崇高的目的可能會耗資巨大;還有一些人選擇做貓頭鷹派,與兩個極端都保持距離。
在整個戰爭期間,主流聲音想當然地認為美國是在保衛南越;鴿派也不明智地如此相信。在隨后的幾年,這個思想一直未被撼動。對那些在暴行升級時拙劣地模仿*卑劣的共產黨領導層的人而言確實如此,人口密集的區域發生的飽和轟炸在他們看來,無非是“在美國軍隊幫助南越人民擊退北越及其游擊隊時發生的不幸的人員死亡”—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即便在美國將侵略拓展到北越后很久,那里都沒有北越部隊,當地抵抗美國及其附庸國入侵者的人民都不能算作“南越人民”。從這些我們如今仍在閱讀的資料和所有已披露的信息來看,這些結論并不令人驚訝:“南越的人民渴望擺脫共產主義國家在他們北部邊境的統治,獲得自由”,“美國通過干涉越南……來確立這樣的原則:亞洲的改變不會因外力突然降臨”。更滑稽的是這樣的事實:盡管許多人反感為大規模暴行狡辯的丑陋行為,但眾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對這樣的歷史評價毫不稱奇。這是民主制度有效控制思想的一個*好例證。
類似的,在當今的中美洲,美國正在“新興的民主”國家中全力保衛自由,為尼加拉瓜“恢復民主”—如果詞匯還能表達意義,這里指的索摩查(Somoza)時期。在異議能夠被表達的極限,一篇嚴厲譴責美國攻打尼加拉瓜的報道甚至援引了紐倫堡審判,報道中,《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編輯杰克??貝蒂(Jack Beatty)寫道:“民主一直是我們在尼加拉瓜的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支持對成千上萬尼加拉瓜人民的殺戮。但為民主而殺戮—即便為了民主找代理來殺戮—不是發起戰爭的合適理由。”人們幾乎找不到比《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威克(Tom Wicker)關于美國戰爭更前后一致的評論了,他譴責將里根主義用于尼加拉瓜,因為“美國沒有歷史使命或上帝賜予的權利向其他國家傳播民主”。評論家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個假設,即我們一貫的“對民主的渴望”實際上指導了自1979年7月19日以來,美國的附庸索摩查被推翻后,美國對尼加拉瓜的政策—盡管公認,不是在這個通過某種神秘手段、時機恰當得讓人匪夷所思的非凡革命發生之前。仔細搜索所有的媒體,會發掘出個別不符合這個模型的例外,但這些例外極為罕見,是對教化效果的錦上添花。
就在自豪地標榜自己是“一份獨立的報紙”的刊頭下,《華盛頓郵報》的編輯這樣提醒讀者:“中美洲為其明顯的自身利益,督促”桑解陣“遵守他們做出的民主化承諾”,而且,“那些反復敦促他人‘給和平一個機會’的美國人現在也有義務將他們的注意力和熱情轉向確保給民主一個機會”。在美國支持的恐怖國家中,脆弱的民主表象之下軍隊牢牢掌權,在這些國家“保衛民主”不成問題。
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1928— )
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及社會活動家,麻省理工學院榮休教授。被認為是美國外交政策方面最富影響力的左翼批評家。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煙與鏡
- >
月亮虎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