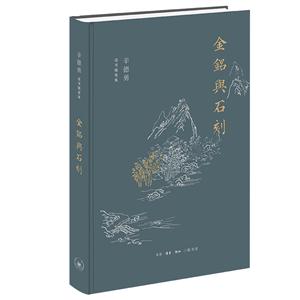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金銘與石刻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9818
- 條形碼:9787108069818 ; 978-7-108-06981-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金銘與石刻 本書特色
金銘石刻作為史料的價值日益凸顯,成為學術界研治相關問題所必須參考之資料。對于金銘與石刻之記載,我們不能聽之信之,而是要慎之辨之,去偽存真。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金銘石刻的價值在于對傳世文獻的補充與深入,并不能存以金銘石刻記載顛覆現有歷史記載之認知。本書所收有關《燕然山銘》《雒陽武庫鐘銘文》《李訓墓志》的相關論述,體現了作者認真務實的治學態度和廣博貫通的學術素養。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金銘與石刻 內容簡介
全書主要圍繞兩方面內容:,針對新近發現的重要石刻史料《燕然山銘》,從刊刻的歷史背景、文本內容的辨析以及文本文字的校訂等方面進行總體論述與具體考辨,是對作者此前出版《發現燕然山銘》的重要訂正與補充;第二,針對作者所見的一些金銘與石刻,從史學研究的角度進行辨偽,尤其是去年年底新見的所謂“李訓墓志”以及前一段曾引起較多關注的“雒陽武庫鐘銘文”,作者均依事理、據史實進行了認真考證,很終得出這些銘文均為贗造的結論。本冊的多篇文章由于其所關涉的內容收到廣大社會公眾關注,作者的論述也較為精彩,使得本冊書的亮點較多,可讀性亦較強。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金銘與石刻 目錄
自序
開成石經——遷,還是不遷
竇氏兄妹的政治危機與《燕然山銘》的刊刻
我看《燕然山銘》
遠方那座山
——發現《燕然山銘》背后的歷史
燕然山上的新發現
《燕然山銘》文本新訂定
《張氾請雨銘》辨偽
眼見也不一定為實
重申我對“雒陽武庫鐘”銘文的看法
所謂“中元二年”銀鋌銘文辨偽
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
由《井真成墓志》看所謂《李訓墓志》的真偽
《李訓墓志》降生的故事
題明嘉靖刻《重修鄆城玄武廟記》
天馬騰驤金褭蹏
——談談劉賀墓出土的所謂“馬蹏金”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金銘與石刻 節選
《李訓墓志》在去年圣誕節這一天鄭重其事地向社會公布之后,盡管也有人在網絡上一定程度地表示出應當更為審慎地排除某些疑惑,可是除了敝人之外,似乎并沒有人公開對它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或者說并沒有人斷然指出這是一件現代贗品。
有些學者,如日本學習院大學教授王瑞來先生,雖然也對墓志持有者的某些解讀(如出面“書丹”的“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備)提出質疑,但對這方墓志的真實性并絲毫沒有懷疑,甚至還特別強調指出:“盡管書寫者‘朝臣備’究竟是不是吉備真備尚存疑點,但這并不能否認《李訓墓志》本身的重要價值。墓志的書寫年代本身以及‘日本國朝臣備書’的表述,從日本史的視點考慮,無疑已經具有極大的意義”(王瑞來《〈李訓墓志〉書寫者“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備?》)。其他一些人的議論,也多集中在考察“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備和這一稱謂是否符合當時日本的通例這一點上。
這樣的討論,對于準確認識這通刻石銘文固然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我認識這篇墓志的首要觀察點,卻不在于這些具體的寫法是不是符合當時的情況,而是先從總體狀況出發,來看它是不是符合李唐社會的一般觀念和做法。況且當時的具體情況,有許多方面,由于缺乏足夠的較為具體的事例,往往不易取得很有說服力的證據。
譬如,王瑞來先生和其他一些學者討論的“朝臣備”這一題名是不是符合其實際姓氏和用名以及是否符合當時日本人姓名制度的通例這一問題,盡管王瑞來等人并沒有因此而否定這通刻石的真實可信性,但若誠實地面對眼前的真實情景,自然可以把它看作是賈人作偽的有力證據,可是固持《李訓墓志》為大唐真貨的那些人,也完全可以用唐世的變例來做解釋。相對于日本,唐朝畢竟在經濟和文化上具有絕對的優勢,根據自己通行的習慣來改易外來夷人姓名的用法,或是夷人入境隨俗,自行取漢名替代倭名,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看到“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一題名**眼后就感到的強烈疑惑,是覺得在李唐朝中的官員,尤其是主管外夷的鴻臚寺中的高官,其后人是不大可能選擇一位像“朝臣備”這樣的日本人來為他的父親執筆寫錄墓志銘的。
蓋后人為生身父祖倩人書寫碑志,乃是為先人增光添彩的舉措,更是生人的社會榮耀,即如明人姚希孟所云“非名筆書丹,不足以增琬琰之光,發松楸之色”是也(明姚希夢《文遠集》卷二五《楊方壺編修》)。所以,唐人的墓志,若非死者親人書寫上石,必盡可能邀請具有較高書法水平和社會聲譽、地位的人來執筆施行其事。其實這也是古今一貫的通例,或者說是必然的道理,用不著多做什么論證。
在剛一看到所謂《李訓墓志》的片段照片之后,我當即就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表看法說:“所謂‘李訓墓志’當屬贗造”,接著又稍微具體一些講道:“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志》必假。”
很多人不理解這話講的是什么意思,其實當時我引述的清人陳介祺在論述古器物銘文辨偽原則時講的下面這樣一段話,已經申明了其間的道理,這就是: 古學之長,必折衷于理,博而不明,不能斷也。辭賦之勝,亦必以理;漢學之雜,必擇以理。讀古人文字,不可不求古人之文;讀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不可專論其字。竊向往之而愧未能也。(陳介祺《簠齋鑒古與博古·辨偽分論》) 我認為《李訓墓志》是一件贗品,首先遵循的就是陳介祺講的這個“古人之理”。
具體地講,這個“古人之理”,乃是在所謂大唐盛世,相對于外圍諸國,唐王朝是具有絕對的領先地位和至高無上的優越感的。觀《舊唐書·東夷傳》記吉備真備等人入唐事時所說“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云云,一派輕視的口吻,這自是出自唐朝官方的載籍。檢《唐會要》卷一〇〇“日本國”條下紀事,正與此相同,可證《舊唐書》的記載乃淵源于此,而這反映的乃是唐人通行的觀念。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一題名,自然就會思考:像李訓這樣的朝廷命官,其后人又有什么理由非去請一個倭國島夷來書丹不可?這實在太難以想象了。換句話來說,也許大家更容易理解,即若是出現由日本人執筆書寫墓志這樣的事兒,就完全不像是皇皇大唐盛世應有的情況,而更符合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門初開之際華夏居民對待東洋來客的觀念和舉止。
更何況若是把這個書寫者落實為吉備真備的話,他還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留學生”,在唐朝,可以說幾乎是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觀李訓身膺的鴻臚寺丞一職,是從六品上的朝廷命官,而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之所受學的四門助教趙玄默官僅從八品下(《舊唐書·職官志三》),也就是說連老師都與李訓的地位相差很多,更不用說他所教授的外來“留學生”了。
因而,在我看來,李家后人特地邀請吉備真備或是其他任何一位普通的日本入唐留學生來為李訓書寫墓志銘文,都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不是什么唐朝人的國際性強弱和開放胸懷大小的問題,乃是實際社會地位高低使然,而這一點,古今一貫,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
做學問,研治古代文史,我耳邊常常回響的,是孔夫子講的那句淺顯易懂的話,即“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我看待所謂《李訓墓志》的真假,*先入手著眼的地方,就是這么淺顯的人情事理,而不是什么“朝臣備”的寫法和這個人的筆跡到底對與不對——那些都是不易弄明白的細瑣小節,這個才是難以逾越的大道理。 要是連這么淺顯的人情事理都講不通,我就有理由懷疑它的真實可靠性。關于這一點,清人方東樹在《書林揚觶》中講述辨偽之術時也曾有所論述,乃謂之曰: 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偽者,一在以其義理之當而知之,一在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余按二者相須不可偏廢,今之為漢學考證者,專主左驗異同而全置文義不顧。(《書林揚觶》卷下) 這“專主左驗異同而全置文義不顧”一語,實實在在地正切中清代很多所謂考據學家治學的根本弊病。今天我們看待所謂《李訓墓志》的真偽,首先要審視的,也應該是其整體“文義”這個大道理;特別是在墓志持有者公布之初,絕大多數人尚且無法看到完整、清晰的墓志拓本的情況下,學者們評判這通刻石銘文,尤其要首先關注這個大道理。換個角度講述這一態度,那就是學者治學,要把書一頁一頁地連著讀,并不能只是挑揀個別字句跳著看。
更進一步看,假若暫時拋開“朝臣備”的社會地位高低不管,“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一題名形式,同樣很不合乎情理。
這是因為“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七個字太過于突兀,即徒以國名冠加于人名之上,這樣的表述太過含糊。不拘古今中外,若是單看“日本國”這個國名,并不足以標明其身份地位;再同上文所題“秘書丞褚思光撰文”這幾個字相對照,就會更容易理解這一點:即這里的撰文者和書丹者本是相互對舉的兩件事兒,前者既有標記身份的職銜,后者也理應要有相應的內容。要是沒有,就意味著這樣的題名存在嚴重問題,存在著贗造的可能;若是再考慮到撰文者褚思光這個秘書丞從五品上的官階(《舊唐書·職官志二》),光著身子就上來書寫志文的東夷之人“朝臣備”,其身影行跡就變得更加可疑了。
我今天講演的題目,是“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這個“打虎武松”,出自武二郎在血濺鴛鴦樓后沾著人血寫在白粉墻壁上的那八個大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為什么他不只寫“武松”而要特地記明這個人是“打虎武松”?這就在于“打虎”者是武松的身份標志,若沒有這樣的身份標志,他的社會地位也就含糊不清了,特別是這樣做并不符合當時的習慣。參照《水滸傳》中描述的這一情況,再來審視“日本國朝臣備”這一題名,大家也就更容易理解這種題名形式的不合理性了。
我說“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志》必假”,除了由“日本國”人來書寫墓志銘文這一點完全不合乎情理之外,更深一層的含義,即在于此。而所謂《李訓墓志》既假,再來糾纏“朝臣備”這個人是不是吉備真備以及這一姓名稱謂形式是不是符合日本的實情,似乎也就沒有多大必要了。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金銘與石刻 作者簡介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古地理與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中國地理學史、中國地圖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舊史輿地文錄》《石室賸言》《舊史輿地文編》《制造漢武帝》《祭獺食蹠》《海昏侯劉賀》《中國印刷史研究》《〈史記〉新本校勘》《發現燕然山銘》《學人書影(初集)》《海昏侯新論》《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等。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山海經
- >
自卑與超越
- >
巴金-再思錄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史學評論
- >
月亮虎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