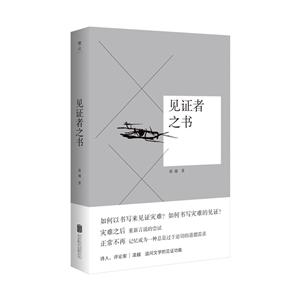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見證者之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642110
- 條形碼:9787559642110 ; 978-7-5596-4211-0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見證者之書 本書特色
如何以書寫來見證災難?如何書寫災難的見證? 災難之后 重新言說的嘗試正常不再 記憶成為一種總是過于迫切的道德需求 詩人、評論家 | 凌越 追問文學的見證功能 1.本書是知名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凌越的*新評論集,作品一見證主題,拷問文學在災難年代的見證作用,主題新穎。 2.本書以見證主題為經,具體作家和作品為緯,以對普里莫·萊維、霍布斯鮑姆、凱爾泰斯、米沃什以及斯坦納等人的作品進行了精彩的分析,既是精彩的批評著作也是對這些作品的精彩導讀。 3.本書中分析的作品和作者在國內讀者中都有十分大的影響力,有利于本書市場推廣。 1.本書是知名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凌越的*新評論集,作品一見證主題,拷問文學在災難年代的見證作用,主題新穎。 2.本書以見證主題為經,具體作家和作品為緯,以對普里莫·萊維、霍布斯鮑姆、凱爾泰斯、米沃什以及斯坦納等人的作品進行了精彩的分析,既是精彩的批評著作也是對這些作品的精彩導讀。 3.本書中分析的作品和作者在國內讀者中都有十分大的影響力,有利于本書市場推廣。
見證者之書 內容簡介
《見證者之書》是知名詩人、評論家凌越以“見證”為主題寫作的評論集,共收錄作者在2012—2019年間撰寫的二十六篇文章。全書共分三輯,輯“奧斯維辛靈魂的代言人”以對普里莫?萊維、博羅夫斯基、凱爾泰斯、威塞爾等奧斯維辛幸存者的作品為例,探討文學在見證災難時的責任與困境;第二輯“被戕害的詞語”從記憶與語言的角度,剖析專制權力對于日常生活的侵害;第三輯“用苦難量度語言”則從米沃什、斯坦納、曼德施塔姆夫人以及努斯鮑姆等人的作品出發,討論文學作為見證之必要,以及文學領航社會正義的可能性。此三輯文字以見證主題為經,具體的作家與作品為緯,借助作者豐沛的熱情與充滿思辨的筆觸,試圖厘清文學與苦難、道德之間錯綜糾纏的關系。
見證者之書 目錄
輯一 奧斯維辛靈魂的代言人
艱難的證詞
用金屬的光澤照亮眾生
萊維:從疲憊的牲畜到碳的詩意輪回
敘述的愉悅,但還不夠
大屠殺幸存者,在一片荒涼的天空下
有毒氣室和焚尸爐的風景
奧斯維辛靈魂的代言人
現代“園藝”國家觀的罪孽
質問希特勒的律師
輯二 被戕害的詞語
開往地獄的火車
來自德國的反省:人性—民族性—獸性
被戕害的詞語
《生而有罪》:我的父母是納粹
刷新第三帝國的歷史與記憶
從專制擁躉到反納粹斗士
從見證者到寫作者
讓歷史真相從迷霧中浮現
德國為什么曾滑入深淵?
輯三 用苦難量度語言
真相為何難以追尋
詩如何承擔“可怕的責任”?
被“新信仰”扭曲的心靈
對抗流逝的時間
用苦難量度語言
見證者之書
用《回憶錄》復活一個詩人的生命和靈魂
文學想象領航社會正義
跋
見證者之書 節選
在《第三帝國的語言》**章,克萊普勒道出寫作此書的內在動機:“在我的日記本里,LTI(第三帝國的語言)這個符號*初是個語言游戲,帶有模仿戲謔的意味,然后很快就作為一種倉促的記憶的緊急救助了,作為在手帕上系的一種結扣,沒過多久,它又成為那全部苦難歲月里的一種正當防衛,成為一種向我自己發出的SOS呼叫。”作為20世紀上半葉在德國境內的猶太人,克萊普勒兇險的境地一望而知,事實上他只是因為妻子是雅利安人,才*終幸免于難。在整個納粹統治的十幾年間,克萊普勒親歷了猶太人所受的侮辱和虐待,而且因為這本在德國六十多年間出版了三十多版、售出四十萬冊的《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克萊普勒成為納粹暴政*有名望的見證者之一。 克萊普勒青年時代在慕尼黑、日內瓦、巴黎和柏林修讀哲學、羅曼語文學和日耳曼學專業。1920—1935年任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羅曼語文學教授,1935年因其猶太出身被解聘。克萊普勒的求學和教學經歷對于日后寫作《第三帝國的語言》有重要意義,使他對語言有一種職業性的敏感,克萊普勒后來說那些年記下的日記對他來說起到了平衡桿的作用,“沒有它我早已經摔下去上百次了”。問題是,如果不是一位語言學者,誰會想到在對納粹語言極端冷靜的審視中將自己暫時帶離悲慘的境遇呢?那是逃避嗎?不!那是對生命的渴望。在感到惡心和渺無希望的時候,在機械工廠無盡的荒涼中,在病人和死者的床邊,在一個個墓碑旁,在極端恥辱的時刻,對語言的審視像是一層鎧甲保護著已經非常微弱的生之希望。許多時候,當我們冷靜地凝視自己的傷口時,疼痛的感覺會減輕,而對于克萊普勒而言,審視語言就有這樣的作用。同時,這也是一種*深沉的反抗,因為在克萊普勒的意識深處是對納粹語言的厭惡:也許明天它就會有所不同,也許明天你對它的感覺就會有所不同。這種隱隱的期待將克萊普勒凌駕在他自己的境遇之上,*終維護了內心的自由。 如果說語言就是世界,那么我們也可以說,對于語言的極端敏感正對應著作者對于世界的犀利觀察,克萊普勒的信念是:一個人說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是謊言—但在其語言風格中,他的本質會暴露無遺。那么,與其說克萊普勒在纖毫畢露地展示納粹語言的荒謬,不如說他經由語言的分析極其準確地捕捉到納粹事實上的殘暴。 剛開始的時候,當克萊普勒還只是遭到輕微的迫害時,他想到的是避開它—避開那些櫥窗里廣告牌上旗幟上的粗鄙語言,他埋頭沉浸在自己的職業中,全神貫注地寫作18世紀的法國文學。是啊,狀況已經夠糟的了,為什么還要用納粹的文字破壞自己的生活呢?如果偶然讀到一本宣揚納粹的文字,讀了**段,克萊普勒就會將它扔到一邊。街上若有什么地方響起希特勒或者戈培爾聲嘶力竭的怪叫,他就會繞一個大圈子避開高音喇叭。可是逐漸地,克萊普勒被禁止使用德累斯頓大學的圖書館,被掃地出門,被送進工廠。此時,作為一名語言學教授,他唯一可以研究的材料只剩下時代的語言,也就是他每天在報(當然只可能是納粹報紙)上看到的文字,每天在街上、在工廠里聽到的說辭。逃避再無可能,情勢使克萊普勒只能直視這一堆令他作嘔的腐爛的語言材料。 起初,克萊普勒是抱著學術研究的心態去記取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納粹語言材料的,因此他在筆記和摘要里總會留有類似這樣的注腳:“以后確認!”“以后補充!”“以后回答!”但是在戰后開始著手整理這些筆記時,克萊普勒意識到尋求納粹語言的語言學淵源的研究是一個太過浩大的工程,遠非他一人所能完成,同時他也對自己在**時間所做的記錄抱有信心,相信它們總有其價值。今天,我們看克萊普勒對于自己作品的認知,感覺他多少有點謙虛了。這些“半成品”(一半是具體的經歷講述,一半是已經進入到形而上階段的科學觀察分析)首先具有極重要的見證價值,而且由于克萊普勒是從他所擅長的語言分析進入歷史描述的,這使他的著作獨具一種穿透歷史的深度。 作為語言學者,克萊普勒深知語言的厲害:“納粹主義是通過那一句句的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眾人的肉體與血液的,它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復,將這些用語和句型強加給了大眾,令人機械地和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也就是說,納粹宣傳的本質是語言之毒素的滲透,這毒素慢慢滲進大眾的日常用語中,令他們偏執和短視,而語言毒素*終會演變成行為上的殘暴。席勒詩句說得好:“教養之語言,為你吟詩和思考。”反之,粗鄙的語言則會讓你瘋狂和暴戾。語言是行為的先導,有什么樣的語言習慣必然會引發相應的行為,從無例外。在克萊普勒看來:納粹語言改變了詞語的價值和使用率,將從前一般的大眾語匯收繳為黨話,并讓所有這些詞語、詞組和句型浸染毒素,讓這個語言服務于他們可怕的體制,令其成為他們*強大的、*公開的,也是*秘密的宣傳鼓動手段。如此看來,克萊普勒的工作其實是釜底抽薪的工作,他試圖分離出混在德語中的毒素(哪怕是劑量微小的砷),并將這些完全被污染弄臟的詞語置入群葬墓坑,長時間掩埋,有一些更要永遠掩埋。 在克萊普勒之后,另一個對德語的墮落做過精深分析的學者是喬治??斯坦納,在其1959年撰寫的著名論文《空洞的奇跡》中,斯坦納列舉出德語被病菌腐蝕肌體之后的種種癥狀:“修辭代替了文采,行話代替了精確的通用表達,外來語或借用詞匯不再被吸收進入本土語言的血脈,它們被生吞活剝,依然保持其外來入侵者的身份。語言不再使思想清晰,反而使之更模糊;語言不再直接有效地表達思想感情,反而分散了感情的強度;語言不再冒險(一種活的語言就是人腦能夠經歷的*大的冒險);語言不再被經歷,語言只被言說。”斯坦納的精彩總結很像是對克萊普勒所提供的**手納粹語言材料的歸納。而斯坦納給出的語言治療方案—當語言受到謊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實能把謊言清洗—克萊普勒早已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采納。 和斯坦納相似,克萊普勒將第三帝國語言的基本特征歸結為“貧瘠”,在十多年的廣泛傳播中,第三帝國的語言始終保持著驚人的貧瘠和單調,所有得以出版的報刊和書籍都在訴說著陳詞濫調,盡管是以狂熱的方式。克萊普勒注意到,甚至在那些被虐待得*厲害的受害者那里,在那些國家社會主義的死敵那里,在猶太人那里,到處都籠罩著第三帝國的語言,包括他們的談話、他們的信件,也包括他們的著作,只要他們還被允許發表東西,全都一樣。這個語言一方面獨霸天下,一方面貧瘠可憐,而且正是這貧瘠的語言令整個第三帝國方方面面都變得單調,從而使統治和奴役變得得心應手。比如,希特勒一上臺便迫不及待指認納粹黨是唯一合法政黨,而所有持有和納粹主義主張相悖觀點的人則要被清除,一切變得簡單明了—種族需要凈化,觀點需要統一,那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影響越來越大的政治園藝學思想的極致:一切旁逸斜出的東西都要被修剪整齊,一切異類則要被蕩滌,其理由則是極具欺騙性的所謂的美好未來。貧瘠的語言產生暴力行為,暴力行為清除異己,剩下簡單的整齊劃一的世界則更容易統治。這是一切極權清晰簡明的邏輯,而在這一過程中,良知和美的泯滅在他們看來則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小代價—不!他們不會認為這是代價,而只會認為這是必需的過程。*終,第三帝國的語言唯有服務于起誓,從而幾乎喪失其他的諸如告白、自語、請求和祈禱的功能。單調的語言造就面目模糊的人民,整齊的觀念則助長了具有毀滅性的狂熱,理性則被徹底隔離在國家生活的荒郊野外。 隨著寫作的推進,克萊普勒開始進入對具體詞語的回憶和分析—通常這兩種狀態攪拌在一起,對某個納粹用語的分析必然帶出與這個詞相關聯的個人記憶。在第五章“摘自**年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錄了1933年納粹初步掌握國家權力時的新狀況和新語言,以原材料的形式集中在一起。在寫作這一章內容時,克萊普勒個人狀況還比較正常—在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魏瑪德國培養起來的法治思維仍然在左右著他的觀察,他憤懣的語調里描述的幾乎難以容忍的現象日后看來還只是初步癥狀,而在那時他視作地獄*底層的東西,在后來頂多只能算地獄的前院而已。這些早期記述反映出他作為一個正直的學者敏銳的洞察力,在7月28日的記述里,他描寫了在每周新聞里一個有聲的電影錄像:希特勒在一個大集會上標志性的歇斯底里的怒吼,一邊握緊拳頭扭曲著面孔。對此,克萊普勒忍不住評價道:“真正確信自己有恒久、毀滅性力量的人,會像他那樣不斷地絮叨著千年大業和被殲之敵嗎?—我幾乎是帶著一絲希望從電影院走出來的。”然而事實上恐怖的氛圍已經在這一年隨著納粹的上臺全面鋪開:“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被突然解聘;選修克萊普勒法文課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克萊普勒是猶太人,學生來他的課堂上甚至需要一點勇氣了;也有一些善良的雅利安人在向克萊普勒表達著對希特勒政權的嫌惡。 這一切都讓他對于未來抱有某種希望,當然他絕對想不到納粹政權會持續十二年之久。在納粹十二年統治中被頻繁使用(*終被用濫)的詞匯在1933年還算是初次登場,但憑借著語言學者的敏銳,克萊普勒已經捕捉到這些詞所蘊含的可怕意味—“第三帝國的行話很煽情,而煽情總是可疑的”。克萊普勒發現,“人民”這個詞在納粹的行文中被頻繁使用:“就像吃飯時用鹽一樣,給所有的東西都捏上一撮人民:人民的節日、人民的同志、人民的團體、接近人民、背離人民、來自人民。”“集中營”這個詞當時還很新鮮,有一種異國的殖民地色彩,克萊普勒小時候聽到過,可是它又突然重新出現,表示一種德國的機構,一種和平的設施,在歐洲土地上針對德國人而設立。所有這些都已經顯露出納粹日后那些暴行的端倪,克萊普勒像一根敏感的天線都將其納入自己的日記,成為同時代德國人的一份杰出見證。 克萊普勒在寫作中沒有平均分配描述和語言學分析這兩大手段,一般來說,在書的前半部分,由于他還抱有撰寫一部科學的語言學著作的念頭,分析的成分更多一點。后來隨著事實的重壓,可能也因為克萊普勒已經決定以見證作為這本書的立足點,事實描述的成分越來越多,但總體來說,描述和分析這兩種手法在書中是相得益彰的。這本書*吸引人的地方應該還是那些親歷者才能捕捉到的納粹統治下德國人生活的種種細節,它們經由克萊普勒的記述活生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具有原生態生活所具有的撲面而來的生氣和震撼力。同時,分析的不斷出現又仿佛在這些事實外面包裹了一層薄膜—一方面用來防腐,一方面也是禁絕任何煽情的可能。克萊普勒對煽情很敏感,他早就因為煽情對納粹宣傳持有本能的懷疑。有時候這種分析還局限在語言風格的范疇內,比如在第十二章“標點應用”中,克萊普勒就精彩地分析了納粹主義行文在運用標點符號方面的特點。一般人會猜想,第三帝國的語言因為其本質上是玩弄辭藻不斷訴諸情感的,肯定會類似于狂飆突進派,沉湎于驚嘆號,然而克萊普勒發現這一點并不明顯,他給出的解釋是,納粹用那種持續夸張的態度將一切都組編成了呼喚和驚嘆,所以它根本不再有必要借助特殊的標點符號—哪里還能找到平實的敘述,以讓驚嘆語句凸顯自己呢?事實上,在第三帝國語言中被大肆濫用的標點符號是引號,一種意在諷刺的引號。它的出現在于對所引內容表示懷疑,并暗示所轉述的話語是謊言,比如俄羅斯“戰略”,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而丘吉爾和羅斯福也順理成章成為諷刺引號里的“國家政要”。 隨著寫作的鋪開,克萊普勒的分析逐漸越出語言風格層面,有時甚至涉及思想史的領地。在整本書中*具深度的分析,出現在第二十一章“德意志之根”中。在這一章克萊普勒從各個角度展開的語言學分析終于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納粹主義的源頭到底在哪里?是那個杰出作家和學者輩出的古典主義的德國嗎?更具體的則是歌德時代的德國人和希特勒時代的民眾之間存在著任何一種精神上的關聯嗎?懷著這樣的疑問,克萊普勒在威廉??佘若(Wilhelm Scherer)所著的《德國文學史》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在德國,精神生活方面的忽上忽下帶有堅定的徹底性,并且往上和往下都能走得很遠,無度似乎是我們精神發展的詛咒。我們飛得越高,這樣也就跌得越深。”克萊普勒就此確信,在希特勒的獸性與德國經典文學以及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浮士德式的放縱無度之間存在著一種關聯,而德國浪漫主義的“去界限”傾向則進一步助長了德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極端傾向。在該章末尾,克萊普勒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宣稱,納粹主義和德國浪漫派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確切地說,納粹是從浪漫派里生長出來的。納粹主義包含的一切在浪漫派那里都已經開始萌芽:摘除理性的桂冠、將人動物化、追捧權力思想、追捧哺乳動物、追捧金發野獸。后來著名學者以賽亞??伯林和沃格林都以更縝密的學術語言闡述過幾乎同樣的觀點,但是考慮到克萊普勒是在“二戰”之后的一年半里寫就此書(首版于1947年),他應該是*早將納粹和德國浪漫派聯系在一起的學者之一,這無疑是極具眼光的。 立足于詞的寫作,往往和詩不遠。詩人的工作一般主要圍繞詞展開—洗滌、擦拭、打磨,直至詞語生發出炫目的、讓人心智迷亂的光芒。克萊普勒的寫作已經顯露出他對于詞語超人的敏感,但和詩人稍稍不同的是,他選擇聚焦的詞語往往充滿了污跡和黑暗,這是一些被戕害的詞語,極端的意識形態和殘暴的行為已經將這些勉強用來指代它們的那些詞語腐蝕得銹跡斑斑、支離破碎。克萊普勒盯視著這些詞語,用冷靜的反諷襯托出它們的臃腫和狂妄。哦,“人民”“領袖”“英勇”“狂熱”—所有這些美好的詞語在納粹的語境中都墮入深淵,正如戈培爾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所說:“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是真理。”納粹所強調和依仗的精神作用到底斬斷了詞語通常和現實聯系在一起的紐帶,被戕害的詞語飄浮著,孤獨無依,仿佛更方便為那些虛妄的激情服務,仿佛更方便將其玩弄于股掌之間,甚至于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但是事物如果失去了詞語的命名、厘清和區分,終將會墮入空虛的黑暗中或者陷入瘋狂而不加限制的毀滅中。詞語輕飄飄給人們的日常交流帶來便利,但是它們有自己的尊嚴,一旦受到無底線的戕害,它們的反擊將會是致命的,想想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分子的下場吧。它們有一種隱忍的氣質,但是為了尋求與現實事物真實的聯系,它們也會果斷地掃除一切障礙—納粹主義不過是詞語清除的無數個障礙中的一個晚近的例子而已。它們執拗地抵達真實,因為在任何時代總有像克萊普勒這樣的人會尊重它們、幫助它們,而戈培爾早已抱著他充滿毒素的格言葬身地獄。
見證者之書 作者簡介
凌越 詩人、評論家、譯者。著有詩集《塵世之歌》、評論集《寂寞者的觀察》等,與梁嘉瑩合作翻譯《匙河集》《遲來的旅行者》等。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煙與鏡
- >
姑媽的寶刀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推拿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