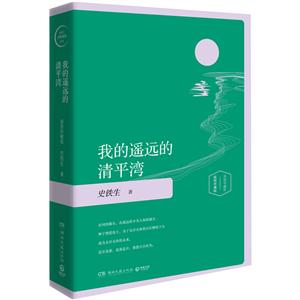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圖珍藏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0478094
- 條形碼:9787540478094 ; 978-7-5404-7809-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圖珍藏版 本書特色
▲精裝美圖,典藏之選:內文附錄吳冠中10幀靈動畫境,精美四色印刷,用紙考究。▲史鐵生夫人米親自審定,精細校訂。▲史鐵生是當代中國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寫作與他的生命接近同構在了一起,用殘缺的身體,說出了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出的卻是存在的明朗和歡樂,他睿智的言辭,照亮的反而是我們日益幽暗的心。——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得主史鐵生授獎詞▲被譽為“純粹的寫作者”,“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代表了我們當代文學所能達到的高度”;“他用自己的苦難提升了大家對生命的認識,而我們沒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當代文學大家史鐵生的小說思想深刻,視角獨特,結構精妙,以詩性的語言講述各色人物的生命故事,探討人生、命運、文化、信仰、情感等命題。他“對生命的解讀,對宗教精神的闡釋,對文學和自然的感悟,構成了真正的哲學”。透過史鐵生小說獨具匠心的結構與充滿意蘊的語言,我們時時可以感受到智慧的閃耀,讀懂人生與命運,信念與愛。▲讀史鐵生,如同讀我們自己,走失的心會安定下來。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圖珍藏版 內容簡介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是當代作家史鐵生創作的一篇小說。小說描繪了黃土高原上的小山村和一個風趣的放牛倌的故事。
內容:“我”插隊的時候,在陜北小山村清平灣喂過兩年牛。和“我”一起攔牛的破老漢是綏德人,一肚子民歌,“我”和他趕牛上山,便聽他一路走一路唱《走西口》、《信天游》。破老漢心地極善,平時遇到那些串鄉糊口的吹鼓手和說書藝人,他“尤其給得多”。他干過那活,知道攬工人的難處。破老漢帶著小孫女留小兒過活。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漢在飼養場給牛添草,留小兒便沒完沒了問我北京的事。破老漢是見過世面的,他1937年入黨,跟著隊伍一直打到廣州。正是在那動亂歲月,破老漢因為舍不得給大夫送“十斤米或面”的禮,耽誤了兒子的病,痛悔莫及。因而,他雖然和一個寡婦相戀卻不結婚,怕對不起兒子留下的留小兒。后來,“我”回北京治病,鄉親們托同學捎來各種土產,還有留小兒包著玉米花的手絹包。*后,同學摸出一張十斤的陜西省通用糧票,那是破老漢特意用十斤好小米換的,他記得兒子的病是怎樣耽誤的。破老漢、留小兒,還有“我”鐘愛的紅犍牛、老黑牛,清平灣留給“我”無限眷戀。
小說以抒情散文的筆法,通過老知青對插隊生活的回憶,真實鮮活、自然貼切地描繪了革命根據地陜北黃土高原的風貌,為讀者展示了陜北人民的樸實、忠厚、積極樂觀的性格,以激發人們認真地思考人生,思考社會。小說感情深厚,娓娓敘來,令人回味無窮。
小說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圖珍藏版 目錄
關于詹牧師的報告文學 019
插隊的故事 076
禮拜日 195
原罪?宿命 263
中篇1或短篇4 306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圖珍藏版 節選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北方的黃牛一般分為蒙古牛和華北牛。華北牛中要數秦川牛和南陽牛*好,個兒大,肩峰很高,勁兒足。華北牛和蒙古牛雜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彎去,頂架也厲害,而且皮實、好養。對北方的黃牛,我多少懂一點兒。這么說吧:現在要是有誰想買牛,我擔保能給他挑頭好的。看體形,看牙口,看精神兒,這誰都知道,光憑這些也許能挑到一頭不壞的,可未必能挑到一頭真正的好牛。關鍵是得看脾氣。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聲,好牛就會瞪圓了眼睛,左蹦右跳。這樣的牛干起活來下死勁兒,走得歡。疲牛呢?聽見鞭子響準是把腰往下一塌,閉一下眼睛,忍了。這樣的牛,別?要。 我插隊的時候喂過兩年牛,那是在陜北的一個小山村兒——清平灣。 我們那個地方雖然也還算是黃土高原,卻只有黃土,見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總在塌方,順著溝、渠、小河,流進了黃河。從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黃的山峁或一道道黃的山梁,綿延不斷。樹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幾棵什么樹,老鄉們都記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窯或是做棺木的時候;才放倒一兩棵。碗口粗的柏樹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誰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就都佩服,方圓幾十里內都會傳開。 在山上攔牛的時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黃土山都是谷堆、麥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溝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樹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總是“吸溜吸溜”地抽著旱煙,笑笑,說:“那可就一股勁兒吃白饃饃了。老漢兒家、老婆兒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姓白。陜北話里,“白”發“破”的音,我們都管他叫“破老漢”。也許還因為他窮吧,英語中的“poor”就是“窮”的意思。或者還因為別的:那幾顆零零碎碎的牙,那幾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愛唱,可嗓子像破鑼。傍晚趕著牛回村的時候,*后一縷陽光照在崖畔上,紅的。破老漢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著,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 過得好光景……”聲音拉得很長,雖不洪亮,但顫巍巍的,悠揚。碰巧了,崖頂上探出兩個小腦瓜,豎著耳朵聽一陣,跑了;可能是狐貍,也可能是野羊。不過,要想靠打獵為生可不行,野獸很少。我們那地方突出的特點是窮,窮山窮水,“好光景”永遠是“受苦人”的一種盼望。天快黑的時候,進山尋野菜的孩子們也都回村了,大的拉著小的,小的扯著更小的,每人的臂彎里都㧟著個小籃兒,裝的苦菜、莧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們跟在牛群后面,“嘰嘰嘎嘎”地吵,爭搶著把牛糞撮回窯里 去。 越是窮地方,農活也越重。春天播種,夏天收麥,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壩、修梯田,總不得閑。單說春種吧,往山上送糞全靠人挑。一擔糞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掙兩個工分,合六分錢。在北京,才夠買兩根冰棍兒的。那地方當然沒有冰棍兒,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們就扛著木犁、趕著牛上山了。太陽出來,已經耕完了幾坰地。火紅的太陽把牛和人的影子長長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著撒糞的,撒糞的后頭跟著點籽的,點籽的后頭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節奏地向前移動,隨著那悠長的吆牛聲。吆牛聲有時疲憊、凄婉,有時又歡快、詼諧,引動一片笑聲。那情景幾乎使我忘記自己是生活在哪個世紀,默默地想著人類遙遠而漫長的歷史。人類好像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圖珍藏版 作者簡介
史鐵生,生于1951年1月4日,北京人,小說家、文學家。1967年畢業于清華附中,1969年去延安地區插隊落戶,1972年因雙腿癱瘓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廠工作,后因急性腎損傷回家療養。1979年后,相繼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命若琴弦》《我與地壇》《務虛筆記》等小說與散文發表。1998年病情轉為尿毒癥,終至透析。此后有隨筆集《病隙碎筆》、散文集《記憶與印象》、長篇小說《我的丁一之旅》出版。2010年12月31日凌晨,因突發腦出血去世。其作品先后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多種全國文學大獎,多部作品被譯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 >
莉莉和章魚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二體千字文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煙與鏡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