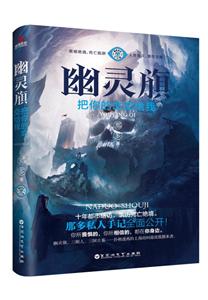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幽靈旗·把你的命交給我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031050
- 條形碼:9787550031050 ; 978-7-5500-3105-0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幽靈旗·把你的命交給我 本書特色
四幢經過抗戰時日軍轟炸而奇跡般被保存下來的“三層樓”,究竟為何幸免于炮火?是得益于傳說中樓頂飄揚的旗幟的庇護嗎?“三層樓”地基之下 到底有什么秘密?故事情節扣人心弦,又富有正能量,有一種深深的感染力。
幽靈旗·把你的命交給我 內容簡介
四幢經過日軍轟炸而奇跡般保存下來的“三層樓”正面臨拆除的窘境, 記者那多受命對其進行深度報道。那多試圖通過新聞輿論將“三層樓”作為歷史見證保存下來。上海圖書館一張當年轟炸后的照片使那多疑竇叢生: “三層樓”究竟為何幸免于炮火而完好保留? 是得益于傳說中其樓頂飄揚的國旗庇護, 還是當年“三層樓”的主人孫氏兄弟扛出的大旗震懾了日本鬼子的囂張, 或者是另有隱情……
幽靈旗·把你的命交給我 目錄
楔子
**章 六十七年前的照片
第二章 扛旗子的四兄弟
第三章 深藏在地下的秘密
第四章 盜墓之王
第五章 孫輝祖的白骨
第六章 噩夢開始
第七章 死亡詛咒
第八章暗世界的聚會
第九章“第三只眼”的秘密
尾 聲
把你的命交給我
楔 子
**章 歷史的迷霧
第二章 赤 裸
第三章 變化的歷史
第四章 一個人的精神病院
第五章武夷山市精神病院連續自殺事件
第六章 紫色的夢境
第七章 死亡惡作劇
第八章 夢 力
番外篇
后 記
幽靈旗·把你的命交給我 節選
幽靈旗 楔子 當年日寇濫炸后僅存的完整建筑物如今卻要被毀 2004年6月9日《新民晚報》 在閘北區恒豐路附近的裕通路85弄弄口,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層樓房子。據《閘北區志》記載,這個“三層樓”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遺跡。1937年,日寇對蘇州河北狂轟濫炸后,閘北成了一片廢墟,僅剩下的一處完整建筑物,便是這個“三層樓”。如今,因為舊區改造,作為重要歷史見證的“三層樓”,就要被拆除了。有識之士提出,“三層樓”不該拆,應當從愛國主義教育和歷史遺跡的角度加以保護。 記者昨天來到“三層樓”采訪,巧的是,天目西路街道“三層樓居委會”的辦公室,就在“三層樓”里。居委會主任周玉蘭介紹說,“三層樓”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4個有錢人合伙建造的,當時共有4幢。之所以在日本人轟炸下“幸免于難”,據說是因為當時住在樓里的外國人打出了外國旗子。以后,幸存的房子成了這里*顯眼的建筑,并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閘北境內*高的建筑。人們習慣于把這里稱為“三層樓”,連“三層樓居委會”也因此而得名。 由于恒豐路拓寬和舊區改造,此前已經有兩幢“三層樓”被拆除,剩下的兩幢現在也“岌岌可危”,被列入了拆除的范圍。眼看這一歷史遺跡就要“銷聲匿跡”,閘北區政協委員吳大齊等心急如焚,提交提案反對拆除“三層樓”,他認為,盡管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三層樓”沒有保護建筑的名分,但這些建筑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見證,這樣的遺址在上海也并不多見,應采取各種措施積極保護下來,將其改建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教育后人勿忘國恥,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周玉蘭也覺得拆除“三層樓”實在可惜,居住在這里的幾十戶人家雖然盼望改善住房條件,但他們也認為“三層樓”應該得到保護。 **章六十七年前的照片 由于要參加今天的評報,所以我把同城幾家主要競爭媒體的當日報紙都找來看了一遍。每家報社每天都會有類似的會議,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幾家媒體,如果別家有的新聞自家沒有,叫漏稿,責任可大可小,嚴重的能讓相關記者立馬下崗;如果自家有別家沒有,當然沾沾自喜一番,獎勵嘛,一些銅錢而已,多數時候只有口頭表揚。重罰輕獎,皆是如此。 所以開會前一小時,我把《新聞晨報》《青年報》《東方早報》《解放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掃了一遍,于是就看到了以上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我們漏了。 不過在我看來,這算不上是重大新聞,也不是條線上必發的稿子,屬于別家的獨家新聞,是他們記者自己發現的稿,總不能不讓別人有獨家新聞吧?雖然領導們總是這樣想,但小兵如我們,還是覺得,該給別人一條生路走……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聞都不漏的報紙,那別家報社就不是都不用活了?而且《新民晚報》是每日上午截稿,相比我們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報而言,本來就有先天優勢,報道比他們晚一天是常有的事。 再說,評評報而已,有必要得罪平日在報社里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嗎? 所以,評報時輪到我說話,我只以一句:“今天《新民晚報》有篇關于歷史遺跡的獨家稿,我們要是以后能多些這樣的發現性稿子,報紙會更好看。”輕輕掠過,絲毫沒有加罪于誰的意思。 可是頭頭兒自有頭頭兒的想法。如果是新來的頭頭兒,想法就特別多。 評報會開完,藍頭讓我留一下。 藍頭姓藍,是新來的頭兒,所以叫藍頭。職務是副總編。這是個分管業務的副總編,于是我們分管業務的變成了兩個副總,職務重疊,誰都知道這其中涉及報社高層的權力糾紛。 藍頭初來乍到很賣力,磨刀霍霍,已經有許多不走運的記者編輯挨刀子了,被他叫住,讓俺滿心地不爽,不過我在報社也算是老記者,功名赫赫,聽得見得多了,心一橫,誰怕誰。 話是這樣說,好像心還有點慌,一點點,真的只有一點點而已。 “想和你說晚報那篇獨家稿的事。”藍頭滿臉笑容地說。 我看著他點了點頭,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記派頭,好像我是領導似的。 “別人有獨家稿不怕,但我們得跟上,有時候,先把新聞做出來的,不見得是笑到*后的。”藍頭開始娓娓道出他的計劃。 原來他想讓我去做一個深入調查,把這兩幢大樓的底細翻出來,擴大影響,力圖通過媒體的影響力,*終把這兩幢大樓保留下來。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件功德無量的事,同時也展現了媒體輿論監督的力量,*重要的是,也展現了我們《晨星報》的力量”。有句話我知道他沒有說出來:“這也展現了我藍頭的英明領導。” “我雖然剛來不久,可你的報道我看了很多,你是《晨星報》的骨干,這個專題報道就交給你了。”他站起來,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 “沒問題。”我拍胸脯保證,心里暗笑,看看,這藍頭還知道哪些人能動,哪些人不能動,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不是? 深入報道是件細活,我打了個電話,和居委會說好明天下午去采訪,而明天上午,我打算去一次上海圖書館。如果那幢大樓真如《新民晚報》報道里說的那么有名,上海圖書館一定有它的資料。要想把大樓保下來,這類能證明其珍貴性的資料是不能缺少的。再說,引用一下資料,我的稿子也好寫。 第二天一早九點,我就到了上海圖書館。我是那里的熟客,早就辦了張特許閱覽證,可以查閱那些不對外開放的文獻資料,他們管宣傳的幾個人我都認識,*關鍵的是,幾個古舊文獻書籍的分理員我都熟。雖然他們的內部網絡可以查書目,但許多時候沒人指點還是有無從著手之感。 也巧,剛走進上海圖書館的底樓大堂,就看見分理員趙維穿堂而過。 我把他叫住,然后遞了根“中華”過去。我不怎么抽,但好煙是一直帶著的。 “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這里不準抽煙,說吧,這次又要查什么?”趙維推開煙,很上路地說。 “呵呵,還是你了解我。”我笑著把煙收回去。 “沒事你還會上這兒來?” 我把事情一說,趙維指了指VIP休息室,扔下一句“在那兒等著”就走了。 坐在沙發上等了大約十分鐘光景,趙維拿著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裝本過來。 《上海老建筑圖冊》。 “1987年出的書,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從前的老照片,對建筑的介紹也相當詳細。”趙維說著翻到其中的一頁。 “看,這就是那四幢樓,當時日軍轟炸后不久拍的,珍貴的照片、文字資料也挺多的,你慢慢看,要掃照片的話去辦公室,反正那里你也熟,我還有事,不陪你了。” “你忙你忙。”我嘴里說著,眼睛卻緊緊盯在這頁的照片上,一瞬間的驚詫,讓我甚至忘記對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趙維表示應該有的禮貌。 我不得不承認,這真是一張令人驚嘆的照片。 那簡直是一個奇跡,這張照片所呈現的,是近七十年前的一個奇跡。 我猜測著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是那場轟炸過后的一小時,還是一天、兩天?不可能更長的時間了,因為照片中的畫面上,四處是廢墟和濃煙,見不到一個人。 當年日軍轟炸過后,上海像這樣一片廢墟的地方很多,但在這張照片里,殘屋碎瓦間,卻突兀地聳立著四幢毫發未損的建筑。 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是在高處,取的是遠景。遙遙望去,四幢明顯高出周圍破爛平房的大樓,分外顯眼。 在剎那間我甚至以為,當年日軍轟炸機投下一顆顆重磅炸彈時,這片街區張開了只有在科幻小說中才聽說過的能量防護罩,所以毫發無傷,否則,以周圍建筑被炸損的嚴重程度,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這當然是個可笑的念頭,真有保護罩的話,怎么四幢樓四周和之間的平房都塌了,就只留了這四幢樓在?可是,照片上所顯示的狀態,顯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區更為荒謬和不可思議。 我隨手翻了翻前面幾頁,發現其他建筑取的都是近景,而且照片只占整頁的一半左右,只有這張照片取的是遠景,而且占了一整頁。我翻到后一頁,果然,后頁上是四幅比較小的大樓近照,以及文字資料。想必當時的編者也覺得這張取遠景的照片極為神奇,所以才給予特殊待遇。 我翻回前頁,凝神仔細看這張照片,四幢大樓的排列很奇怪,每幢大樓都相隔了一段距離,*前面兩幢,后面一幢,再后面一幢。 我總覺得這排列有問題,翻到后面的文字介紹,果然看到這一段。 “當時孫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樓,以孫家長兄的大樓為中心,其他三幢大樓呈‘品’字形圍在周圍,每幢大樓之間的距離有五六百米。” 我翻回去一對照,果然是“品”字形。 不知不覺間,我的眉頭已經皺了起來。當年這里并不是租界區,憑什么日本飛機周圍炸了一圈愣留了這么大一片盲區? 不對,不是一片盲區,而是特意留了四個點沒有炸! 見鬼了,以今天美國人的精確制導技術,都不能保證精確到這種程度,當年的日本鬼子,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樓,也不可能做得這樣精確,這樣漂亮啊。 文字介紹里也提到了這四幢樓得以保存的原因,和報道里基本一致:住在樓里的外國人打出了外國旗子,日本飛行員看到了,就沒炸。 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給出一個答案,大多數人就不會再去深究,眼前就是個例子。而作為要進行深度報道的記者,我當然不能延續這種思考的惰性。 只是不論我如何地思索,疑點越來越多,答案卻想不出一個。 首先,那是什么國旗?其次,為什么那些外國人不待在租界里,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多少面旗,如果四幢樓里都有旗升出來,那么多外國人怎么會聚集到這里來?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飛機上的飛行員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樣的戰爭狀態下,日本人高昂甚而嗜血的戰爭意志下,還能因為這小小的外國旗子就放過這四幢建筑? 再者,也是*奇異的地方,即便日軍飛行員決心放過這四幢樓,他們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樓周圍的建筑都炸得稀爛,而四幢樓卻分毫無損?難道說那時他們的飛行員,憑肉眼制導,就能把精確度控制在十米之內? 這些無解的問題在我腦海中盤旋了許久,我忽然失笑,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一個難以解釋的奇跡,難道不是讓這幢大樓保存下來的*好理由嗎?只要稍加炒作,每一個看了報道的人都會認為,這四幢當年在日軍的炸彈下神話般屹立不倒的大樓,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難道連半數都保存不下來嗎?四幢樓平凡無奇的外觀,建造者有錢人孫氏四兄弟沒有顯赫的身份,這些都將不再成為問題。 復印,然后掃描,該干的都干完以后,我把書還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圖書館。報道的主線我已經找到,文章該怎樣布局已經心中有數,接下來只要找一些經歷過當年戰火的老居民,讓他們敘說一些當年“神話”發生的細節,就大功告成了。據資料上介紹,孫氏四兄弟當年購下這四塊地皮時,曾和地皮的原主達成協議,四幢樓建成后,撥出一些房間給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樓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從這點上來看,雖然不知道孫氏兄弟是做什么買賣,此等行徑倒頗有“紅色資本家”之風。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殘存的兩幢大樓之一。在進入之前,我站在門口拍了張照,從新聞的角度講,我需要一張今天的照片來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進行對比。 和之前在書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樓近景一樣,如今站在了它面前,除了灰色的外墻讓大樓顯得老舊之外,沒有什么區別。這實在是一幢極其普通的老樓,毫無建筑上的特色,和美學、藝術之類的扯不上邊,唯一有點特別的,是這幢三層樓的樓層很高,大約相當于現在的五層樓。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張老照片作為切入點,我實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三層樓居委會”就在這幢大樓的一樓,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楊的副主任。他很熱情地向我介紹大樓的情況,只是他所說的,我大多已經了解。過了半個多小時,我才有機會打斷他的話,問起目前住在樓里的老居民有多少。 “從那時候就開始住到現在的老人啊?”楊副主任的眉頭皺了起來。 他想了想,告訴我這樣的老住戶已經很少了,樓里的住戶大多是“文革”前后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戶搬的搬、死的死,畢竟已經過了六十多年。 “這幢樓里是沒有了,后面那幢樓里還住著兩位。二樓的老張頭,還有三樓的蘇逸才蘇老先生。都是八十開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楊副主任稱呼中的細微變化,都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卻有著兩種不同的稱呼語氣。看來他對那位老張頭并不是很尊敬。 “蘇老可真是個大善人哪,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不知有多少,聽說他前前后后給希望工程捐了幾十萬,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萬塊呢。老張頭可就不一樣了,孤僻得很,不太愿意理人。”楊副主任開始向我介紹這兩位老人。 “老張頭,他叫……”我寫稿子的時候可不能這么稱呼老人家,與其當面問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還不如現在就問個清楚明白。 “他叫張輕。不過老實說我覺得這兩個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說,那么多年都是一個人過的,沒有娶妻生子,那么多年來樓里也沒人見過他們的父母或親戚,就那么一個人住在樓里。而且他們都不怎么談過去的事兒,不知會不會對你說。” 八十多歲的單身貴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這可真是罕見,而這里還一下子就出了兩個。不談過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張照片。 壓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楊副主任告辭,還沒接觸前沒什么好想的,說不定他們愿意向我這個記者說些什么。 “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見到那幢樓,離得挺遠的。”楊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問:“聽說原來四幢樓是以一幢為中心呈‘品’字形排列,現在剩下的這兩幢是哪兩幢?” “你現在要去的那幢三層樓,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這幢是外三幢中向著西北面的一幢。” 當我沿著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時候,我才明白剛才那句“挺遠的”到底有多遠。直到走到弄底,不,應該說是穿出這條弄堂,走到普濟路的時候,我才看見另一幢“三層樓”。算一下距離上一幢有一兩百米遠。 我用手搓著額頭,這情況還真有那么點奇怪。 ……
幽靈旗·把你的命交給我 作者簡介
那多,原名趙延。 2000年起開始文學創作,并憑借其超凡的想象力一舉成名。 從公務員到記者再到作者,從歷史小說到荒誕搞笑小說再到懸疑小說,那多如今已是作品總銷量數百萬冊的知名作家。 其文風詭奇多變,引人入勝。不僅蘊含著對宇宙的無限探索,也對人性的無限未知充滿熱忱和期待。想象力的束縛在他的幻想世界里消失無蹤,一切都變得有理可思,一切都充滿了哲學的深刻意味。多元化的想象元素和思考問題的獨特角度沖擊,完美融合成一篇篇文風各異的神奇故事。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回憶愛瑪儂
- >
隨園食單
- >
經典常談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李白與唐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