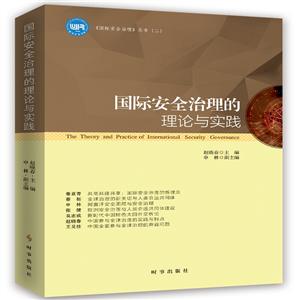預估到手價是按參與促銷活動、以最優惠的購買方案計算出的價格(不含優惠券部分),僅供參考,未必等同于實際到手價。
-
>
論中國
-
>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
>
同盟的真相:美國如何秘密統治日本
-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
-
>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四卷
-
>
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國際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0894
- 條形碼:9787519500894 ; 978-7-5195-0089-4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國際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內容簡介
本書從理論和實踐兩大方面闡述了國際安全治理之困局, 分析了國際安全治理困境之原因, 提出了應對國際安全治理之對策, 并對中國在國際安全治理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解讀。
國際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目錄
理論篇
共商共建共享:國際安全治理的新理念秦亞青()
全球治理的新關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蔡拓()
冷戰后“安全觀”的轉型王樹春()
國際安全治理中的目的性治理和無目的性治理張勝軍()
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李偉()
“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傳播與國際安全治理孫吉勝()
實踐篇
解決朝核問題的思考黃鳳志丁菱()
全球恐怖主義熱點分布與態勢感知楊溪李偉()
美國“打朝”的可能性與朝鮮半島問題的未來程亞克()
東北亞安全形勢的發展與影響孟曉旭()
簡析日本的印太體系安全治理及對中國的影響葛建華()
南亞地區安全治理的困境與出路錢峰()
阿富汗安全困局與安全治理申林張昕李炯燊()
南太地緣政治與中國的南太安全戰略劉丹()
歐洲安全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張健()
當代西歐民族分離主義問題治理的國內因素影響
李渤龐嘉元()
當前國際安全亂局與西方的“責任”張蓓()
中國篇
黨和國家歷代主要領導人的“國家安全觀”析評林利民()
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析論吳志成()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與特點趙曉春()
中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的兼容問題王靈桂()
共同體戰略與金磚合作治理的中國含義劉毅()
附錄國際安全治理論壇2017:國際安全治理與
“人類命運共同體”會議紀要()
國際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節選
國際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一、安全理念的發展:自安全、相互安全和綜合安全 從國家體系產生以來,國家安全概念就伴隨著國家主權的原則誕生了。國家安全概念是西方人提出來的,是國際安全理念的起始,基本上是以自國家為核心的安全理念,強調國家自身的絕對安全保障。也就是說,初始的國家安全概念有一個內涵性的假定,即國家可以不依賴任何其他國家而獨立獲得安全。在設計這個概念的時候,原本就是完全從自身去考慮的,就是從一種自身絕對安全的方式去考慮安全問題的,所以是一種絕對“自安全”的考量。這樣的考慮與西方的自在本體論有很強的關聯。也就是說,個體是獨立的、自在的,甚至是自為的。所以,個體是一切安全問題的根本,也是一切安全研究的起點。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6, 18 (1): 33-47 但是,國家是生活在一個國際社會之中的。任何自國家的存在都是與他國家的存在聯系在一起的,無論國家有多強的實力,這都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于是便產生了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國際安全實際上是指國家之間的安全,這已經涉及到“相互安全”的問題,但其基礎是獨立和自在的個體國家,安全也是指這個獨立自在的國家相對于其他獨立自在的國家的安全。正因為如此,國家安全威脅也就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安全受到另外國家的威脅,即“自國家”安全受到“他國家”的威脅。 到了20世紀50年代,在國際關系的發展和實踐中,國際關系學者提出了“安全困境”概念,將相互安全的概念提升到一個重要的地位。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1950, 2:157-180 安全困境指一個國家處于保護自身安全所采取的自強措施會被其他國家認定為侵犯意圖的反映和安全威脅的表現,因而其他國家也會采取相應的自強行動。結果就是自國家和他國家都陷入一種不斷采取自強措施的惡性循環:越加強自我,就越感到不安全;越感到不安全,就會越加強自我。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包含了一個反映現實并針對現實的假定,即所有安全都是相互的。相互安全的概念從理論上否定了自安全的合理性,指出任何源于自安全的實踐必然導致自我不安全。這可以說是安全困境的深刻啟示。 于是,絕對安全開始向相互安全的概念發展。即便在*嚴酷的情況下,安全也是相互的。阿克塞羅德曾經做過一個安全個案的研究。Robert Axelrod, “The LiveandLetliveSystem in Trench Warfare in World War I,” in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73-87 一戰的時候,戰壕里敵對雙方的士兵,只要上級不命令射擊,是不會主動開槍的。因為每一個士兵都知道,如果我不先開槍打對方,對方就不會先開槍打我。由于這樣一種默契,雙方的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他在這篇文章中專門討論了一戰中戰壕里的戰士為什么在很多應該開槍的時候并沒有開槍;想要說明的是,即便是敵對行為體也可以進行安全合作。冷戰時期美蘇兩家的核戰略也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當時美國人曾經提出實施“核應用戰略”(Nuclear Utilization Strategy,NUTS),這一戰略正是以自我的絕對安全為主。核應用戰略的邏輯是:我可以設立一種高效的防御體系,攔截對方的導彈,使對方不能傷害自己;但同時我的戰略武器系統卻完全可以摧毀對方。Spurgeon Kenny Jr and Wolfgang K H Panofsky, “MAD versus NUTS: Can Doctrine or Weaponry Remedy the Mutual Hostage Relationship of the Superpowers,” Foreign Affairs, 1981, 60 (2): 287-304 星球大戰戰略就是在這套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是一種以絕對自安全為考慮的安全戰略,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戰略,不但難以保證自己的安全,而且會將軍備競爭不斷推向高潮,使整個安全環境更加惡劣。所以冷戰時期美蘇雙方更多地是采用“確保相互摧毀戰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這是一個出于相互安全考慮的理念,也是一種相對合理和切實可行的戰略。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核武器防止了體系性戰爭,而是相互安全的理念使得核武器這一毀滅性武器反而成為防止戰爭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時代安全理念繼續向前發展。兩個方向發展尤為重要,一是從國家層面向個人層面延伸,可以稱為下行移動。聯合國系統提出了“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的理念和原則,反映了安全從國家向個人層面移動,也反映了國際安全自身范疇的變化。二是從國家向全球層面延展,可以說是上行移動,或稱之為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全球化時代也被很多人稱為跨國威脅時代,認為這個時代的威脅主要或者不僅僅是來自于其他國家,而是來自于一些共同的全球性危機。哥本哈根學派對安全化的討論Barry Buzan, Ole W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einner, 1998、一些學者對跨國安全威脅時代安全問題的討論Bruce Jones, 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都反映了這些安全理念的演化。總體上來講,相對于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這兩個層面,這兩個方向的安全問題又被通稱為非傳統安全,結果就是安全形態多樣化和安全范疇的拓展。我們現在討論國際安全形勢的時候常用“復雜多變”等說法,正是因為涉及到諸多方面的安全,已經不僅僅是個體國家的自安全和國家之間的相互安全,而是既涉及方方面面的安全問題,也涉及到這些安全問題的相互影響和層層疊加。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等不同安全領域之間已經高度相互關聯;國家安全、國際安全、人的安全、全球安全等不同層面的安全之間也已經密切相關。一個復雜的綜合安全格局因之形成,安全也已經成為一個綜合安全的概念。 二、民粹現實主義興起及其對安全理念的沖擊 這些年來,隨著全球化發展,民粹現實主義興起。民粹現實主義一方面是民粹主義,一方面是現實主義。民粹主義強調自民族**、本國家優先,而現實主義強調物質性實力是這種優先的重要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安全治理理念的一種倒退。 回顧全球化時代國家關系理念的重要發展,有三個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不容忽視:一是重視全球治理。全球性威脅需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主要的機制是多邊制度安排。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家是國際體系中唯一有意義的行為體,亦即國家中心論的假定,強化了國家之間相互關聯和維護全球公地的意識。二是重視國際合作。由于全球性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的,國家之間、國家與其他行為體之間的合作就成為至關重要的事情。阿克塞羅德將一戰期間戰壕戰的敵對雙方不主動向對方開槍的做法稱為相互生存合作,這是敵對雙方之間為了自我生存的合作;而面對全球問題和跨國威脅產生的合作則是國家社會面對共同威脅的合作,是共同生存合作。三是重視合作安全。安全治理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性質的重要,由于其內涵和范疇的變化,更需要以綜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為重點,以合作安全為基本原則。任何自個體的絕對安全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安全性質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民粹現實主義在安全問題上的倒退,對這些基本共識形成了強勢的沖擊。將民粹現實主義的兩個要素(自國家**和物質性實力**)結合起來,用于國際安全治理,就是重新高調提出絕對的自國家安全。這是國際安全領域一個很重要的信號,背后的假定是只考慮自安全的戰略是可以實現的。這種考慮的結果就是出臺排他性安全觀、安全戰略和安全政策。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我的核彈按鈕比你的大”等言辭和不斷進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的行動。相信國家可以獲得絕對安全,強調獲得絕對安全的途徑是增強自身的物質性實力,這些恰恰是民粹現實主義國家安全理念倒退的特征性表現。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強的國家——美國所謂的“退出”政策,換句話說就是退出全球治理,全球安全也不再是“我”的事情。這個表現方面很多,不勝枚舉。總體上說,不管表現為什么形態,出現在哪一個領域,都是一種理念上的倒退。 三、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理念 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安全治理理念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面。它包括了從國家自安全到全球安全的整個范疇,考慮了全球化時代安全性質和內涵的變化,提出了一個新的安全治理理念,明確了與之配套的行為準則和路線圖。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有幾個非常明確的特點: 一是指明了安全的前提和目標,這就是共同安全。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國際社會存在的基礎是共同存在,而不是孤立存在。這并非是不承認自個體的存在及其對安全的需求。任何一個自個體,比如國家,都是有著自身的獨立存在和自身的安全利益的。但是這種存在和利益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他個體的自身安全和自我利益、與整體的安全和利益共同存在、相互關聯的。既然自我存在與他者存在是共時共在的,那么任何一個自我對于安全的考慮必須將他者的安全置于其中;既然個體存在與整體存在是共時共在的,那么任何一個自我對于安全的考慮必須將公地的安全置于其中。中國傳統文化中“達己達人”的思想,用于安全領域便是“安己安人”。 二是提出了安全的基本原則,這就是平等安全。安全治理需要通過協商安排的過程加以實施和保障,不是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安全,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安全是不可持續的。在廣義的全球治理問題上,從來都存在多種思想和多種模式。英國作為日不落帝國時期推行的帝國式治理,是將英國的治理模式挪移到被治理的國家和地區,這顯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治理模式。均勢治理模式是在歐洲興起的,是在具有主權的國家尤其是大國之間展開的。這也不是一種平等的安全治理模式,因為均勢治理是依賴國家之間物質性實力的均衡而保持的一種戰爭陰影下的安全,大國完全可以犧牲小國的利益。霸權治理模式也是以不平等為前提條件的,因為霸權的存在本身就是強制性的保障。與這些安全治理模式相比較,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治理模式,包含了高度的正義內涵,所以也是一條可持續的安全之路。 三是強調了安全的唯一途徑,這就是合作安全。安全從本質上而言是一個雙贏和多贏的概念,因為個體在社會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與其他個體和整個社會的共同存在,自我的安全與他者的安全、與社會的安全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合作才是建立和維護安全的根本途徑。任何追求自我絕對安全的努力*終都無法得以實現,并且可能導致不斷惡化的自我安全環境,無論這一個體的自身多么強大都是如此。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在合作中尋求相互的、共同的安全。我們常說,在國際社會中鄰居是無法選擇的,鄰里之間只有選擇合作,才能真正保護自我的安全。 四是表述了安全的理想形態,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安全領域反映的是一種多元安全共同體、一種安全命運共同體。這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方面,因為它超出現在國際關系學界尤其是西方關系學界研究的安全共同體。梳理一下西方學者討論國際安全共同體的文獻,就會發現幾個重要的觀點。首先是價值的同質化。國際安全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是高度政治制度同質化,也就是說,只有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完全相同的國家才能形成這樣一個安全共同體。其次是認同的一致性。只有國家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身份認同,才能形成安全共同體。再次是政策的統一性,要求共同體成員在對外的政策上保持高度統一。Beverly Crawford, e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Community, Berkeley: Center for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Emanuel Adler, “Europe as a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67-90 到目前為止,歐盟往往被界定為這樣一種安全共同體。但是,當今的世界是多元多樣的,不可能在這些方面達成高度的一致;未來的世界也一定是多元多樣的,各個國家、民族仍然會保持自己鮮明的特性。即便是歐盟,也會出現類似英國退歐這類難以預測的事情。所以,一種更切實可行的理想安全狀態是多元安全共同體,包括不同文明類型、不同類型國家、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構成一個共同的包容開放的安全所在。 四、結語 ……
國際安全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趙曉春,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碩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理論、國際安全、日本問題。著有《發達國家外交決策制度》《日本皇室》,主編《2008年中國國家安全概覽》等,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 副主編簡介: 申林,博士,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理論、周邊國家與中國國家安全。出版學術專著一部、編著一部,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回憶愛瑪儂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推拿
- >
山海經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有舍有得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