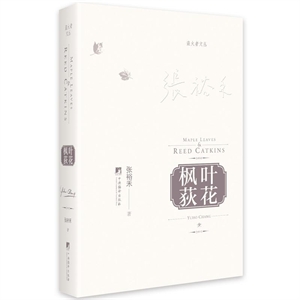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楓葉荻花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34136
- 條形碼:9787511734136 ; 978-7-5117-3413-6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楓葉荻花 本書特色
本書主要探討“文化身份”問題。這個問題在當下國際間人口流動頻繁的大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前導性。作者主攻社會學,較早提出“文化身份”的問題,并得到學界的相應。
楓葉荻花 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3輯。**輯收入9篇文章, 主要是探討“文化身份”問題。這個問題在當下國際間人口流動頻繁的大背景下, 具有一定的前導性。作者主攻社會學, 較早提出“文化身份”的問題, 并得到學界的響應。第二輯收入8篇文章, 內容集中于文學藝術的評論。第三輯名之以魁北克篇, 內容有社會學方面的 (如社會融合、身份變異等) 、文學、個人經歷等等。
楓葉荻花 目錄
自序(暫缺,待補)
**輯
一段譯事的追記
德彪西——一個為后人開辟道路的音樂家
亨德爾——一個為大眾寫作的音樂家
西方畫家的“藝術革新”與“社會反抗”
試說法國新小說
法國的“新小說”與中國的《紅樓夢》
梅特林克及其象征主義戲劇
二十世紀法國主要文學流派
第二輯
關于文化身份問題的備忘錄
跟錢林森教授談文化身份問題
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身份
從何著手研究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重構問題
家庭體制,藝術形象與文化身份
為什么不把思維方式做為文化身份的組成成分
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融合的關系
文化融合與文化多樣性的關系
第三輯
楓葉荻花秋瑟瑟
魁北克人心中的華人形象
閑話偏見、歧視及其他
二十世紀魁北克文化身份的演變
華裔作家應晨——現代小說藝術的探索者
魁北克華文文學的誕生及其發展前景
在魁華作協會上的發言
楓葉荻花 節選
《楓葉荻花》后記
——一個追夢者的自述
筆者少年時代熱愛音樂,曾想獻身音樂事業。可是經過數年努力,兩次投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失敗,這才放棄了做個作曲家的夢想。高中畢業時轉而報考外國語言文學系,想做個外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工作者。1955年,我高中畢業,報考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我如愿以償,成了北大西語系法語專業的一名學生。音樂成了我的業余愛好。我們是**屆五年制的西語系學生。學完三年本科課程后,我被分配到文學專業,又接受了兩年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的訓練。
1959年,北京大學為紀念校慶,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報告會。我受命在西語系做一個有關莫泊桑的介紹。在政治運動頻繁的五十年代,我埋首向學,系統梳理一位法國小說家的生平和著作。討論會當晚,已是深秋季節,西語系的資料室里,師生濟濟一堂。我的讀書報告已經事先油印好發給了與會者。這是我**次寫讀書報告,路子是否正確,心里一點把握也沒有。聞家駟先生發言時稱贊文章中很好地運用了辯證法。羅大岡先生發言前則先讓我站起來給大家看看。我,一個毛頭小伙子,哪里經歷過這樣的場面,緊張得渾身發熱,低著頭站起身來,也記不得當時羅先生究竟說了些什么。但,羅先生記住了我。這篇文章是我蹣跚學步邁出的**步,是篇習作,并無多少學術價值。不過,青年人總有些敝帚自珍的積習罷了,一直將油印稿留著做紀念。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生怕招來麻煩,便將其付諸一炬,化作青煙。文章內容也隨之徹底從記憶中消失了。
大學畢業后,我原本留校做研究生,這非常符合我的心愿。可是,直到1960年年底,事情還定不下來。元旦前夕,西語系派人來告訴我,我的政治審查沒有通過,因為我在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思想右傾,同情右派,沒有積極參加反右斗爭,而受到留團察看的處分。我到北大辦公樓校務處領了到上海高教局報到的紙頭,然后灰溜溜地離開了北大。到上海后,我被安排到外國語學院教書。做研究工作的夢既然碎了,便安下心來,投入法語教學工作。
1962年,我的北大同窗好友胡其鼎,時在人民音樂出版社任編輯,來信約我翻譯法國音樂家德彪西的音樂評論集子。這是我應邀翻譯的**個任務。整天陷入日常教學事務的我,可以想像,是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的。我在教學之余,全心投入《克羅士先生》一書的翻譯。譯完之后,其鼎請我恩師陳占元先生為我校閱和潤色譯文。1963年初,該書問世,受到音樂界人士的熱烈歡迎。當時中蘇關系緊張,中國樂壇在蘇俄音樂的籠罩之下頗感壓抑。法國印象派大師有關音樂藝術的論述,猶如一塊巨石扔進了一潭死水,激起了層層浪花,發出了陣陣轟鳴。可是不久,上海文匯報就發表了姚文元的大塊文章,批判德彪西的藝術觀點。老資格的賀綠汀和初出茅廬的沙葉新起而迎戰。一場無聲的、但火藥味很濃的戰斗就這樣打響了。筆戰延續了一年之久。我在1957年有過觀戰的經驗,深知戰敗的一方,必有滅頂之災。我雖有想法,哪有膽量接受文匯報記者的建議,寫成文章讓他去發表呢?一位對我有所了解的北大學姐,收到我的贈書后,特地來信關照:汝大器,當晚成。我心領神會,明白她的用意,知道自己闖禍了。從此,我韜光養晦,不再譯書,專事教書和句法研究。
1964年我暫時離開教學,被派到上海郊區奉賢縣參加四清運動。這時才有人告訴我,我從進外語學院的那天起,就被定為“控制使用”的對象,因為我受留團察看處分的檔案在我來上外報到時已經緊跟在我后面,送到了上外的團委和人事處。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未能逃過這一劫。8月18日,上外紅衛兵舉行“斗鬼會”,批判西語系主任、精通多國語言的浦允南教授。我跟其他幾十位教師和干部被押到大操場上做陪斗,頭上罩著字紙簍,跪在操場上接受紅衛兵的批判。然后,紅衛兵將所有被批斗對象的臉部用墨汁涂黑,強迫他們在大操場的跑道上爬一圈,任憑圍觀者嘲笑和辱罵。有個別南下干部不接受這樣的人身侮辱而遭到紅衛兵無情的毒打。上外校園,頓時一片恐怖氣氛。個別老教師心臟病發作者有之,跳樓自殺者有之,觸電自殺者有之……
從這天起,我便失去了“革命群眾”的身份,被列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成了隨叫隨到,接受批判的對象。批判我什么呢?**條罪狀,是翻譯了德彪西一本音樂評論集子,做了文藝黑線上的小走卒。我曾對同寢室的人說過,姚文元不懂音樂,望文生義。此話被揭發出來,批判者上綱上線,認為這是對姚文元的攻擊和污蔑。攻擊和污蔑后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人,這是何等罪惡呀?第二條罪狀,是打擊工農子弟。因為我有一位學生由于牙齒長得非常不整齊,不能正確區分開口è和閉口é的發音,我曾出于善意,建議他去請牙醫整理一下牙齒。第三條罪狀,是污蔑偉大的副統帥林彪,反對毛澤東思想,因為我說過一個人一輩子說過許多話,怎么可能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第四條罪狀,是污蔑社會主義。因為我跟同學們說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農民吃樹葉子或者餓死。
工宣隊進駐大學之后,我每天在校園里監督勞動,沒有參加政治活動的權利。連林彪逃亡事件的文件傳達,我也沒有資格聽。學生下鄉勞動,我隨班級跟學生一起勞動,干*臟*累的活。還必須戴個白色的袖章,以區別于革命群眾,就像納粹占領下的波蘭猶太人一樣,被迫穿有白底藍色六角星標志的衣服或戴有六角星標志的袖章,以表明身份。在這是非顛倒,謊言滿天飛的歲月里,不僅沒有道理可講,而且也不能實話實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語錄歌,這些愚昧的儀式和行為,把個社會搞得烏煙瘴氣。在政治高壓的態勢下,人人自危。即使有人心知肚明,可是誰又敢不跟著唱呢,跟著跳呢,跟著揮舞手中的小紅書呢?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上外接到任務,要參與世界國別史的翻譯工作。我和我的北大校友朱威烈,還有我的前輩林鼎生先生,以及我的學生王云云女士,一齊被“托管”到法漢詞典編輯組,分別從事《摩洛哥史》、《毛里塔利亞史》和《阿拉伯馬格里布史》的翻譯工作。活躍的朱威烈結識了在那里參加法漢詞典編寫工作的祝慶英女士。祝慶英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優秀中年骨干。她跟朱威烈講了以下一個故事。文革前,她去北京組稿,拜訪了法國文學研究的大家羅大岡先生。羅先生對她說:“我年歲大了,事情又多,你們為什么不去找張裕禾呢?他在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書。”祝慶英對朱威烈說:“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們早就找他幫我們翻譯法國文學作品了。”這個被前輩記住和推薦的小故事,對我這個已經靠邊站、成為革命對象的人來說,不啻是個鼓勵,讓我有勇氣堅持下去,繼續做我的文學研究夢和文學翻譯夢。
七十年代,工農兵學員陸續進入大學。我被允許重執教鞭。文革開始之后,就沒有開口說過法語。怎么去教學生說法語呢?新來的法國教師要來聽我講課,我不得不婉言謝絕。“我已經六年沒有說法語了。您來聽我的課,我會十分緊張,張口結舌。以后再請您來指教吧。”這時候重返講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工作。原因有三。一是,文化革命初期,老師是學生揭發和批判的對象,師道尊嚴的傳統被砸爛,知識分子被列為第九等,成為臭老九,精神上備受折磨,創傷嚴重。老師在學生面前謹言慎行,生怕被學生揪辮子,對學生有強烈的戒備心理。工農兵學員背后有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支持,對他們的教師監督有余,尊重不足。這樣的師生關系十分難處。其二,教師不知該如何教學生了。學習西方語言,僅僅有好的記憶,掌握詞匯和語法是不夠的,還要懂得所學語言國家的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要了解說話的語境。對語境的介紹,說多了會被人扣上宣揚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方式的帽子;不介紹吧,你會覺得沒有盡到語言教師的責任。教師很難做人:對學生要求嚴了,有人會說你修正主義回潮;對學生不管不問,你覺得有悖職業道德。其三,為了體現語言教材的革命性,教師們常到中國出版的外文雜志上選擇那些充滿政治口號的文章。外國人如果對中國政治背景和政治語匯不熟悉,是很難看懂那些政論文章的。用這樣的文章做教材,怎能教會學生外語呢?到外國報刊上挑選簡單易懂的應用文做教材,或是跟外籍教師合作編寫一些日常生活對話做教材,是當時的*佳選擇。可是,教師總覺得頭上懸著一把德謨克利斯之劍,不知什么時候會落下來砍了自己的腦袋。
1978年,鄧公重新掌舵,撥正中國這艘大船的航向,打開國門,招商引資,同時派出**批中青年業務骨干到西方國家進修訪學,以彌補十年業務荒廢造成的知識斷層。我有幸通過業務考核,被選送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美洲*古老的法語大學——拉瓦爾大學,進修法語和文學。那時的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要把白白浪費掉的十年光陰補回來。加拿大處于嚴寒地帶,一年有半年時間是冰天雪地,對于來自水鄉的我來說,既怕冷,又不會滑雪溜冰之類的戶外活動,那就只能是把自己關在溫暖的屋里讀書了。狠狠讀了兩年書,補了許多語言和文學課。
1980年,我結束進修,按時回國,帶回一大箱子的法文書籍和資料,重回上外教書。教書之余,我或譯或寫,介紹法國戰后興起的文學流派,新批評,結構主義,新小說,荒誕派戲劇,等等,以填補我們知識上的空白。本集收入的八篇介紹法國文學藝術的文章大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此外,還參加了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和世界文學家大辭典的詞條撰寫工作,以及《巴爾扎克全集》的翻譯工作。再加上授課和行政工作,雖值盛年,也覺得不堪重負。身體日漸虛弱。體格檢查,心臟開始出現問題。社會上呼吁,要改善中年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可是,要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積重難返,僧多粥少。中青年骨干,英年早逝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有兩個親戚都在五十不到的年齡先后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倒了下去。再則,這才平安了沒有幾年,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又開始了。北京有老同學警告我,內部又要擬定進行批判的黑名單了。我當時寫了一篇題為“法國的‘新小說’與中國的《紅樓夢》”的文章,旨在證明法國新小說中嘗試的寫作手法,有些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就已經使用過了。這是一篇研究藝術手法的文章,也可以算是比較文學的論文。文章交給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學報,學報拖著不發,也不退稿,就是因為聽到了風聲而“按兵不動”。整整拖了一年,直到1984年下半年才刊登出來。
楓葉荻花 作者簡介
張裕禾,1936年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1958年入文學專門化,專攻法國文學。1960年畢業后被派送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法語。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二體千字文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莉莉和章魚
- >
巴金-再思錄
- >
煙與鏡
- >
詩經-先民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