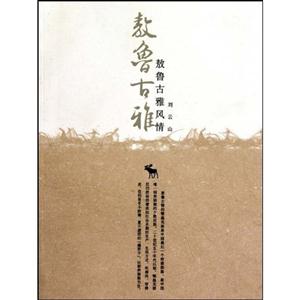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敖魯古雅風情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4091867
- 條形碼:9787204091867 ; 978-7-204-09186-7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敖魯古雅風情 本書特色
《敖魯古雅風情》推薦:敖魯古雅的鄂溫克族是中國*后一個狩獵部落,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少數民族。《敖魯古雅風情》生動的展現了鄂溫克獵民生產生活的場景,再現了生活在大興安嶺密林深處的鄂溫克獵民勤勞、善良、純樸的性格和勇敢、奔放、熱情的品質,向人們講述了*后的狩獵部落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敖魯古雅風情 目錄
敖魯古雅風情 節選
《敖魯古雅風情》介紹:敖魯古雅的鄂溫克族是中國*后一個狩獵部落,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少數民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鄂溫克獵民仍然保持著原始社會末期的生產、生活方式,吃獸肉,穿獸皮,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撮羅子”,以馴養馴鹿為生。
敖魯古雅風情 相關資料
出發前,我把能夠找到的有關鄂溫克民族的資料,全部翻閱了一遍,對居住在大興安嶺深處的鄂溫克人有了一個粗略的了解。鄂溫克民族是我國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全國只有一萬多人。“鄂溫克”一語譯成漢語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歷史上鄂溫克人一直游獵在外興安嶺和大興安嶺之間的廣大地區。史料記載,距今二百六十年前,鄂溫克的祖先就曾經在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苔蘚地區游獵生存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他們游動到了黑龍江支流阿瑪扎爾河一帶。由于沙俄侵略軍的搶掠侵擾,他們被迫南移,渡過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進人大興安嶺,棲息于現在的狩獵區。后來,一部分走出森林,來到大興安嶺西側的呼倫貝爾草原從事畜牧業;一部分進入嶺南一帶較溫暖的嫩江平原,從事農業生產;一部分則仍留在莽莽森林,從事狩獵生產。由于人口稀少,分布地域很廣,加上長期相互隔絕,生活在不同地區的鄂溫克人社會形態差異很大。其他地區的鄂溫克人早就進入封建社會,而游獵在大興安嶺的鄂溫克人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在這里,母權制時期的氏族公社組織雖已退出歷史舞臺,但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家庭公社依然存在。這種家庭公社組織,鄂溫克人叫做“烏力楞”,在烏力楞內部由有威望的老人擔任家族長,家族長和其他成員平等相處,沒有等級。烏力楞內部是公有制,生產工具為共同所有,產品平均分配。整個鄂溫克內部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居住在敖魯古雅一帶的鄂溫克獵民雖然只有一百七十多人,但他們游獵生息的地方卻相當遼闊,從北緯五十一度以北到五十三度半以南,從東經一百二十三度以西到一百二十度以東,大興安嶺幾千平方公里蒼莽浩闊的林海,都是他們張弓射獸的獵場。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他們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一樣,遭受過極為深重的苦難。沙俄侵略者殺戮殘害過他們,日本侵略軍誘騙掠奪過他們,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和奸商壓迫盤剝過他們,加上風雪嚴寒和兇禽猛獸的襲擾,使這個生長在山林中的弱小民族,長期掙扎在困苦、疾病和死亡線上。有位文學工作者曾十分形象地說:那時的鄂溫克人像是一只瀕于覆亡的殘破不堪的小舟,漂蕩在茫茫無邊的林海。解放后,黨和政府派工作組來到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他們翻山越嶺,從深山老林把鄂溫克獵民接下山來,以后又派來醫療隊為他們根治了危及民族生存的結核病。同時,建立了定居點,成立了鄂溫克族自治鄉。鄂溫克獵民從此當家做了主人,獲得了新生。讀著這些文字,像是翻著一頁頁風暴呼嘯和烽火彌漫的歷史,更加牽動了去敖魯古雅的急切心情。恨不得馬上踏進這片神奇的土地,踏著鄂溫克人從苦難走向幸福歲月的足印,同鄂溫克的父老鄉親,共同領略沐浴新生活光輝的無限喜悅。八月三十一日,我們告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呼和浩特,踏上去往大興安嶺山林中的敖魯古雅鄂溫克自治鄉的旅程。同行者有攝影記者小楊和畫報社攝影記者小方。通往敖魯古雅的旅程是遙遠的,輾轉北京,齊齊哈爾,牙克石,途中整整消磨了五個晝夜。這期間,我無時不在乘著想象的翅膀,飛臨那傳奇的千里林海,神游于獸嘯禽鳴之鄉。小楊和小方也是第一次到大森林里的鄂溫克獵鄉采訪,同樣奇想縈懷。我們每每坐在一起,共同揣度著獵村的風貌。小楊說:聽說獵民住的是能流動的帳篷房,那獵村呀,興許和點綴在錫林郭勒草原上的蒙古包和草原浩特差不多。小方說:誰說獵民住的是帳篷房?人家早就住在定居的房子里了;既然是一個村莊,又都住進房子,那一定和土默川和河套平原上那散落著土坯房的村子不會兩樣!我則認為,既是獵民村,就不會像牧區的浩特,也不會像農區的村莊,也許是既有牧區風貌又有農區特點的綜合式的風格。然而,我馬上又否定了這種猜想,因為我知道鄂溫克獵民是五十年代才從深山老林中走出來定居的,敖魯古雅獵村則是一九六七年才在野獸出沒的荒山野林中興建起來的,怎么能和發展了幾千年的農村牧區相比呢?九月四日,慢得和牛車差不了多少的森林火車,終于停在了牙林線的終點——滿歸。站臺上,一輛墨綠色的北京-212型吉普車等著我們,這是國家為接送獵民上山下山和外出上下火車專門給敖魯古雅鄉撥來的。我們乘坐的吉普車一離開站臺,很快就鉆進了莽莽蒼蒼的森林,沿著貝爾茨河左岸彎彎曲曲的沙石公路奔馳。來接我們的副鄉長那德那是一位熱情似火的蒙古族青年干部,他很理解客人的心情,一上車便像拉家常一樣談起“敖魯古雅”的由來。“敖魯古雅”是鄂溫克語,譯成漢語的意思是“一只靴子”。傳說在很早以前,一位青年獵手到這里打獵,碰上一頭雄壯的銀腿犴,青年獵手緊追在銀腿犴后面,連著放了十來槍也沒打中。等到太陽落山之后,犴鉆進一片樟松林不見了。又累又餓的青年獵人坐在地上休息時,才發現自己右腳的鹿皮靴不見了。從那以后,青年獵人整整半年沒打到一只野獸。后來有人對他說,那次你碰到的是犴仙,不該開槍,你腳上的靴子就是犴仙弄走了,你還是應該再做一只靴子送到樟松林表示“歉意”,以換回狩獵的好運。青年獵人照著辦了,從此,他每次出獵都不再空回。往后獵人們成了習慣,每年都要縫制一只精美的鹿皮靴丟到那里,時間久了,人們就把這里叫做“敖魯古雅”。自然,這是個神話,但卻真實地反映了鄂溫克人同狩獵生活相依為命的關系。“到了!”正當我們聽得入神,司機同志扭過頭來對我們說。透過公路邊上一片稀疏的白樺,獵村敖魯古雅展現在我們眼前。村子掩映在蔥蘢茂密的白樺和松樹林中,貝爾茨河像一條銀練翻著浪花從林邊流過,遠遠就可以聽到激流拍岸發出的“嘩啦嘩啦”的聲音。獵村雖然不大,但村子中間卻有一條寬廣整潔的街道。左邊是供銷社,糧站,醫院,郵電所,一色磚瓦結構的新式建筑,門面還抹上米黃色、淡藍色的水泥,同四面的森林映襯在一起,顯得格外協調,儼然是一幅美麗的畫圖。甚至有點異國情調,既像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林區風光,又有點法國巴比松畫派作品的韻味。然而,它卻真真切切是鄂溫克獵鄉的風格,是我們神奇國土上的景物。街道右邊是獵民們十分奇特的住房。這房子不僅門窗房梁是木頭的,連墻壁、房頂都是木頭的,墻壁全是一樣粗的松樹桿一根挨一根壘起,房頂蓋的是木板做成的“瓦條”。這種從頭到腳都是木頭的房子,獵民們叫做“木刻楞”。“木刻楞”是就地取材,建起來方便,但經不起大興安嶺常年風霜雨雪的侵蝕,壽命不會很長。村子東頭有四棟新蓋的紅磚紅瓦房,這是今年國家撥款為獵民修建的新居。去年自治區民委的一位領導同志到這里來調查情況,看到獵民們的“木刻楞”修建多年已經破舊,而隨著人口的增加,過去的房子已經不夠用了。因而回去以后,建議撥來了專款,為獵民修建住房,準備在三年內使獵民們全部住進新居。新建的住房都是一進三開,有臥室,廚房,客廳,里邊有地板,暖炕,火墻,還配置了寫字臺,碗櫥等,設備齊全。村子中間有一座圓頂建筑,那是獵民俱樂部,可容納四五百人,就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冬,獵民們也可坐在溫暖如春的俱樂部里看到電影和各種文藝演出。這是在附近森林里修鐵路的鐵道兵義務為獵民們修建的,上邊還工工整整寫著“愛民宮”三個大字。村子北邊是鄉人民政府所在地和設施齊全的獵民子弟學校。在村子里散步,不時可以聽到獵民子弟那清脆甜美的歌聲。隆隆的機器聲則是從東北角一片松林中傳出來的,那里是去年才興建的木材加工廠,這是獵民們為了改變單一的狩獵經濟,從當地實際出發,在附近森林工人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工廠主要是利用原始森林中將要腐爛掉的站桿倒木,加工成建筑需要的材料。去年一年這個小工廠就為獵民們增加了十萬元的收入。九月,雖不是狩獵黃金季節,可這個時期獵民大都進山,放養馴鹿,采集野果、蘑菇、木耳等山貨。因此,村子幾乎沒有閑人,獵村顯得十分寧靜,偶爾可以看到體魄健壯的老人領著剛剛學步的兒童悠閑地漫步街頭。在松風氤氳中,在夕陽輝映里,置身于林海深處的獵村,對于我們這些從繁華喧鬧的城市里來的人,簡直像一下步入了仙境!P8-19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我與地壇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