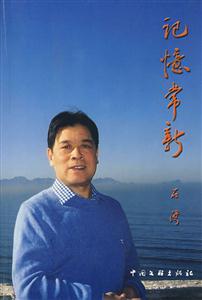有劃線標(biāo)記、光盤(pán)等附件不全詳細(xì)品相說(shuō)明>>
-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guó)”系列(珍藏版全四冊(cè))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jiǎn)⒊視?shū)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guó)大家筆下的父母
記憶常新 版權(quán)信息
- ISBN:7505957392
- 條形碼:9787505957398 ; 978-7-5059-5739-8
- 裝幀:簡(jiǎn)裝本
- 冊(cè)數(shù):暫無(wú)
- 重量:暫無(wú)
- 所屬分類:>
記憶常新 內(nèi)容簡(jiǎn)介
本書(shū)包括:紅樓故舊;不幸年代的幸運(yùn)詩(shī)篇;難得一聚;守衛(wèi)記憶;作家與作協(xié)會(huì)員;說(shuō)長(zhǎng)道短;小書(shū)大做;橫看排行榜;草臺(tái)班子;字不離文等散文作品。
記憶常新 目錄
紅樓故舊
不幸年代的幸運(yùn)詩(shī)篇
難得一聚
黃橋燒餅
楊烈宇伯伯
守衛(wèi)記憶
偶見(jiàn)梅娘
從政從文兩相宜
不辱使命
*早的話劇女明星俞珊
“這個(gè)女人很刁”
龍世煇軼事
也說(shuō)京城名編
遠(yuǎn)飛的不死鳥(niǎo)
一個(gè)古老曲種的新生
一代跤王雙德全
擦鞋卡
同在藍(lán)天下
長(zhǎng)大以后播種太陽(yáng)
第二輯
何來(lái)“驢在叫”?
作家與作協(xié)會(huì)員
詩(shī)的凈土
張學(xué)良將軍的幽禁詩(shī)詞
說(shuō)長(zhǎng)道短
小書(shū)大做
橫看排行榜
有感于楊絳“點(diǎn)煩”
獻(xiàn)身文學(xué)
“副高”之憾
藝術(shù)成本
獨(dú)苗現(xiàn)象
草臺(tái)班子
遍地畫(huà)家
城雕姓“城”
字不離文
小廣告背后的大問(wèn)題
帶血的煤和該罵的人
生死攸關(guān)
仿寫(xiě)《公仆銘》
第三輯
還鳥(niǎo)以天堂
丹頂鶴放飛
走進(jìn)朱鹮故里
成語(yǔ)典故之城
又見(jiàn)紅旗渠
大自然的樂(lè)土
比薩斜塔
“屁”錢(qián)
享受陽(yáng)光
人生公園
丹麥新童話
從桌山到好望角
后記
記憶常新 節(jié)選
紅樓故舊
去年年末,為紀(jì)念中國(guó)電影百年華誕,一座設(shè)計(jì)新穎、氣勢(shì)恢弘的中國(guó)電影博物館在京開(kāi)館,我有幸在開(kāi)館的*初幾天,去看了中國(guó)電影百年發(fā)展歷程展覽。一部中國(guó)電影發(fā)展史,像一條星漢璀璨的銀河,在觀眾的面前潺潺流淌,令人目不暇接。驀然間,一張似曾相識(shí)的明星照,跳入我的眼簾,著實(shí)令我一驚!細(xì)一看照片說(shuō)明,呀,果然是她——姚向黎!從1950年到1952年,她主演了《民主青年進(jìn)行曲》、《無(wú)形的戰(zhàn)線》、《一貫害人道》、《新兒女英雄傳》等故事片,出鏡率如此之高,這在當(dāng)時(shí)的青年演員中,極為少見(jiàn)。尤其是她在我國(guó)首部驚險(xiǎn)反特影片《無(wú)形的戰(zhàn)線》中飾演的崔國(guó)芳,是新中國(guó)電影史上**個(gè)女特務(wù)形象,給廣大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與我妻子是同事,二十多年前,曾是我家的鄰居。那時(shí),我們都住在東單三條56號(hào)院。說(shuō)是小院,其實(shí)只是一座家家都擠在樓道里做飯、共用一個(gè)水龍頭的二層小紅樓。自從1986年我搬進(jìn)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的住宅樓后,就再也沒(méi)見(jiàn)過(guò)姚向黎。猛一見(jiàn)到她年輕時(shí)代的倩影,不禁使我回想起那座已經(jīng)消失的小紅樓……
記得很清楚,我家是1969年春天住進(jìn)那座已有上百年歷史的法式小紅樓的。盡管我們*初住的一間樓下陰面的小房間僅八九個(gè)平方米,但用現(xiàn)在的話來(lái)說(shuō),那可是寸土寸金之地啊!當(dāng)時(shí)我妻子在中國(guó)青年藝術(shù)劇院工作,小紅樓就坐落在東單與王府井的中心位置,她到劇院上班,僅一二百米路,近便之極。*為有利的是,小紅樓就在協(xié)和醫(yī)院的西南角上。女兒出生的頭天晚上,我正在應(yīng)約為《北京日?qǐng)?bào)》趕寫(xiě)一篇?jiǎng)≡u(píng),因答應(yīng)第二天上班時(shí)就得交稿,妻子的腹痛雖已明顯加劇,我還直勸她再忍一忍,等我把文章的*后一段寫(xiě)完。好在協(xié)和醫(yī)院近在咫尺,急就章擱筆,我就讓妻子坐到自行車的后坐上,把她送進(jìn)了協(xié)和的產(chǎn)房。拂曉時(shí)分,女兒就順利降生了。也就是說(shuō),我女兒童年的大部分時(shí)光,是在那兒度過(guò)的。
那是一段極不平靜的歲月。女兒出生才三個(gè)月,我就下放去了“五七”干校。有一天早晨,妻子尚未起床,正給女兒喂奶,突然有一男青年破門(mén)而入,癡癡地盯著她袒露的胸部不走,她怕他行無(wú)禮之舉,便驚叫起來(lái)。幸好住對(duì)門(mén)的劇場(chǎng)經(jīng)理王明仁聞聲而至,才為她解了一難。妻子后來(lái)告訴我,那闖講我家的男青年就是姚向黎的二兒子,因高考落榜而受刺激,患了精神病。姚向黎當(dāng)時(shí)住在小紅樓的半地下室,日子過(guò)得相當(dāng)艱難,丈夫過(guò)世之后,大兒子又因患血癌而亡,小兒子還因在“文革”中失去求學(xué)機(jī)會(huì)而四處游蕩,誤入歧途……在住進(jìn)小紅樓之前,我從沒(méi)見(jiàn)過(guò)姚向黎,只聽(tīng)說(shuō)她畢業(yè)于延安魯藝,是個(gè)名演員,建國(guó)初期她主演的多部影片公映時(shí),我還在江南農(nóng)村讀小學(xué),尚不知電影為何物。加上“文革”剝奪了她再登舞臺(tái)的權(quán)利,我就失去了一睹她展現(xiàn)藝術(shù)才華的機(jī)緣。只感到她是一個(gè)待人謙恭溫良的長(zhǎng)者,與鄰居們和諧相處,總是面帶微笑地問(wèn)寒問(wèn)暖,敘說(shuō)家常。鄰居們對(duì)她的遭遇也都十分同情,多有體諒。因此,每當(dāng)她二兒子在院子里闖了什么禍,往往都瞞著她,免得她傷心落淚,又得真心實(shí)意地挨家去賠不是、道感謝……
我1973年春下放歸來(lái),母親從江南來(lái)京幫我們照看女兒,搬進(jìn)了王經(jīng)理騰出的一間20平米的房子。未料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睡夢(mèng)中,只聽(tīng)我母親驚呼:“啊呀!天搖地動(dòng)啦!”所幸小紅樓只是被震掉了東北角的一個(gè)房檐,而沒(méi)有坍塌。但在人人都成驚弓之鳥(niǎo)之日,就誰(shuí)也不敢在這危樓里住了。我家先是在長(zhǎng)安街頭住了兩個(gè)月的防震棚,后又在院部暫住了兩三年,等我們?cè)倩氐揭研蘅槻⒓庸毯蟮哪亲〖t樓時(shí),原先的住戶少了好多家,我才搬進(jìn)老演員姜祖麟騰出的兩間房子,結(jié)束了祖孫三代長(zhǎng)年擠在斗室的困境。我只知姚向黎后來(lái)調(diào)到中央戲劇學(xué)院教表演去了,但不知她在地震之后把家搬到了何處,前些年卻突然聽(tīng)到了一個(gè)令我毛骨悚然的不幸消息:她那不爭(zhēng)氣的小兒子,刑滿釋放后競(jìng)逼她交出所有積蓄不成而一怒之下把她殺害,隨后他就畏罪自殺……在中國(guó)電影博物館里展出的姚向黎的明星照是那么風(fēng)姿綽約,光彩照人,誰(shuí)會(huì)想到她生命的結(jié)局竟如此血腥和凄慘呢?
參觀中國(guó)電影博物館歸來(lái),我就從姚向黎說(shuō)起,向妻子把當(dāng)年老鄰居們的近況打聽(tīng)了一個(gè)遍。說(shuō)也巧,沒(méi)隔幾天,正好老鄰居小畢打電話來(lái)約我去她家玩牌,而邀來(lái)的新牌友,竟是大名鼎鼎的杜高先生。杜高和小畢的丈夫老程不僅建國(guó)初期在青藝共事,而且也是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難兄難弟。杜高得知老程1979年落實(shí)政策后回京,搬進(jìn)東單三條56號(hào)院時(shí)住的就是我家地震前的那個(gè)房間,便饒有興致地說(shuō):“那座小紅樓可有故事啦!解放初,那里東西兩部樓梯,樓上樓下只住四戶人家:金山、孫維世夫婦,石羽夫婦,張正宇夫婦和張逸生夫婦。”我告訴他,當(dāng)我住進(jìn)去時(shí),已變成十幾戶人家,他說(shuō)的這四對(duì)名藝術(shù)家中,就剩張逸生夫婦還在,但只留有一間大房了。杜高問(wèn):“張逸生成名也很早,你一定知道吧?”我答:“在我上大學(xué)的時(shí)候,就知道郭沫若曾尊他為‘一字師’。”
說(shuō)起“一字師”的由來(lái),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1942年4月3日晚,郭沫若的名劇《屈原》在重慶柴家巷的國(guó)泰劇院首演,臺(tái)上臺(tái)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騰的海洋,獲得了巨大的轟動(dòng)效應(yīng)。郭老很感振奮,天天親臨劇場(chǎng),不是在臺(tái)下細(xì)心觀察觀眾的反應(yīng),就是站在條幕旁和劇中的人物一同歡笑和流淚。4月5日晚,他在后臺(tái)與張瑞芳說(shuō)到嬋娟斥責(zé)宋玉的一句臺(tái)詞:“宋玉,我特別的恨你,你辜負(fù)了先生的教訓(xùn),你是沒(méi)有骨氣的文人!”郭老說(shuō):“在臺(tái)下聽(tīng)起來(lái),這話總覺(jué)得有點(diǎn)不夠味兒,似乎可以在‘沒(méi)有骨氣的’下邊再加上‘無(wú)恥的’三個(gè)字。”正在旁邊化妝的演員張逸生插了一句,說(shuō):“你是’不如改成‘你這’,‘你這沒(méi)有骨氣的文人!’那就夠了。”郭老一聽(tīng)大受啟發(fā),高聲呼好。當(dāng)晚的演出,飾嬋娟的張瑞芳就照此改了,果然贏得了預(yù)期的效果。后來(lái),郭老特地為此寫(xiě)了《一字之師》的文章,隨之傳為文壇佳話……由此,杜高先生感慨道:“有關(guān)這四對(duì)夫婦的文壇佳話可多啦!那座小紅樓拆得太可惜了。如果能保留至今,很可以當(dāng)成中國(guó)話劇的一座紀(jì)念館。”
我應(yīng)和他說(shuō):“是啊,前些年我在南京見(jiàn)到曾被打成‘胡風(fēng)分子’的老詩(shī)人化鐵,他托我回京后打聽(tīng)一位老導(dǎo)演的下落,我就先找到張逸生家去問(wèn)的。沒(méi)想到僅兩三個(gè)月后,他夫人金淑芝就去世了。”
由張逸生,杜高又和我說(shuō)到曾在東單三條56號(hào)院住過(guò)的姜祖麟、常大年、陳永驚、冀淑平等老鄰居。我告訴他,這幾位都是長(zhǎng)壽的老藝術(shù)家,且后繼有人。常大年是化妝大師,活到九十多歲,他臨去世前夕,我還見(jiàn)他騎自行車在街上轉(zhuǎn)悠,一生都活得很自在,是個(gè)樂(lè)天派。他兒子藍(lán)天如今已是知名的影視演員了。陳永驚、冀淑平夫婦的二女兒小梅是改革開(kāi)放后**批出國(guó)留學(xué)的,現(xiàn)在美國(guó)一所大學(xué)教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前年她回國(guó)探親時(shí),特意約請(qǐng)老鄰居們聚會(huì)了一次。在我的印象中,當(dāng)年她是小院里*好學(xué)上進(jìn)的女孩,在“讀書(shū)無(wú)用”的“文革”年代,經(jīng)常向我借書(shū)看,一起侃文學(xué)。赴美之后,她一直把精力用在學(xué)問(wèn)的鉆研上,直到45歲才結(jié)婚生子。她的美國(guó)丈夫比她小三歲,是個(gè)漢學(xué)家,談起中國(guó)的戲劇,也如數(shù)家珍,頭頭是道,仿佛他也從小在東單三條那座小紅樓里受過(guò)藝術(shù)熏陶一樣。小梅告訴我,他倆正在合作寫(xiě)一篇題為《青藝對(duì)中國(guó)話劇的貢獻(xiàn)》的論文,此次回國(guó)的一個(gè)重要目的,就是為收集更多的資料,包括向尚健在的張逸生、姜祖麟等老藝術(shù)家們請(qǐng)教,因?yàn)樗麄儺吘苟家讶腚q笾辏俨话鸦钤谒麄冇洃浿械恼滟F資料挖掘、搶救出來(lái),就太可惜了!
1986年,為建東方廣場(chǎng),東單三條56號(hào)院的住戶們?nèi)縿?dòng)遷,各奔東西。這些年來(lái),隨著舊城的改造,倉(cāng)促間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名人故居被拆掉了,這實(shí)在是一種歷史的遺憾。雖說(shuō)在我如今住的高層商品樓里,也住著不少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家家都安裝了防盜的大鐵門(mén),除偶然在電梯里會(huì)照上一面外,幾乎都老死不相往來(lái),再也找不到在東單三條56號(hào)院住時(shí)芳鄰間那種親如一家的氛圍了。因此,盡管那座小紅樓已經(jīng)消失,但從在中國(guó)電影博物館里見(jiàn)到姚向黎當(dāng)年的明星照后,便就激活了我的許多記憶,令我久久回想……
2006年6月2日
不幸年代的幸運(yùn)詩(shī)篇
在我的青少年時(shí)代,也即初學(xué)寫(xiě)作時(shí),只要有首小詩(shī)見(jiàn)報(bào),被人見(jiàn)了,就難免要挨幾句批,扣上一頂所謂有資產(chǎn)階級(jí)名利思想的帽子。那年月,誰(shuí)想要成名成家,仿佛就是犯罪!可是,寫(xiě)作就是有一種魔力,你愛(ài)上之后,就休想罷手。我是在高中畢業(yè)那年的暑假以石灣為筆名發(fā)表處女作的,而我進(jìn)南京大學(xué)讀的卻是歷史系,因此,時(shí)有小詩(shī)在《新華日?qǐng)?bào)》、《雨花》、《江蘇青年報(bào)》等報(bào)刊上發(fā)表,頭上就多了一頂“專業(yè)思想不鞏固”的帽子。雖說(shuō)幾乎每個(gè)學(xué)期總是迫不得已地在班會(huì)上作違心的檢討,可我依然癡迷于寫(xiě)詩(shī),到1964年畢業(yè)時(shí),我已經(jīng)在《萌芽》、《新民晚報(bào)》、《光明日?qǐng)?bào)》、《詩(shī)刊》等報(bào)刊上發(fā)表幾十首短詩(shī)了。恰好那年文化部派人到幾個(gè)名牌大學(xué)挑選戲曲編劇人才,先是中文系推薦了我,歷史系主管畢業(yè)分配的領(lǐng)導(dǎo)也就順?biāo)浦郏屛胰缭敢詢數(shù)貙?shí)現(xiàn)了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的夢(mèng)想!
我滿懷喜悅地來(lái)到向往已久的北京,辦完報(bào)到手續(xù),就直奔天安門(mén)廣場(chǎng)!大學(xué)畢業(yè)前,填寫(xiě)分配志愿表時(shí),在去向欄里,我填寫(xiě)的是“農(nóng)村文化館站”。因那時(shí)我所敬慕的詩(shī)人憶明珠和沙白,都在地、縣文化館工作。我覺(jué)得那是一個(gè)既貼近生活又有**的報(bào)刊圖書(shū)資料的創(chuàng)作基地,*能出作品、出人才。至于進(jìn)京搞專業(yè)創(chuàng)作,是我這個(gè)農(nóng)家子弟從未敢奢望的事。我曾對(duì)同學(xué)說(shuō),這一輩子要是有機(jī)會(huì)去一趟北京,那就是*大的幸福了。真的,在那個(gè)年代,天安門(mén)在外地年輕人的心中,真是遙遠(yuǎn)而又親近,神圣而又高峻……
可是,我到北京工作才一個(gè)多月,對(duì)一切都還充滿著新鮮感,就奉命下到吉林通化搞“四清”去了,一期“四清”搞完,又留在當(dāng)?shù)劁撹F廠勞動(dòng)鍛煉……隨即就是“文革”爆發(fā),搞所謂斗批改,下放到文化部團(tuán)泊洼“五七”干校勞動(dòng)改造。當(dāng)時(shí),文化部和文聯(lián)各協(xié)會(huì)都屬于“砸爛”單位,初下放時(shí),我們都以為此生不僅再也搞不了文藝創(chuàng)作,而且,怕是北京都回不去了。可以說(shuō),在團(tuán)泊洼度過(guò)的艱苦歲月里,我在心中常常默念的是聞捷的那首膾炙人口的《我思念北京》:“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像白云眷戀著山岫,清泉向往海洋,/游子夢(mèng)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在“五七”干校,我是第三批重新分配工作,回到北京的,那是1973年春天的事了。妻子比我晚回京半年。記得那年國(guó)慶節(jié),帶著我剮從蘇南老家接回的不滿四歲的女兒去天安門(mén)廣場(chǎng)和勞動(dòng)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玩,從早到晚,女兒騎在我的脖子上,我?guī)缀蹩噶怂徽欤膊挥X(jué)得累,興致之高,至今仍難以忘懷!就在那天,我萌發(fā)了強(qiáng)烈的創(chuàng)作沖動(dòng):好好寫(xiě)一首詩(shī)來(lái)歌頌天安門(mén),借此抒發(fā)我對(duì)北京、對(duì)祖國(guó)和事業(yè)的深情——
笑迎一輪紅日,
擎起萬(wàn)里晴空,
一身戰(zhàn)斗榮譽(yù),
滿懷人間春風(fēng)。
——天安門(mén)!
你昂首挺立,
雄偉莊嚴(yán),氣貫長(zhǎng)虹;
你紅燈高掛,
燦爛輝煌,光耀九重!
在我們的話語(yǔ)里,
你的名字是如此親切,
提起你便熱血沸騰,心湖奔涌;
在我們的心目中,
你的形象是那么崇高,
遠(yuǎn)勝過(guò)百丈層樓,萬(wàn)仞山峰!
我們仰望你金色的城樓,
就像見(jiàn)到祖國(guó)母親端莊的面容;
我們奔向你寬闊的廣場(chǎng),
就像撲進(jìn)祖國(guó)母親的懷中……
這是我寫(xiě)的《天安門(mén)頌》的**小節(jié),全詩(shī)共五小節(jié),二百多行,是我學(xué)寫(xiě)詩(shī)以來(lái)所寫(xiě)的*長(zhǎng)的一首政治抒情詩(shī)。1974年初夏寫(xiě)成之后,我就投寄給了《解放軍文藝》。大約是8月下旬,我突然接到《解放軍文藝》編輯部打來(lái)的電話:“我是李瑛,你寫(xiě)的《天安門(mén)頌》我們已經(jīng)編好,準(zhǔn)備在10月號(hào)上用。我給你改了幾個(gè)字,校樣就不送來(lái)給你看了,行吧?”……李瑛是我心儀已久的著名詩(shī)人之一,一聽(tīng)他報(bào)出大名,我激動(dòng)得手都微微顫抖,連聲回答:“謝謝、謝謝!”放下電話,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那期《解放軍文藝》的樣刊,是當(dāng)時(shí)剛到《解放軍文藝》當(dāng)編輯的雷抒雁親自給我送來(lái)的。翻開(kāi)一看,《天安門(mén)頌》竟然發(fā)在頭條位置上,占了整整三頁(yè),還請(qǐng)畫(huà)家配了題圖、書(shū)寫(xiě)了標(biāo)題字。抒雁說(shuō):“這一期刊物特辟了慶祝新中國(guó)成立25周年專欄,把你的詩(shī)排在首頁(yè),編輯部是經(jīng)過(guò)認(rèn)真研究后定下的,領(lǐng)導(dǎo)很重視哩!”我很感動(dòng)。因?yàn)樵诖酥埃蚁驁?bào)刊投稿,往往收到的都是鉛印的退稿信,少數(shù)稿件被采用了,也從沒(méi)有編輯署名給我寫(xiě)過(guò)信,以至當(dāng)初我在上海、北京幾家報(bào)刊上發(fā)詩(shī)時(shí)的責(zé)任編輯究竟是誰(shuí),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此次能遇上李瑛親自為我定稿,又結(jié)識(shí)了與我年齡相仿的抒雁,怎能不倍感興奮呢!
《天安門(mén)頌》發(fā)表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tái)文藝部很快就制作了配樂(lè)詩(shī)朗誦節(jié)目,朗誦者是中央戲劇學(xué)院教臺(tái)詞課的馮明義老師,節(jié)目播出后,在聽(tīng)眾和讀者中產(chǎn)生了熱烈的反響。直到1977年初我出差去長(zhǎng)沙,在省委大院里的一面墻上,仍貼著抄寫(xiě)在幾十張朱紙上的《天安門(mén)頌》。省軍區(qū)的一位文化干事告訴我,省委大院警衛(wèi)連的全體官兵,曾在晚會(huì)上集體朗誦過(guò)這首詩(shī)。到了上世紀(jì)的80年代末,剛調(diào)到作家出版社的年輕女編輯林金榮驚奇地問(wèn)我:“你就是寫(xiě)《天安門(mén)頌》的石灣嗎?我們讀初中時(shí)就集體朗誦你的詩(shī),不信,我的日記本上還抄著這首長(zhǎng)詩(shī)呢!”……無(wú)疑,《天安門(mén)頌》是我的成名作。直到近些年,還有讀者一見(jiàn)我面就問(wèn):“你原先是軍旅作家吧?什么時(shí)候轉(zhuǎn)業(yè)到地方的?”殊不知十年浩劫中文聯(lián)、作協(xié)系統(tǒng)的文學(xué)期刊全都被迫停刊了,唯有《解放軍文藝》還堅(jiān)持出刊,團(tuán)結(jié)和培養(yǎng)了一批青年作家,我成了那不幸年代的幸運(yùn)作者之一。
不過(guò),話又得說(shuō)回來(lái)。在當(dāng)時(shí)的政治氣候下,《天安門(mén)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shí)代的烙印,所夾著的某些標(biāo)語(yǔ)口號(hào)式的句子,毫無(wú)詩(shī)意不說(shuō),還帶有一種明顯的“階級(jí)斗爭(zhēng)”的色彩。這自然是不足取的。但自《天安門(mén)頌、》發(fā)表之后,向我約稿的編輯紛至沓來(lái),我在一發(fā)而不可收的情形之下,也就積重難返。因此,上世紀(jì)70年代末,同在一個(gè)創(chuàng)作組的汪曾祺先生就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對(duì)我說(shuō):“如果你還繼續(xù)寫(xiě)詩(shī),就得變法!”我在短時(shí)內(nèi)“變法”不成,進(jìn)入80年代,就索性不再寫(xiě)詩(shī),而學(xué)寫(xiě)起報(bào)告文學(xué)和散文來(lái)了。
2005年8月28日
……
……
- >
經(jīng)典常談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煙與鏡
- >
朝聞道
- >
巴金-再思錄
- >
自卑與超越
- >
中國(guó)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xué)概述
- >
企鵝口袋書(shū)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y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