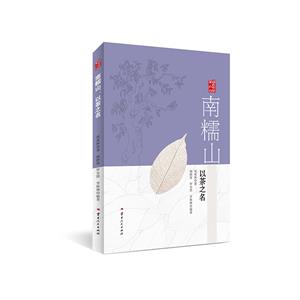-
>
兩種文化之爭 戰后英國的科學、文學與文化政治
-
>
東方守藝人:在時間之外(簽名本)
-
>
易經
-
>
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2輯
-
>
(精)唐風拂檻:織物與時尚的審美游戲(花口本)
-
>
日本禪
-
>
日本墨繪
南糯山:以茶之名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2205758
- 條形碼:9787222205758 ; 978-7-222-20575-8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南糯山:以茶之名 本書特色
經常有人問我, 云南的古茶山你都走遍了吧? 我仔細想了下,回答:“大約走了一大半,還有很多沒有去過。” 云南古茶山有多少?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們熟知的西雙版納、普洱、臨滄、保山、德宏、大理有著數目眾多的古茶山,我們不太熟悉的紅河、文山、曲靖也有古茶山。云南好些地方還有古茶園,我也是*近一段時間才知道,比如怒江,那里的老姆登茶品質還不錯。當然,昭通也有茶園,麗江也有茶園,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新建的茶園。 2022年,在官方給出的《普洱茶名山名典》里,收錄了108座云南知名普洱茶山頭。我拿著名單問過不少資深茶人,都到過沒有?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說自己都去過。這至少說明,云南知名茶山確實多,多到即便資深茶人,也有望洋興嘆之感。再一個,也沒有必要去那么多古茶山,經典的茶山就那么幾個。現在云南熱門山頭,有古六大茶山(攸樂、革登、莽枝、易武、倚邦、蠻磚),新六大茶山(南糯、布朗、勐宋、巴達、帕沙、景邁),還有冰島五寨(冰島老寨、地界、南迫、壩歪、糯伍)。許多作家,也把自己極大的熱情獻給了這些地方。 自蔣銓在《古“六大茶山”訪問記》里倡導考察茶山以來,到云南進行茶山考察已然成為茶人的一門必修課。從2004年開始,我帶著團隊沿著蔣銓的足跡,完完整整地探訪了古六大茶山,先后寫了《天下普洱》《云南茶典》《茶葉江山》《易武與古六大茶山》《新茶路:在革登與倚邦之間》。后來又對新六大茶山進行探訪,寫了《造物記:云南古茶園的秘密》《新茶路:普洱茶王老班章》。在勐庫探訪,寫了《茶葉邊疆:勐庫尋茶記》。2020年,在知名媒體人任維東先生的倡導下, 我又帶著團隊寫了《南糯山:以茶之名》。 為什么云南的茶山能夠支撐起那么持久的書寫與研究? 有三個原因。**,有歷史足夠悠久的古茶園。云南有數量眾多的古茶園,而這些古茶園的研究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空白。云南古茶園過去僅僅以資源的面貌存活,或者以某一類型的茶樹獲得過世人關注,比如各地的茶樹王,之前有著證明云南為世界茶樹原產地的需求(“茶葉之國”什么的),證明中國是資源型大國的需求(“植物王國”什么的),現在則是商業吸引眼球的需求(老班章茶王、冰島茶王都是單株價格百萬起)。這些是古茶園魅力的構成元素,但遠遠不只是這些,挖掘云南古茶園的秘密,成為近二十年來云南古茶園書寫的一大動力。這方面,云南出現了很多杰出的茶山書寫者。 第二,有歷史足夠悠久的茶葉制作與品飲傳統。云南茶山有特色鮮明的民族,他們的制茶方式、飲茶方式形成了獨到的茶俗,深深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滇紅茶制作技藝、普洱茶貢茶制作技藝、普洱茶大益茶制作技藝、下關沱茶制作技藝、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藝以及茶俗白族三道茶在2022年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云南境內,至今還保留著從茶樹種植到茶園管理的*古老的方式。在全球幾乎所有茶園都用扦插技術的今天,云南還保留著古老的種子培育,實生苗移植,藤條茶管理方式,還保留著吃鮮葉、吃老枝、用竹筒來煮茶、用竹筒來腌茶等古老的習慣。 第三,古老的茶馬古道帶來飲茶的融合與交流。如果沒有茶馬古道,如果茶樹只是長在山上,沒有人制作、品飲與消費,那么這種茶樹與其他樹有什么區別?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跡?有茶樹,有人為規模種植的古茶園,有人品飲,并把自己認為好的茶帶給周邊的人群,茶的消費圈才形成了不同的半徑,直達世界各地。在已知的國家與地區,沒有不飲茶的。比較而言,有些地方沒有咖啡,沒有酒。在已知的宗教里,也有排斥酒與咖啡的,但茶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茶一旦與一個地方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會壯大這個民族的文化,形成自己獨特的茶文化,延續千年。在老曼峨,現在結婚還要帶著竹筒茶做的茶禮去提親。這個風俗在宋代稱為“吃茶”,是婚聘要求,現在因為布朗族的留存風俗而讓我們相信宋人誠不欺我。 古茶園、古民族與古道,是我研究云南茶山的“三板斧”,呈現為文字后就是古老的制作技法、古老的茶園管理方法以及古老的飲品方式……有著追之不盡的樂趣,后來我把這個研究方法寫進了《茶馬古道文化線路研究報道》里,成為國家層面處理茶馬古道遺產的方法。 具體到南糯山,這個我無數次造訪的茶山,一直給我言之不盡的驚喜。表面上看,瀾滄江把茶區分為江內茶與江外茶,但懂行的知道,西雙版納茶山的真實分界,是從南糯山開始。 我希望你的閱讀也從南糯山開始,在這里,不僅有古老的茶園,還有古老的民族、古老的飲茶習俗。我的筆墨不能呈現出南糯山萬分之一的精彩,只懇求你有空上山隨處走走,那些美好目遇而成。 我的許多茶山知識,來自一位低調而謙遜的兄長樊露。在勐宋雨林莊園里,有一個小茶亭,我們經常坐在那里品茶聊天,他會為我們講述他對茶山的理解,對古茶園的理解,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茶是苦的,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茶是甜的,當地人是怎么看待茶的苦與甜……我仍然記得某一天,說起曼糯這個地方的時候,他說這里很奇怪,是勐海唯一一個采摘三到四葉茶的地方,很像易武。 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實地考察后,發現這里也是勐海唯一一個有藤條茶的地方。曼糯居住著布朗族,為什么這里會有藤條茶的采摘方式?我追問了很久,得出一個結論,只有在茶馬古道的要道上,才會保留藤條茶的工藝。曼糯這樣,張家灣這樣,昔歸這樣,勐庫東半山也這樣,因為他們對鮮葉的需求,一直都在的,不受外在經濟周期影響。藤條茶采摘很容易失傳,往往比鄰的村寨,一個村寨的人會,另一個村寨的人不會。它是一種繁雜的技術,很容易失傳,于是我就建議云南省非遺中心的同仁,把這門茶葉采摘技術單獨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藤條茶這種工藝與茶馬古道繁榮的這種看法,我寫《造物記:云南古茶園的秘密》時還沒有形成,所以那本書里沒有寫到。我要說的是,像樊露這樣,在一線做茶的人,他去過許多地方,看過很多茶園,他不一定會有寫作的愿望,但他對茶園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的。而像我這樣的書寫者,要做的,往往就是把這些思考與想法呈現出來。這些年,樊露資助了許多像我這樣的茶文化研究者,讓云南古茶樹被更多人看到、品飲。 雨林茶道院院長張敏是我無數次上茶山的向導,他認真、好學,是我學習的榜樣。說句過分的話,他帶過數萬人上茶山,這數字恐怕短時間內無人能超越。我的創作團隊里,楊靜茜是我在云南大學中文系的師妹,從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開始,我們共事了十多年的時間,一起去了太多的地方,寫了幾十本書(真的有那么多),是那種可以聊很多話題的小師妹。羅安然與李姝琳都是云南農業大學畢業,按照現在茶學的分類, 她們兩位才是科班出身, 所以她們的專業知識,讓我們團隊的專業知識不至于有所偏離。經常有人問我, 云南的古茶山你都走遍了吧? 我仔細想了下,回答:“大約走了一大半,還有很多沒有去過。” 云南古茶山有多少?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們熟知的西雙版納、普洱、臨滄、保山、德宏、大理有著數目眾多的古茶山,我們不太熟悉的紅河、文山、曲靖也有古茶山。云南好些地方還有古茶園,我也是*近一段時間才知道,比如怒江,那里的老姆登茶品質還不錯。當然,昭通也有茶園,麗江也有茶園,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新建的茶園。 2022年,在官方給出的《普洱茶名山名典》里,收錄了108座云南知名普洱茶山頭。我拿著名單問過不少資深茶人,都到過沒有?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說自己都去過。這至少說明,云南知名茶山確實多,多到即便資深茶人,也有望洋興嘆之感。再一個,也沒有必要去那么多古茶山,經典的茶山就那么幾個。現在云南熱門山頭,有古六大茶山(攸樂、革登、莽枝、易武、倚邦、蠻磚),新六大茶山(南糯、布朗、勐宋、巴達、帕沙、景邁),還有冰島五寨(冰島老寨、地界、南迫、壩歪、糯伍)。許多作家,也把自己極大的熱情獻給了這些地方。 自蔣銓在《古“六大茶山”訪問記》里倡導考察茶山以來,到云南進行茶山考察已然成為茶人的一門必修課。從2004年開始,我帶著團隊沿著蔣銓的足跡,完完整整地探訪了古六大茶山,先后寫了《天下普洱》《云南茶典》《茶葉江山》《易武與古六大茶山》《新茶路:在革登與倚邦之間》。后來又對新六大茶山進行探訪,寫了《造物記:云南古茶園的秘密》《新茶路:普洱茶王老班章》。在勐庫探訪,寫了《茶葉邊疆:勐庫尋茶記》。2020年,在知名媒體人任維東先生的倡導下, 我又帶著團隊寫了《南糯山:以茶之名》。 為什么云南的茶山能夠支撐起那么持久的書寫與研究? 有三個原因。**,有歷史足夠悠久的古茶園。云南有數量眾多的古茶園,而這些古茶園的研究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空白。云南古茶園過去僅僅以資源的面貌存活,或者以某一類型的茶樹獲得過世人關注,比如各地的茶樹王,之前有著證明云南為世界茶樹原產地的需求(“茶葉之國”什么的),證明中國是資源型大國的需求(“植物王國”什么的),現在則是商業吸引眼球的需求(老班章茶王、冰島茶王都是單株價格百萬起)。這些是古茶園魅力的構成元素,但遠遠不只是這些,挖掘云南古茶園的秘密,成為近二十年來云南古茶園書寫的一大動力。這方面,云南出現了很多杰出的茶山書寫者。 第二,有歷史足夠悠久的茶葉制作與品飲傳統。云南茶山有特色鮮明的民族,他們的制茶方式、飲茶方式形成了獨到的茶俗,深深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滇紅茶制作技藝、普洱茶貢茶制作技藝、普洱茶大益茶制作技藝、下關沱茶制作技藝、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藝以及茶俗白族三道茶在2022年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云南境內,至今還保留著從茶樹種植到茶園管理的*古老的方式。在全球幾乎所有茶園都用扦插技術的今天,云南還保留著古老的種子培育,實生苗移植,藤條茶管理方式,還保留著吃鮮葉、吃老枝、用竹筒來煮茶、用竹筒來腌茶等古老的習慣。 第三,古老的茶馬古道帶來飲茶的融合與交流。如果沒有茶馬古道,如果茶樹只是長在山上,沒有人制作、品飲與消費,那么這種茶樹與其他樹有什么區別?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跡?有茶樹,有人為規模種植的古茶園,有人品飲,并把自己認為好的茶帶給周邊的人群,茶的消費圈才形成了不同的半徑,直達世界各地。在已知的國家與地區,沒有不飲茶的。比較而言,有些地方沒有咖啡,沒有酒。在已知的宗教里,也有排斥酒與咖啡的,但茶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茶一旦與一個地方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會壯大這個民族的文化,形成自己獨特的茶文化,延續千年。在老曼峨,現在結婚還要帶著竹筒茶做的茶禮去提親。這個風俗在宋代稱為“吃茶”,是婚聘要求,現在因為布朗族的留存風俗而讓我們相信宋人誠不欺我。 古茶園、古民族與古道,是我研究云南茶山的“三板斧”,呈現為文字后就是古老的制作技法、古老的茶園管理方法以及古老的飲品方式……有著追之不盡的樂趣,后來我把這個研究方法寫進了《茶馬古道文化線路研究報道》里,成為國家層面處理茶馬古道遺產的方法。 具體到南糯山,這個我無數次造訪的茶山,一直給我言之不盡的驚喜。表面上看,瀾滄江把茶區分為江內茶與江外茶,但懂行的知道,西雙版納茶山的真實分界,是從南糯山開始。 我希望你的閱讀也從南糯山開始,在這里,不僅有古老的茶園,還有古老的民族、古老的飲茶習俗。我的筆墨不能呈現出南糯山萬分之一的精彩,只懇求你有空上山隨處走走,那些美好目遇而成。 我的許多茶山知識,來自一位低調而謙遜的兄長樊露。在勐宋雨林莊園里,有一個小茶亭,我們經常坐在那里品茶聊天,他會為我們講述他對茶山的理解,對古茶園的理解,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茶是苦的,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茶是甜的,當地人是怎么看待茶的苦與甜……我仍然記得某一天,說起曼糯這個地方的時候,他說這里很奇怪,是勐海唯一一個采摘三到四葉茶的地方,很像易武。 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實地考察后,發現這里也是勐海唯一一個有藤條茶的地方。曼糯居住著布朗族,為什么這里會有藤條茶的采摘方式?我追問了很久,得出一個結論,只有在茶馬古道的要道上,才會保留藤條茶的工藝。曼糯這樣,張家灣這樣,昔歸這樣,勐庫東半山也這樣,因為他們對鮮葉的需求,一直都在的,不受外在經濟周期影響。藤條茶采摘很容易失傳,往往比鄰的村寨,一個村寨的人會,另一個村寨的人不會。它是一種繁雜的技術,很容易失傳,于是我就建議云南省非遺中心的同仁,把這門茶葉采摘技術單獨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藤條茶這種工藝與茶馬古道繁榮的這種看法,我寫《造物記:云南古茶園的秘密》時還沒有形成,所以那本書里沒有寫到。我要說的是,像樊露這樣,在一線做茶的人,他去過許多地方,看過很多茶園,他不一定會有寫作的愿望,但他對茶園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的。而像我這樣的書寫者,要做的,往往就是把這些思考與想法呈現出來。這些年,樊露資助了許多像我這樣的茶文化研究者,讓云南古茶樹被更多人看到、品飲。 雨林茶道院院長張敏是我無數次上茶山的向導,他認真、好學,是我學習的榜樣。說句過分的話,他帶過數萬人上茶山,這數字恐怕短時間內無人能超越。我的創作團隊里,楊靜茜是我在云南大學中文系的師妹,從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開始,我們共事了十多年的時間,一起去了太多的地方,寫了幾十本書(真的有那么多),是那種可以聊很多話題的小師妹。羅安然與李姝琳都是云南農業大學畢業,按照現在茶學的分類, 她們兩位才是科班出身, 所以她們的專業知識,讓我們團隊的專業知識不至于有所偏離。
南糯山:以茶之名 內容簡介
本書為滇版精品出版工程項目“綠色中國茶山行”叢書之一種,從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出發,聚焦“青山”,落腳于全國茶山綠色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本書聚焦南糯山的茶山、茶事、茶人、茶食、茶生活,共分為五個部分:南糯山考察散記、南糯山考察散記、半山經濟、哈尼族品牌、哈式下午茶等。用文學的筆觸,貫通茶山古今脈絡,于茶山綠色發展中探索邊疆民族地區脫貧致富、鄉村振興的成功路徑,由知名學者、文化行者、行業領軍人物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道出中國綠色發展、云南生態文明、茶山產業提升的新時代故事。可讀性較強,具有較好的文學價值和出版價值。
南糯山:以茶之名 目錄
南糯山:以茶之名 作者簡介
周重林,學者、作家。潛心研究茶學近20年,著有多部暢銷茶學著作,代表作有《茶葉戰爭》《茶之基本》,茶文入選全國高考,各地會考、聯考。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煙與鏡
- >
隨園食單
- >
月亮與六便士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朝聞道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有舍有得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