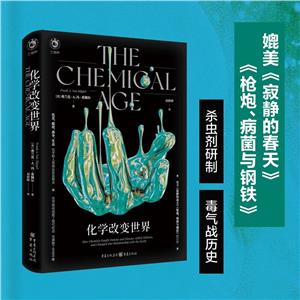-
>
上海花園動植物指南
-
>
世界鳥類百科圖鑒:亞洲鳥類/歐洲鳥類/非洲鳥類/澳洲鳥類(全五冊)
-
>
科壇趣話:科學、科學家與科學家精神
-
>
愛因斯坦在路上:科學偶像的旅行日記
-
>
不可思議的科學史
-
>
動物生活史
-
>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全新修訂版)
化學改變世界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9170752
- 條形碼:9787229170752 ; 978-7-229-17075-2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化學改變世界 本書特色
★跨學科佳作:“我們對化工產品的熱愛可能起源于神話英雄的故事,但我們也剛剛意識到它同樣帶來了普羅米修斯式的后果。”饑荒、瘟疫、戰爭、生態,化學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化學制品成就了現代社會,也威脅了生態平衡。媲美《寂靜的春天》《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生態環境與歷史的跨學科佳作。★內容真實:作者弗蘭克??A.馮??希佩爾潛心8年創作,“從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汲取靈感,以清晰的文筆寫出了一個真正發人深省的故事,揭露了歷史真相”。馮??希佩爾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詹姆斯·弗蘭克的曾外孫,作者妻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亞瑟·康普頓的侄女,祖父曾與弗里茨·哈伯、馬克斯·馮·勞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馬克斯·普朗克、古斯塔夫·赫茲、瓦爾特·能斯特等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來往密切,馮??希佩爾根據家族史料真實講述哈伯研發殺蟲劑齊克隆的過程和戰爭中的毒氣戰歷史。★發人深省:本書“融合了公共衛生、農業發展、戰爭進程和農藥研制等諸多內容”,“對科學界存在的短視行為作出了精辟而引人入勝的描述”,“化學品可以消除饑餓、對抗疾病,但濫用則可能會破壞我們的未來”。★名家推薦:多位世界知名生物生態學家強烈推薦,包括泰勒環境成就獎、藍色星球獎得主托馬斯??洛夫喬伊,斯坦福大學保護生物學中心主任保羅??埃爾利希,博物學家、現任國際野生動物保護學會負責人、世界自然基金會金質勛章得主、大熊貓科學研究和保護終身成就獎得主喬治??夏勒;《自然》 (Nature)、《新科學家》 (New Scientist)、《化學化工新聞》(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今日物理》 (Physics Today)等多本知名學術期刊重磅推薦。
化學改變世界 內容簡介
化學和歷史的走向是密不可分的,如瘧疾的治療促成了殖民主義的發展,生化武器的應用改變了戰爭的格局,殺蟲劑的大規模使用減少了馬鈴薯晚疫病所造成的饑荒。化學制品也是損害人體健康、危及物種生存的罪魁禍首。 本書結合毒理學、流行病學、歷史學和化學等多學科領域知識,生動簡明地闡述了化學是如何拯救人類于饑荒和瘟疫,又是如何通過生化武器和化學制品威脅人類健康和物種多樣性的。化學在成就現代社會的同時,也威脅到了當今的生態平衡
化學改變世界 目錄
序言 /1
**部分:饑荒 /1
1.馬鈴薯晚疫病(1586—1883)/2
第二部分:瘟疫 /25
1. 沼澤熱(瘧疾)(公元前2700—1902)/26
2. 黑嘔(黃熱病)(1793—1953)/45
3.監獄熱(斑疹傷寒)(1489—1958)/75
4.黑死病(鼠疫)(541—1922)/85
第三部分:戰爭 /111
1.戰爭中的合成化學品(公元前423年—1920年)/112
2.齊克隆(1917—1947)/134
3.滴滴涕 (1939—1950)/156
4.I.G. 法本公司 (1916—1959)/185
第四部分:生態 /213
1. 殺蟲劑抗性(1945—1962)/214
2.《寂靜的春天》(1962—1964)/230
3. 驚奇與謙卑(1962年后)/246
后記 /258
致謝 /276
化學改變世界 節選
1.馬鈴薯晚疫病(1586—1883 年) 我曾探訪過北美印第安保留地,曾經尊貴的印第安原住民如今只留下荒蕪的遺跡;我也曾深入“黑人區”,非洲黑奴仍遭受著種種打壓與奴役。而蝸居洞穴的愛爾蘭艾里斯地區居民,其不幸遭遇則是我所目睹過的*深切的痛苦,*殘酷的折磨。——詹姆斯· H. 圖克,1847 年秋 馬鈴薯是世界第四大糧食作物,在某些國家是主要的食物來源。但馬鈴薯易受蟲害,曾一度引發嚴重的饑荒。馬鈴薯與蟲害的故事展現了商業的全球化發展,饑荒與疾病的暴發,以及人們為了對抗植物病原體和害蟲而堅持不懈尋找化學制劑的努力。這些化學制劑便是殺蟲劑,可消滅啃食馬鈴薯并傳播疾病的蟲害。人類與饑餓和疾病的斗爭長達一個世紀,成效顯著,而殺蟲劑功不可沒,但它也是導致現代 戰爭和環境破壞的重要因素。要追溯殺蟲劑的歷史,不妨以馬鈴薯及其引發的愛爾蘭大饑荒為原點,聽我把這些往事一一道來。 馬鈴薯的種植始于八千多年前的安第斯山脈。當地人開發出了上千個馬鈴薯品種。一些安第斯農民可在一塊土地上同時種植 200 多個品種。16 世紀,馬鈴薯被探險家從印加帝國帶到西班牙,后至美 國佛羅里達,再由此地被殖民者帶到了弗吉尼亞。一番漫游后,馬鈴薯*終從弗吉尼亞重返歐洲。 1586 年,英國探險家沃爾特·雷利爵士的同伴托馬斯·赫里奧特爵士將馬鈴薯運到了英國。幾年后, 著名的植物學家加斯帕德·鮑欣給它起了個學名 Solanum tuberosum。Solanum(茄屬植物)源自拉丁語,意為“舒緩”或“鎮靜”,然而,這種塊莖植物的未來卻充滿了跌宕起伏。 歐洲*早種植馬鈴薯的地區是愛爾蘭的科克郡一帶,隨后歐洲大陸的農場也紛紛仿效。馬鈴薯因與含毒的顛茄同屬茄科而名譽蒙塵,被認為是麻風病和其他疾病的罪魁禍首。經過人們艱苦卓絕的努力,馬鈴薯的接受之路被逐漸拓寬,但仍舊關卡重重。雖然沃爾特·雷利爵士設法說服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允許馬鈴薯登上皇家餐桌的大雅之堂,但它始終不受待見。在 1906 年出版的有關馬鈴薯歷史的書中,作者寫道:“客人囿于禮節,不得拒絕品嘗新菜,但顯而易見,他們非常排斥,而且不遺余力地散布這種塊莖植物有毒的流言飛語。”盡管馬鈴薯早已在愛爾蘭順利扎根,但直到 1663 年,英國皇家學會才 鑒于其在饑荒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開始提倡對其的普遍種植。 在法國,經過出身行伍、德高望重的藥劑師安托萬·奧古斯丁·帕門捷不遺余力的推廣,馬鈴薯的種植才*終合法化。帕門捷在普魯士戰俘營中曾以馬鈴薯為食。回國后,他說服巴黎醫學院于 1772 年宣布馬鈴薯可以安全食用,但公眾并不買賬。帕門捷不得不采用小伎倆哄得人們相信。他得到國王路易十六的允許,派兵守衛自己的馬鈴薯地,百姓對此很是好奇。他告訴士兵們對于想嘗試馬鈴薯的人,士兵可以接收他們的賄賂,夜晚撤軍方便大家偷食。 帕門捷還用自己收獲的馬鈴薯制作美食,當時的權貴名人,如本杰明·富蘭克林等人,受邀品嘗并贊不絕口。路易十六將馬鈴薯花別在扣眼中作飾品,并下令大規模種植,極大推動了這種塊莖植物的大 眾接受度。截至 1813 年,法國中央農業學會已收集到一百多個在本國種植的馬鈴薯品種。馬鈴薯在法語中被稱為 pomme de terre,即“大地之果”。 在愛爾蘭,馬鈴薯尤為重要,因為不適宜其他農作物生長的土地都可用于種植馬鈴薯。為了掠奪土地養牛供應英國市場,英國地主將愛爾蘭農民從良田上驅逐出去。種植在荒地、沼澤甚至半山腰的馬鈴 薯,以其充足的產量和豐富的營養保證了愛爾蘭人口的爆發式增長。1779 年至 1841 年間,愛爾蘭人口增長了 172%,達到 800 萬人,成為歐洲人口*稠密的地區,其耕地人口密度甚至超過了 19 世紀中葉的中國。 愛爾蘭島人多地少,占人口 95%的農民幾乎完全依靠土地中密集播種的馬鈴薯為生,由此埋下了一個特殊的隱患。由于人口增長過快,貧窮的愛爾蘭家庭要想以小塊土地養家糊口,馬鈴薯便成為唯一 可以果腹的食物。馬鈴薯帶來自給自足,但對其長久而過度的依賴也形成了危機。在有關愛爾蘭馬鈴薯大饑荒的歷史著作中,塞西爾·伍德姆 - 史密斯曾如此評論愛爾蘭社會:“社會的宏觀結構及微觀結構,過高的人口密度,極低的生活水平,昂貴的地租,土地資源的激烈爭奪,這一切都源于馬鈴薯。” 作為*早走向全球的物種之一,馬鈴薯在 1845 年成為真菌腐爛的目標,由此引發了有史以來*嚴重的饑荒。幾乎在一夜之間,愛爾蘭農民的主食便腐爛成有毒的糊狀物。一位愛爾蘭人曾如此記述: “一個民族的所有糧食,還未成熟就全部腐爛——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英國官方對愛爾蘭的情況漠不關心,加之歧視性政策已持續了幾個世紀,1845 年愛爾蘭發生馬鈴薯晚疫病時,一場劇烈的風暴應運而生。愛爾蘭天主教與英格蘭新教之間的差異是歧視的焦點。直至 1829 年頒布《天主教解放法案》,愛爾蘭天主教徒才獲得了進入議會的權利;此前一直遵循的 1695 年刑法“旨在通過一系列殘忍的法令摧毀愛爾蘭的天主教”。天主教徒被禁止在軍隊服役、從事公共事務、投票、擔任政治職務、購買土地,甚至接受教育。根據法律條款,天主教徒死亡后,全部財產將被“分割”,土地將被分給所有的兒子,長子如改信新教,則可繼承所有遺產。 即便《天主教解放法案》在 1829 年得以通過,大多數愛爾蘭人的生活依然毫無起色。佃農們用燕麥、小麥和大麥等作物繳付地租,幾乎完全依靠土豆維持生活。愛爾蘭的社會結構阻礙了工業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即使佃農的土地增產,增產部分也屬于地主,甚至可能成為地租提高的理由,因此產業發展所需的經濟動力并不存在。地主隨意驅逐佃農,無論他們是否能夠足額繳租,而這正是愛爾蘭人的 不安全感及怨恨情緒的深刻根源。根據當時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說法,欠租,又稱“奪命颶風”,使下層階級始終處于“焦慮恐懼的狀態”,成為“壓迫的主要方式之一”。要驅逐一個家庭,便要摧毀他們的房屋,將他們從廢墟中趕出去,從藏身的溝渠和地洞中趕出去。在英國法律面前,愛爾蘭佃農如同害蟲。保守黨的上議院大臣克萊爾伯爵在談到地主時說“掠奪土地是他們的共同伎倆”。 愛爾蘭多次出現部分地區馬鈴薯歉收的情況,尤其是 1728、1739、1740、1770、1800、1807、1821、1822、1830—1837、1839、1841 及 1844 年,人們食用了大部分儲備種子,導致大范圍的饑荒與 減產。但與 1845 年 8 月至 9 月席卷愛爾蘭鄉村的馬鈴薯晚疫病相比,這些歉收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這場晚疫病首先襲擊了懷特島。 馬鈴薯晚疫病可能起源于墨西哥 , 幾世紀前向南傳播至安第斯山脈。1841—1842 年間,可能從南美洲傳到美國的大西洋北部沿岸,并于 1843 年在費城及紐約附近的沿海各州首先暴發。1843—1844 年,疫病又從美國或南美洲或兩者兼有,橫渡大洋來到了歐洲。 疫病*先可能是隨著進口馬鈴薯傳播到比利時的,這些進口馬鈴薯是為了取代那些受病毒感染以及受干腐病(由真菌鐮刀菌引起)影響的馬鈴薯;另一種可能的傳播渠道是 19 世紀 30 年代開始的鳥糞肥料生意。商船將馬鈴薯從一個半球快速運送到另一個半球,疫病也隨之在大西洋上往來穿梭。商船提速或許是造成這種狀況的關鍵因素:從 1838 年即愛爾蘭發生饑荒的 7 年前,蒸汽動力輪船開始定期橫渡大西洋。商人用來保存馬鈴薯的冰塊也進一步確保了疫病能在橫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存活”下來。 疫病可能是通過快速帆船或蒸汽船從巴爾的摩、費城或紐約——北美疫情暴發的中心——抵達愛爾蘭的。饑荒隨之而來,這些城市又成為飽受饑餓與斑疹傷寒折磨的愛爾蘭人逃亡的避難所。但美國城市的居民不同于愛爾蘭,并不依賴馬鈴薯為生。當時愛爾蘭的三十二郡則仿佛被一根長長的鋼絲繩捆在一起,當疫病“剪斷”鋼絲繩時,整個國家便分崩離析。即使已經策劃好應對方案,順利執行尚且不易,何況政府非但沒有采取措施控制饑荒的時間與范圍,與之相反的是,饑荒發生前甚至發生時政府的所作所為,更是使危機進一步蔓延,使局勢愈發惡化。1845 年,約有一半馬鈴薯歉收;1846 年,災情一發 不可收拾,人們成批死去。 幾乎是一夜之間,馬鈴薯晚疫病就席卷了整個鄉村。1846 年 7月 27 日,一位牧師記錄自己的愛爾蘭之旅時寫道:馬鈴薯“花期正旺,應該是個豐收的年份”。只一周后,返程途中路過同樣的地方,卻發現“遍地都是腐爛的植物,觸目驚心。絕望的農民隨處可見,坐在腐爛菜園的籬笆上,絞著雙手,痛苦地哀號。這場災難令他們顆粒無收”。經歷了 1845 年的饑荒,人們渴望的豐收“在短短幾天內就煙消云散”,只剩下令人作嘔的腐敗氣息。 連續兩屆英國政府,無論是托利黨還是輝格黨政府,都未能救愛爾蘭于水火之中。英國領導人認為,迅速而有效的援助會干擾自由貿易,從而惡化愛爾蘭局面,并影響英帝國的經濟發展。遠在英國本土 的“缺席地主”繼續驅逐饑餓的愛爾蘭佃農以掠奪土地,英國政府也不加干涉。由此,災難的火種形成燎原之勢,一百多萬人不堪饑餓與疾病四處流亡。 許多愛爾蘭人希望能移民到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英屬北美(加拿大)和美國,以逃離饑荒或“饑荒熱”——斑疹傷寒和回歸熱。貨船載著絕望的愛爾蘭人漂洋過海,靠岸時,四分之一、二分 之一甚至更多的乘客死于饑餓和傳染病。“船上的慘狀,”研究英國“艾琳女王號”的學者寫道,“連非洲海岸邊運送奴隸的船只都不及一二”。在利物浦、格拉斯哥、魁北克、蒙特利爾、波士頓、費城及 紐約的港口登陸后,愛爾蘭移民窩在新建的愛爾蘭貧民窟地窖內,斑疹傷寒開始在他們中間傳播。他們被視作高燒的罪魁禍首,人們對其避之唯恐不及,也因為骯臟而受人歧視。
化學改變世界 作者簡介
弗蘭克??A.馮??希佩爾:北亞利桑那大學的生態毒理學教授,曾在20多個國家講授生態學實地課程,并在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亞進行研究。
- >
月亮與六便士
- >
回憶愛瑪儂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經典常談
- >
隨園食單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姑媽的寶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