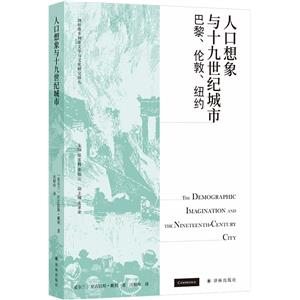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zhàn)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tài)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叢書: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44790956
- 條形碼:9787544790956 ; 978-7-5447-9095-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叢書: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 本書特色
本書將帶領(lǐng)讀者走進英國、法國、美國的核心都市,切身體驗19世紀人口大爆炸對城市文化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 從關(guān)于火山爆發(fā)的災(zāi)難敘事,到將都市想象成一個破壞者的原生態(tài)情境,再到繁榮的都市對各類動物造成的傷害,尼古拉斯·戴利在書中展示了19世紀的歐美城市文化在人口增長壓力下所發(fā)生的巨大變革 不僅適合人口學(xué)、歷史學(xué)、文學(xué)等領(lǐng)域的專業(yè)讀者,也適合對維多利亞時代發(fā)生的社會巨變感興趣的讀者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叢書: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 內(nèi)容簡介
在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中,尼古拉斯·戴利追蹤了19世紀人口大爆炸的文化影響。隨著擁擠的巴黎、倫敦、紐約等城市相繼經(jīng)歷了類似的轉(zhuǎn)變,一套針對城市生活的、共享的敘事圖景在城市居民之間廣為流傳,包括對城市災(zāi)難的幻想、關(guān)于犯罪的影視劇以及匪夷所思的公共交通故事,這一切都折射出一種所謂“他人即地獄”的想象情景。在視覺藝術(shù)中,偏向于感性的圖片開始大量出現(xiàn),將城市大眾濃縮成了少數(shù)弱勢角色:報童和花童。在19世紀末,甚至出現(xiàn)了認為這座龐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破壞者的原生態(tài)故事。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叢書: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 目錄
致 謝
引 言
**章 火山之下:大規(guī)模毀
第二章 處處可見的街道:法國通俗劇和英語本地化
第三章 幽靈來到城鎮(zhèn):鬧鬼的城市
第四章 大眾時代的識讀狂熱
第五章 毛皮和羽毛:“人類世”時代的動物和城市
結(jié) 語
注 釋
參考文獻
索 引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叢書: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 節(jié)選
引言 隨著人口的爆炸式增長,現(xiàn)代文化中出現(xiàn)了“人口想象”。換句話說,本書所關(guān)注的多模態(tài)敘事和大眾形象,出現(xiàn)在人口革命中:突然間,有更多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 我們非常熟悉19世紀人口變化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城市化。早在1851年(萬國博覽會于該年舉行),英國人口的大多數(shù)生活在“主要城鎮(zhèn)及其近郊”。1861年人口普查報告的序言指出:“雖然仍保有其鄉(xiāng)村……英國已經(jīng)具有城市人口占優(yōu)勢的特征。”到了19世紀末,法國、其他歐洲國家以及美國的城市人口也超過了各自的農(nóng)村人口。但是,除了這一被大量引用的歷史轉(zhuǎn)變,人口層面上也發(fā)生了同樣意義重大的事件,即一次名副其實的人口革命。醫(yī)學(xué)、衛(wèi)生、交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進步,尤其是工業(yè)帶來的繁榮,促使人口急劇增加。在歐洲各地,人的壽命在這一時期不斷提高。在法國,如果出生在1800年,你活到二十八歲以上,就超過了平均水平;但若出生在1910年,你很有可能活到五十歲。在英國,從1800年到1910年,平均壽命從大約三十六歲提高到五十三歲。(長壽的維多利亞女王,雖然生于1819年,卻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嬰兒的高死亡率使這些數(shù)據(jù)有些水分,但那整個世紀的總體情況是清楚的:大多數(shù)人的人生變得更長、更容易預(yù)測。正如邁克爾·安德森所說的那樣:“人們不再擔(dān)心自己會因突發(fā)的、不可預(yù)知的事件而大規(guī)模死亡。”當(dāng)然,從人口這個角度來說,**次世界大戰(zhàn),特別是1918年的流感疫情,似乎使人類社會回到了古代。但是,這只是人口增長過程中的短暫中斷。 這種人口革命通常被社會地理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和歷史學(xué)家輕描淡寫為“人口轉(zhuǎn)變”。從長遠來看,它涉及歐洲與北美從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較小的家庭規(guī)模)和低死亡率(長壽)的轉(zhuǎn)變。但是,整個19世紀,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直線下降,這意味著人口爆炸:不僅僅是城鎮(zhèn)居民增多,實際上就是人多了。在英國,這個歐洲城市化程度*高的國家,我們錯誤地想象其鄉(xiāng)村人口日漸稀少。理查德·塞內(nèi)特喚起了人們的擔(dān)憂:倫敦人口暴漲的必然結(jié)果是“大片荒涼的田地和無數(shù)破敗的村莊”。事實上,農(nóng)村人口數(shù)量相對穩(wěn)定,甚至在一些地方還有所增長,雖然沒有城市那般驚人的增長速度。1901年,英國仍有超過700萬的農(nóng)村居民,大致相當(dāng)于1801年的英國農(nóng)村居民人數(shù)。農(nóng)村看似人煙稀少,這只是因為城鎮(zhèn)增長過于迅速。1801年,倫敦居民不到100萬,到了1901年,其居民人數(shù)達到450萬(大倫敦都會區(qū)的人口為650萬),而英國總?cè)丝趶?80萬增長到3200萬以上。盡管法國人口增長相對緩慢,從2900萬增至3800萬(眾所周知,法國是較早進行生育管制的國家),而巴黎及其周邊地區(qū)的人口,從1801年的54萬多,飆升至1851年的100萬,到了20世紀初達到約270萬。當(dāng)時各國總?cè)丝谝恢痹谠鲩L,間或大規(guī)模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取代農(nóng)村生活就成了常態(tài)。在歐洲,英國一馬當(dāng)先,其人口總量幾乎翻了兩番。整個19世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人口翻了一番,德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俄羅斯的人口增長到原來的三倍。(愛爾蘭人口因饑荒和大規(guī)模移民銳減,在人口普遍呈上升趨勢之時,這明顯是個例外。)20世紀初,這種驚人的人口增長被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視為“統(tǒng)計事實”以支撐其所謂“大眾的反叛”。 事實是這樣的:從公元6世紀開始到1800年,也就是說,在12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歐洲的總?cè)丝跊]有超過1.8億。而從1800年到1914年,僅一個多世紀,歐洲的人口就從1.8億增加到4.6億!……歷經(jīng)三代人,便擴展成一個如此巨大的人類群體,像一股洪流般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地區(qū)奔涌、泛濫。 雖然*近的估算顯示,這一百多年歐洲的人口變化是從1.88億增加到4.58億,但這種巨大的變化是不可否認的:幾乎有250%的增長。我們無須深究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對大眾社會的令人沮喪的分析,而應(yīng)該認識到他指出的是意義深遠的人口變化,這一變化的方式同法國革命或工業(yè)革命一樣激烈。 像詹姆斯·比利奇*近描述的那樣,這股人類的洪流并不局限于歐洲。其中*引人注目的變化發(fā)生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以英語為母語的移民定居地。這些地區(qū)的發(fā)展,靠不斷循環(huán)的繁榮、蕭條、出口援救來拉動。(從這些年輸出的人口數(shù)量看,19世紀英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似乎更加顯著了。而事實上,這些移民成了殖民地社群的基礎(chǔ),他們將食品和原料運回祖國,又使人口增長得以持續(xù)。)例如,1900年,人口在10萬以上的美國城市中心有38個(當(dāng)時美國任何城鎮(zhèn)的人口都不超過10萬),而美國總?cè)丝趶?30萬上升到7600萬。受移民潮以及人口自然增長的驅(qū)動,紐約的人口甚至比倫敦增長得更快,但其人口基數(shù)較低,從19世紀初的大約6萬增長到1900年的300多萬。像歐洲一樣,20世紀初,美國城市總?cè)丝诔^其農(nóng)村人口。 城市人口集中,只是更廣泛的人口革命的一部分。關(guān)鍵是,它使人口革命變得明顯可見了。無論是在北美新世界還是歐洲舊世界,到處都是迅速發(fā)展起來的城鎮(zhèn),印證著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統(tǒng)計事實”。羅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在1843年就將其定義為“偉大的城市時代”,大西洋兩岸的很多后輩作家也認同這一觀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倫敦是城市之首。1891年,西德尼·韋伯注意到,倫敦的人口比愛爾蘭多,大致相當(dāng)于威爾士和蘇格蘭的人口總和;倫敦人的數(shù)量也超過挪威人、希臘人、澳大利亞人,或者瑞士人。到了1900年,大倫敦的人口比當(dāng)時整個美國的人口還要多。這種增長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加(生育率超過了死亡率)而非移民。 這種人口方面非同尋常的變化所產(chǎn)生的文化反應(yīng),我將其定義為人口想象。有鑒于此,約翰·凱里在其《知識分子與大眾》(1992)中描述的,針對人類洪流的、明確的現(xiàn)代主義敵意,僅僅是更廣泛的文化反應(yīng)的一個方面。這些反應(yīng)始于現(xiàn)代主義發(fā)生之前,并沒有單一的政治理念。19世紀的文化生產(chǎn),確實有可能歸結(jié)到人口想象的范疇。其中包括直接與人口數(shù)量相關(guān)的工業(yè)小說和貧民窟小說,如《瑪麗·巴頓》(1848)和《雅戈的孩子》,以及避開了人口革命的、有關(guān)“可知社群”的地域小說,像《米德爾馬契》(1874)。另一個方面的代表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魯濱孫式故事和帝國冒險故事。這些文學(xué)作品,如《珊瑚島》(1858),提供了從擁擠不堪的城市世界逃離的夢想。藝術(shù)方面,有故意避開人群的、描繪人煙稀少之場所的風(fēng)景畫[約翰·康斯特布爾(John Constable)],也有描繪市井萬象的城市風(fēng)俗圖(比如威廉·鮑威爾·弗里思的全景作品)。舞臺上,我們可以看到表現(xiàn)城市棄兒及其他復(fù)雜主題的情景劇(《兩個孤女》),這些戲劇被深深地打上了人口增長的烙印,就像它們被深深地打上政治和社會革命的烙印一樣。 人口革命也對各種類型的作家產(chǎn)生了更加微妙的影響。維多利亞孤兒是個象征性的角色,無論是孤獨的簡·愛和露西·斯諾、脆弱的奧利弗·退斯特,還是命運沉浮的貝基·夏普,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甚至作者本人的現(xiàn)實:露西·斯諾不是夏洛蒂·勃朗特。然而,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突然死亡,的確與19世紀早期的意外死亡精算概率相吻合,因此至少從這一方面看,露西·斯諾就是夏洛蒂·勃朗特。整整一個世紀,老齡化和長壽成為人們反復(fù)關(guān)注并參與的話題。而到了世紀末,與人口變化趨勢相一致,小說中的人物開始活得更長久,整個家庭也不再那么容易支離破碎。下面是幾個著名的例子,讓我們看看“精算”的現(xiàn)實是如何開始以想象的形式呈現(xiàn)的。在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1914)中,葛麗泰·康羅伊的戀人,工人階級的邁克爾·富里年紀輕輕便死去了,可葛麗泰·康羅伊自己卻能活到成年,有機會回想邁克爾的早逝;而加布里埃爾·康羅伊年長的阿姨們,與上一個時代的音樂大師有過直接的接觸。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1925)雖然是一部創(chuàng)作于**次世界大戰(zhàn)陰影下的小說,但它也讓我們看到了新時代的長壽。彼得·沃爾什還以為達洛維夫人的姑媽海倫娜·帕里小姐是一位去世多年、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物呢。可到了小說的結(jié)尾,在克拉麗莎的宴會上,我們終于發(fā)現(xiàn),“帕里小姐還沒死;帕里小姐還活著”(《達洛維夫人》,第233頁),她仍然熱衷于談?wù)摬闋査?middot;達爾文對她的緬甸蘭花之書的評論,而此書“1870年之前已經(jīng)出了三版”(同上書,第235頁)。同樣,經(jīng)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更大規(guī)模的屠殺之后,對生命變得更安全的普遍期望,明顯成了文學(xué)作品的預(yù)設(shè)背景。例如,在伊麗莎白·泰勒的《海港風(fēng)景》(1947)中,退休的伯特倫·海明威是*活躍的或者說*愛摻和的角色;在小說的結(jié)尾,他與離異美女托莉成雙成對,標(biāo)志著兩人生活新階段的開始。此前,仿佛是為了清楚地確認“敘事游戲”已經(jīng)有所改觀,醫(yī)生卡佐邦向他的妻子小說家貝絲(其作品中對臨終場景和葬禮的描寫廣為人知)保證,這年頭沒人必定死于肺炎。(在小說出版的兩年前,亞歷山大·弗萊明、厄恩斯特·鮑里斯·錢恩、愛德華·亞伯拉罕已經(jīng)因其對青霉素的研究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些工作對研發(fā)現(xiàn)代抗生素起到了基礎(chǔ)性的作用。) 此后,在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長壽成了常態(tài),21世紀的文學(xué)和電影都對此有所涉及。認識到人口數(shù)據(jù)的變化和“第三齡”的概念,2006年,美國人文基金會以“老年探索:有關(guān)老年的電影和文學(xué)的出現(xiàn)”為主題,在十四個州舉辦了系列講座,放映了相關(guān)影片,并展開了討論。涉及的材料包括英格瑪·伯格曼、大衛(wèi)·林奇、葆拉·馬歇爾的作品,他們都在虛構(gòu)的形式中探討了長壽的話題。除了這些明確的討論,我們還可以通過國際流行文化中日益更新的想象,來追蹤關(guān)于壽命預(yù)期的“漫長革命”。例如,如果大多數(shù)英國人還是像在1800年那么短壽,那么,《駭人命案事件簿》(1996— )中令人啼笑皆非的謀殺者就不會具有同樣的諷刺意味。如果在風(fēng)景如畫的英國村莊,死亡率像該系列小說暗示的一樣高,《駭人命案事件簿》或許仍會被當(dāng)作現(xiàn)代哥特式小說來閱讀,但絕不可能被改編為輕松愉快的電視節(jié)目。 如果用人口想象去指代自1800年以來所有人口變化帶來的文化反射,包括人口爆炸性增長、更長的壽命、更小的家庭、移民等,人口想象就勢必會涵蓋遠遠超過任何學(xué)術(shù)專著可能合理討論的范疇,從隱居鄉(xiāng)村的浪漫主義詩歌,到不斷延展的維多利亞城市小說,再到當(dāng)代好萊塢的僵尸或外星人入侵。在這里,我希望把討論的范圍縮小一些,將重點放在人口想象的**階段,即應(yīng)對19世紀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我將提出五個方面,來回應(yīng)大眾的問題。這些方面,大致可歸納為大災(zāi)變、犯罪、超自然、視覺、原生態(tài)。本書將討論三種新的文類(火山災(zāi)難敘事、犯罪劇、城市幽靈故事),并思考一種成熟的藝術(shù)類型(城市風(fēng)俗畫)是如何變化的,*后論述一種看待人口與其他物種關(guān)系的新方式的興起(反對用動物毛皮做時裝的原始生態(tài)運動)。約翰·凱里認為,正是在對“大眾”(或者被少數(shù)知識分子看作“大眾”)的敵意反應(yīng)中,實驗現(xiàn)代主義得到了發(fā)展,尤其是在1870年通過《教育法案》普及了教育之后的英國。但我認為,類似的態(tài)度,很久以前就存在了。我探討的一些主要材料都是比較出名的:例如,愛德華·利頓·布爾沃(即后來的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龐貝城的末日》(1834),繼歐仁·蘇《巴黎的秘密》(1842—1843)之后的犯罪劇,以及J. S. 勒法努和亨利·詹姆斯的城市幽靈故事;其他的材料也許不那么為人所知,比如,奧古斯都·馬爾雷迪的城市風(fēng)俗畫、“羽毛聯(lián)盟”開展的各類活動。本書主要關(guān)涉19世紀的城市想象,這一研究明確強調(diào)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統(tǒng)計事實”;它關(guān)注的不只是城市生活,而且是無處不在的絕對的數(shù)字壓力。 本書并不是一部(從政治和審美角度)描述作為集體主體的群眾的書,不是有關(guān)文學(xué)、有關(guān)19世紀公共領(lǐng)域的書,也不是分析人與城市主體關(guān)系的書。這些領(lǐng)域別人討論過,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也討論過。我在此想探討的是,人口想象如何通過文化形式來運作,而并不總是強調(diào)群眾。瓦爾特·本雅明在《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一文中認為,巴黎群眾是波德萊爾城市抒情詩的必要歷史條件:無須在詩里明確提及,巴黎群眾是他所描述的城市經(jīng)驗的決定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想法是:人口爆炸并不總是直接引發(fā)一整套文化形式,卻是其發(fā)展的基礎(chǔ)。 19世紀的人口想象是流動性的。我在這里討論的許多重復(fù)的主題,如火山災(zāi)難,是“多模態(tài)”的,跨越通俗表演、歌劇、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的類型界限;而時尚,我*后一章的主題,涵蓋了新聞、物質(zhì)文化、國際商務(wù)和日常生活。那么,我的方法必然是跨學(xué)科的。但如果我討論的這些材料不在意類別界限,那么它們中的大部分就會在不同意義上流動,且能很輕易地跨越國界。在史無前例的城市發(fā)展時期,有關(guān)城市街道的故事和圖像成為民族文化的素材,也許并不奇怪。但城市也超越了國家,有些城市主題和素材,無論屬于高雅文化還是低俗文化,都能相當(dāng)輕松地跨越語言和其他文化壁壘。這是一種國際性的(或許,更準確地說,是跨國性的)城市文化:犯罪劇將人群吸引到圣馬丁大道,也會吸引到斯特蘭德街(也稱河濱路)和波威里街;能讓梅瑞恩廣場上的讀者驚悚的讀物,也可能會使華盛頓廣場上的讀者戰(zhàn)栗;能打動皇家學(xué)院的城市風(fēng)俗畫,在紐約和布法羅也同樣受到青睞。流行的戲劇和小說被翻譯、轉(zhuǎn)載、改編,而原創(chuàng)者通常幾乎得不到什么經(jīng)濟回報;一定的城市類型主題—報童、賣花女等—在繪畫中不斷地重現(xiàn)。我的討論所涉及的這個時期,都市時尚也越來越成為跨國性的了。圖像、故事、物資,迅速穿梭在國境之間。具有異國情調(diào)的羽毛和毛皮進入了巴黎、倫敦、紐約;受到激增的法國時尚雜志和報紙專欄的慫恿,被制成別致的羽毛帽子和海豹皮大衣,之后很快運到其他城市。我們將看到,反對用動物毛皮做時裝的原始生態(tài)運動,也是跨大西洋的。 這種流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能的。因為倫敦或紐約的生活,與英國或美國農(nóng)村地區(qū)相去甚遠,而與巴黎更加接近。國與國有諸多不同,但隨著人口的增長,現(xiàn)代城市生活共有著跨國界的相似輪廓;伴隨人口增長的類似經(jīng)驗,以及有朝一日過上富裕生活的共同幻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慣習(xí)”(habitus)的趨向。這里數(shù)字又發(fā)揮了作用:1800年,倫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百萬居民的城市;到了19世紀50年代,巴黎和紐約也達到了這個規(guī)模;到了1890年,又有六個城市加入其中,包括芝加哥和費城;而到了1920年,數(shù)字增長到了二十個。*大的城市確實變得非常大,實際上變得更像國家(就其經(jīng)濟實力來說)或者說是城邦。這些“想象的共同體”擁有自己的報紙和新聞媒體,但也會分享人們在資歷更老的超級城市倫敦和巴黎的所讀、所看、所穿;而這兩個城市一直在提供城市生活的范式。沒有單一的國際城市文化,但在形形色色的城市文化之間存在著相當(dāng)高程度的相似性。 我們早就意識到這種文化國際主義的一些不對稱方面,這與帕斯卡·卡薩諾瓦在《世界文學(xué)共和國》(2004)中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卡薩諾瓦認為,到了巴黎,文學(xué)商品才是神圣的;而我則希望,本書描述的19世紀文學(xué)電路圖,沒有單一的中心。然而,巴黎對跨國人口想象的影響仍然很大,其霸主地位眾所周知。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威爾基·柯林斯、湯姆·泰勒、愛德華·布爾沃·利頓、M. E. 布拉登等,都寫過巴黎這座現(xiàn)代都市,或直接借鑒過法國文學(xué)模式。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戲劇界和時裝界一樣,法國的主導(dǎo)地位毋庸置疑。正如阿勒代斯·尼科爾在1946年寫的《十九世紀晚期戲劇史》一書中所說的那樣,1850年,英國的戲劇處于“隨意剽竊法國”階段。19世紀下半葉,這種借鑒現(xiàn)象一直持續(xù)著。尼科爾引用了珀西·菲茨杰拉德在1881年所做的悲觀評論:“現(xiàn)在可以說,英國戲劇舞臺幾乎只能靠法國戲劇支撐了。”在1897年7月發(fā)表的題為“法國入侵”的文章中,愛德華·莫頓做了同樣悲觀的評價:“當(dāng)前,世界*大帝國之首都提供的戲劇演出中有一部戲,只有一部戲是由英國著名劇作家創(chuàng)作的。”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國際版權(quán)意識薄弱的結(jié)果。查爾斯·狄更斯小說中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試圖謀求為英國劇院經(jīng)理翻譯法語戲劇的職務(wù)。他不是**個,也不是*后一個這樣做的人。例如,查爾斯·基恩在擔(dān)任公主劇院的演員兼劇團總監(jiān)的*初三年里,買了11部法語翻譯作品,總價為1135英鎊。在圣馬丁門劇院這樣的場所,不管上演了什么觀眾喜愛的戲劇,都可以迅速地翻譯并提供給阿德菲劇院或公主劇院,甚至是特魯里街劇院。同樣的戲劇,在紐約、波士頓或者費城都是筆好買賣。雖然版權(quán)意識薄弱,或者說缺乏版權(quán)意識,導(dǎo)致了這種快速流通;但是,如果城市主題和情境不為國際觀眾服務(wù),這些劇作也不會如此流行。 ……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叢書: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 作者簡介
尼古拉斯·戴利 都柏林大學(xué)英語、戲劇和電影學(xué)院現(xiàn)代英美文學(xué)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現(xiàn)代主義、浪漫與世紀末》(1999)、《文學(xué)、技術(shù)與現(xiàn)代性》(2004)、《19世紀60 年代的感性與現(xiàn)代性》(2009)等。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二體千字文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xué)叢書:一天的工作
- >
唐代進士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