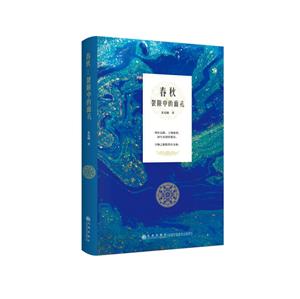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zhàn)為何爆發(fā)及戰(zhàn)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春秋:裂隙中的面孔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89905
- 條形碼:9787510889905 ; 978-7-5108-8990-5
- 裝幀:80g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春秋:裂隙中的面孔 本書特色
以諸侯爭霸的時間線為軸,歷史事件依次推進、相互勾連,脈絡得以清晰,人物面貌得以浮現(xiàn)。 人的軌跡、事的首尾,被割裂、分散在數(shù)年、數(shù)十年、數(shù)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時空中,所呈現(xiàn)的跳躍性、碎片感,難免會造成一定的閱讀難度。使各歸其位,并在其飄搖之狀中描摹、拼接,正是本書試圖去做的。
春秋:裂隙中的面孔 內(nèi)容簡介
本書以時間線為軸, 在魯隱公元年 (前722) 至魯成公十六年 (前575) 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 以某一人物或事件為點, 分析春秋時期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各國關系及整體局勢, 由點輻射至面進行闡釋。
春秋:裂隙中的面孔 目錄
菟裘空夢
——魯隱公未能抵達的遠方
東門十年
——州吁,春秋時個成功弒君篡位的公子
齊大非耦
——太子忽的傲慢,與鄭國夭折的霸業(yè)
敝笱在梁
——文姜:政治是女人能玩的游戲嗎?
二子同舟
——一點手足的溫情,一場親情的陰謀
懿公好鶴
——衛(wèi)文公,如何重建一個國家
慶父之難
——野心家的悲劇,在于權力的可望不可即
驪姬之亂
——誰是*后的勝利者?
不共楚王言
——息夫人的復仇,與楚國的野心
城濮之戰(zhàn)
——真正的霸業(yè),自戰(zhàn)火中淬煉而就
頹帶荏禍
——驅虎吞狼,周王室的尷尬與衰頹
蹇叔哭師
——崤山,秦穆公爭霸中原的折戟之地
晉靈公不君
——趙盾,踏向專權之路
邲之戰(zhàn)
——士會,晉國霸業(yè)得與失的見證者
趙氏孤兒
——繁華盛極,權力反噬
爾虞我詐
——休戰(zhàn),是奢望嗎
申公巫臣
——*可怕的復仇,是以天下大勢為籌碼
后 記
春秋:裂隙中的面孔 節(jié)選
菟裘空夢 ——魯隱公未能抵達的遠方 《左傳·隱公十一年》 (魯隱公):“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隱公十一年(前712),冬夜,魯國。一陣兵刃相接的喧嚷聲驚破了寂寥。 聲音是從大夫寪a氏的家宅之中傳來的。一伙歹人手持利刃,直奔國君息姑的住處。他們目標明確,動作迅捷嫻熟,仿佛經(jīng)過演練一般:他們早就摸清了息姑的行蹤,知道這一日他會離開宮室,知道他將入住寪氏家宅,也知道屆時守衛(wèi)薄弱,將是下手的好時機。 寒冷的夜色被刀劍點燃,敵意在一步步逼近。息姑錯愕中有些恍惚,仿佛再次回到了戰(zhàn)場之上。 十多年前,他還只是一個年輕的公子。那一日,魯宋兩國交戰(zhàn),他也在戰(zhàn)場上奮力搏殺,突然地就陷進了一片昏暗與混沌之中。他被包圍了,像是落入陷阱的獵物,只能束手就擒。而后,他被送到了宋國大夫尹氏家中囚禁。 會如何處置自己呢?他惴惴不安。正是在這個地方,他遇見了鐘巫。焦循在《春秋左傳補疏》中說:“ 鐘巫在鄭為尹氏所主祭。” 這是尹氏所祭祀的家 神,尹氏俯首祭拜,恭順而虔誠。息姑決定說服尹氏放自己走。為表誠意,息姑在鐘巫的神像面前立下誓約:“若能助我回國,日后定將奉尹氏家神為自己的神主。”有神主見證,尹氏同意了,隨他一同投奔了魯國。 那大概是他離絕境*近的一次。是鐘巫的庇佑自己才能化險為夷啊。他銘記于心,一直踐行著當日的承諾。今天,他也正是為了祭拜鐘巫才選擇了出宮。 鐘巫神像所在的園子相去寪氏家不遠,他就近住下,卻不想給了歹人可趁之機。是他大意了,他忘了,世上的兇險之地,并不獨獨是戰(zhàn)場。他再一次成了困獸,走投無路;而這一次,神主鐘巫沒能保護他。 血腥味越來越濃。這些人比當年戰(zhàn)場上的宋軍更加可怕——他們似乎專為置他于死地而來。這次是真的逃不開了。 菟裘,他忽然想到了魯國這個僻遠的小邑——他為自己擇選的隱居之所,自己本該在那里終老的。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他閉上了眼睛。 │一、繼位│ 當人間*后一絲亮光消失在眼前時,息姑看到的是弟弟允的臉孔。這張臉很陌生,此時他方驚覺,自己已很久沒有認真看過這個弟弟了。當年那個羸弱的稚子原來早已長大成人。 他與允的糾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在他成年時,父親魯惠公曾預備為他迎娶宋國國君的女兒。然而宋女至魯國后,惠公見其貌美,自納之,令他另娶。宋女生下的就是他的弟弟,是魯國的太子,允。 父奪子媳,當時不算罕見。息姑什么都沒有說,也沒有什么可說的。若是有幾分悵惘,更多的也是為父親——是不是在父親眼里,在任何的博弈之中,他都是無足輕重可隨時被犧牲的那一個;或許也正因為這一點,當年他被宋國擄走后,并未寄希望于兩國的交涉,而是選擇了私下逃回。 是的,自己不是被偏愛的那個兒子,息姑很早就接受了這個事實。所以十一年前,當命運將他與允并置于命運的分岔口時,他甚至感到了一絲受寵若驚。 公元前723年,魯惠公去世,君位空缺,該由誰來繼任,成了一道難題。按照慣例,自然是太子繼位,但此時正值魯宋兩國頻繁交戰(zhàn),而太子允年紀尚幼,無法擔此重責——立幼主無助于振奮國威,而國本不穩(wěn)必然影響前線。于是順理成章地,作為庶長子的息姑成了候選人。 他年長,穩(wěn)重,唯一招致非議的是他的出身——庶出,這先天的缺陷使得他無法理直氣壯地越過太子允去攫取君位。事實上,非議聲也不時傳入他的耳中。但這是他唯一的機會了,戰(zhàn)亂的局勢與幼年的太子,共同為他鋪就了前往*高權力的道路。如果放過,再也不會有了。 權衡之下,他做了個折中的決定以平息爭議:太子年幼,我只好代為攝政;待太子長大,自然會歸政于他。 我沒有僭越,權力只是在自己這里過渡而已。他對自己說,對那些質(zhì)疑的聲音說。他看向身邊的允,如此弱小,像是永遠不會長大一般。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了,我會交給他一個怎樣的國家呢? 無論如何,息姑成為了魯國國君,死后謚號“隱”。魯惠公去世次年,公元前722年,即魯隱公元年。《春秋》紀事自此而始。 作為魯國第十四代國君,息姑繼位于戰(zhàn)亂之中,深知戰(zhàn)爭帶來的巨大損失與破壞。他決心彌合這個傷口。 魯國雖歷史悠久,此時卻算不上強國。西周建立之初,周天子將這片土地作為周公的封地,只是周公要留在周室輔佐天子,就由其子伯禽代為赴任并建國。然而,魯國“封土不過百里”,被周邊林立的小國擠壓,又有強大的齊國威懾,加之彪悍善戰(zhàn)的夷狄不時侵擾,開疆辟土困難重重。與宋國的矛盾也多來自于此——兩國相鄰,實力又在伯仲之間。 盡管惠公晚年大敗宋軍,但息姑明白,戰(zhàn)爭的代價太大,一時的收益并不足以填補國內(nèi)的損耗。既然無法徹底壓制對方,如此耗費下去,只能是兩敗俱傷。他決定為這場戰(zhàn)爭畫上休止符,于是主動停戰(zhàn),與宋國在宿地結盟,兩國自此開始友好往來。 選擇停戰(zhàn)的另一個現(xiàn)實需求,是來自齊鄭兩國聯(lián)盟的壓力。隱公三年(前720),齊國和鄭國結成石屋之盟。齊是大國,鄭是春秋初年崛起的新秀,兩者的聯(lián)合令鄰近的諸侯國感受到了強大的壓迫。為了與之抗衡,很快,魯宋兩國重溫宿之盟,約定互為援助。 面對與自己勢均力敵甚至更為強大的國家,若沒有必勝的把握,維護平衡的局勢是必要的。當然,息姑的作為不限于此。對不同的國家,他開展了靈活的外交政策。 莒國地處魯國東側, “ 莒雖小國, 東夷之雄者也”,面積雖小,實力卻不弱。當齊魯?shù)葒萑雰?nèi)亂時,弱勢方經(jīng)常投奔這個鄰近的國家尋求庇護。后來的五霸之一齊桓公,早年就投奔過此地,并留下了“勿忘在莒”的典故。這樣的國家,必須要成為它的朋友而非敵人。為了加以籠絡,息姑還頗費了一番心思,先將公室女兒嫁往與莒國關系密切的紀國,再以紀國為介,與莒國建立了聯(lián)盟關系。 此外,息姑還主動與屬國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如邾國只是一個子爵國,地位不高,而其國君邾儀父當時未受周天子冊封,連子爵都不是,但是息姑并沒有因此輕慢于他,而是尊之重之,兩國結盟;另一個屬國戎國為東夷,主動前來示好,息姑也同樣與之舉行了盟會。 在這般苦心孤詣的聯(lián)姻加結盟政策的運作之下,魯國邊境日趨安定,民生也漸漸回歸于正軌。但是懷柔并不意味著沒有獠牙,一旦有機會,魯國也會積極地向外擴張,拓展自己的發(fā)展空間。正如整個春秋時代所展現(xiàn)的那樣,和平是權宜之計,戰(zhàn)爭才是常態(tài)。 隱公二年( 前7 2 1 ) , 魯國發(fā)動了戰(zhàn)爭, “ ( 魯國)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極國被滅,并入了魯國的版圖。那些尚未被吞并的國家,只是因為滅它們的成本太高才得以存在,而一旦受益遠大于成本,戰(zhàn)爭就在所難免。 │二、混戰(zhàn)│ 息姑很滿意這種局勢。后方穩(wěn)固,魯國在周邊小國間暗暗滲透著影響力;與中原的其他國家則相互觀望,維持著彼此間的平衡。 但這樣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裂隙*先出現(xiàn)在了鄭宋兩國之間——鄭國接納了宋國的公子馮,這個宋殤公政治上的敵手。為了將公子馮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宋國挑起了戰(zhàn)火。 隱公四年(前719),“宋公、陳侯、蔡人、衛(wèi)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被圍困的鄭國堅守不出,保存了實力,而在未來的日子里,它將用一次次的出征來雪洗這五日的恥辱;而雪洗之后,又是新一輪的報復。 東門之役,攪動了中原的風云,余波不斷,很快齊、魯、邾等國也都被卷入其中。一時之間,硝煙四起,金戈鐵蹄之聲不絕。 戰(zhàn)爭的勝敗并無定數(shù),你來我往之中,各個諸侯國漸漸都倦怠了。而且各國國內(nèi)的形勢也時常生變,戰(zhàn)爭的走向更加難以預料。只是沒有一個國家肯先停下來。這時,實力*為強大的齊國站了出來,主持召開了瓦屋之盟,令宋、鄭、衛(wèi)三國平息舊怨。 這是隱公八年(前715)的事,離東門之役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四年。 瓦屋之盟開展得還算順利。當使者將盟約的消息傳達至魯國時,息姑真心誠意地頌揚了齊僖公的德業(yè):齊君令三國冰釋前嫌,令百姓不再受戰(zhàn)亂之苦,真是莫大的功德。 面對強大的國家,他懂得順從;他也深知,這種拉鋸式的戰(zhàn)役,無法為任何一個國家?guī)韯倮芷较⑹窃俸貌贿^的。 但是這依舊是暫時的。不久,鄭、宋之間又起戰(zhàn)爭,瓦屋之盟破裂。而這次,魯國放棄了盟友宋國,站到了鄭國這邊。 其實瓦屋之盟前,魯宋兩國已經(jīng)有了嫌隙。當時宋國奪取魯國的附屬國邾國的土地,邾國又聯(lián)合鄭國伐宋,一直打到宋國外城,情勢萬分危急。作為宋國的盟國,息姑本已準備派遣援兵。可是當宋國的使者前來告急,息姑問起敵人的軍隊到達哪里之時,使者卻說尚未到達國都。明明外城已破,前來求援還如此不坦誠。一怒之下,息姑拒絕了出兵,當然言辭說得很漂亮:本應與宋共擔此危難,可是使者告知的情況與我所知不符,就此作罷。當真是因為使者的辭令錯漏嗎?也許息姑只是不愿意在這場混戰(zhàn)中陷得太深,故而以此為借口吧。 “入郛之役”,宋國顏面盡失,與魯國的關系隨之降至冰點。 但魯國似乎并不做此想——他想要宋國這個盟友,當然前提是自己處在安全的位置上。于是當瓦屋之盟鄭宋講和之后,息姑又親自率領軍隊,討伐邾國,聲稱是要替宋國報當年的“入郛”之仇。然而這番示好并沒能消除宋國對其當日不出兵援助的怨恨。 瓦屋之盟破裂之后,宋國出兵,故意不告知魯國,所謂的同盟名存實亡。于是息姑干脆斷絕了與宋國的盟友關系,加入了鄭國與齊國的陣營。此后,便是宋國的節(jié)節(jié)敗退。 息姑,只站在勝利的一方。 │三、危機│ 瓦屋之盟召開的這一年,息姑迎來了他一生之中的高光時刻:隱公八年(前715),“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祊和許這兩個地方各有其特殊的地位。《史記索隱》中道:“‘許田’,近許之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春秋谷梁傳集解》中道:“祊者,鄭伯之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祊地為鄭國所有,是周天子用來祭祀泰山的專用田,周天子在此起居、齋戒、沐浴。而許田靠近許國,為魯國所有,是魯君朝見周天子時的朝宿之邑。但無論歸屬哪個諸侯國,土地都是天子所封,不得私下相與。現(xiàn)在,鄭國借口許近鄭而祊近魯,“祊易許田”,無疑是將周天子拋在了一旁。 但這對魯國而言,卻有著更為特別的意義。“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泰山在魯國的心目中有著神圣的地位,而這次易地,無疑拉進了泰山與魯國的距離,令其祭祀之行更為順遂。 息姑很高興。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鄭國的強勢背后,隱藏著諸侯爭霸的風雨。而自己的處境,并沒有比日漸落寞的周天子要好多少。 自繼位以來,息姑始終沒能樹立起作為君王的絕對權威。他身邊,始終潛伏著一股疏離的勢力,這股勢力毫不避諱自己“不臣”之態(tài)。并非有反叛之心,只是不聽從,不合作,游離在君權控制之外。而他對此,莫可奈何——他沒有一支強有力的心腹隊伍可作依靠。 僅僅隱公元年(前722),息姑甫一即位,就出現(xiàn)了三件“非公命”之事。 “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鄭)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 非公命”,即作為臣子卻不聽從君主的命令而擅自行事,正是對君主權威的極大蔑視乃至忤逆。“不書”,指的是不見載于《春秋》。而《左傳》將這些“不書”之事加以注釋,也是表明了史家的批評與斥責。 在這股不受息姑控制的勢力之中,氣焰*為囂張的當屬權臣公子羽父。 隱公四年(前719),宋、衛(wèi)等諸侯國在圍困鄭國之后,想再次攻打鄭國,“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息姑拒絕了宋國的出兵請求,而羽父卻公然違抗了君命。“固請而行”四個字,更可見息姑的忍讓與羽父的專橫。但息姑不得不對他有所忌憚,因為這位權臣手中掌握著軍隊。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魯國國力漸強,息姑也在逐步地將權力收歸手中。時間很快來到了隱公十一年,息姑生命中的*后一年。 這一年,他和羽父的君臣關系似乎走向了融洽,配合日益默契。滕侯、薛侯來魯國朝拜,為先后的問題產(chǎn)生爭執(zhí),息姑令羽父加以平息,一副君仁臣忠的模樣。 同年,息姑頻繁會見鄭莊公,兩國聯(lián)合齊僖公攻打許國并獲得了勝利。齊僖公將獲得的許國土地讓給息姑,息姑卻送給了鄭莊公,并說了一番漂亮的話:“因您說許國不交納貢品,我才跟隨討伐;如今許國既已認罪,您的好意我不敢領受。”這番舉措,為他同時贏得了齊鄭兩個強國的信任與支持。 一切都正在往更好的方向前行,他理想中那個強大的魯國正在逐步成為現(xiàn)實,而自己這些年的苦心經(jīng)營,也將得到回報。但是令他猝不及防的是,這些很快就戛然而止——十多年前埋下的隱患還是浮現(xiàn)了出來。而挖掘這個隱患并將之引爆的,正是羽父。 這年的冬天,羽父鄭重地向息姑提出了殺掉太子允的建議。作為老謀深算的權臣,他看到了息姑的能力。魯國在變強,一同強大的,還有羽父手中的權力。他想要延續(xù)這樣的君臣模式,更準確地說,想要在原來君臣模式中,為自己謀求更大的權力——他已擁有了兵權,現(xiàn)在,又盯上了主持內(nèi)政的太宰之職。 羽父以為自己洞察了息姑的心思。雖然繼位時,息姑聲稱只是代為攝政,總有一日會將權力交還給太子允,可確切是哪一天,恐怕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十一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他已經(jīng)熟悉了這個位子,習慣了這個位子,難道不會想再坐得久一些嗎?當年的稚子已經(jīng)成人,也不見他有何兌現(xiàn)諾言的動作。是啊,既然已經(jīng)在這個位子上了,何不坐得更安心更安穩(wěn)一些呢?沒有比干掉對手更穩(wěn)妥的法子了。息姑一定是這么想的,只是缺乏一點信心、缺乏一點動力而已。那么,不如由自己來推他一把。 于是羽父主動示好,表示自己愿意為息姑除去這個后顧之憂。但他的這番熱誠迎來的是當頭棒喝。息姑拒絕了,言辭和他繼位時說的如出一轍,“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四、身死│ 菟裘是魯國邊遠的小邑,息姑想好了,等將君位交給太子允后,便在那里安置好田宅,平靜地度過余下的歲月。這是他為自己留的退路。 他應該是真心的,雖然君主的權勢誘人,但他一直是一個厚道、重信諾的人。他規(guī)矩地履行著君王的職責,也真誠地對待著身邊的人。 當年他在宋大夫尹氏家許諾,順利回國后將祭祀其家神鐘巫,他做到了;當日入郛之役,他因宋國使者謊報軍情,怒而拒絕出兵,其中未必沒有幾分率性與真切。 在位期間,他曾不顧大臣臧僖伯的勸誡,執(zhí)意“如棠觀魚者”——去棠這個地方觀看捕魚——臧僖伯認為這有違禮法。數(shù)月后,臧僖伯去世,息姑想起此事,非常后悔,認為自己辜負了臧僖伯赤誠的忠心。為此,他特意將其葬禮在原來的規(guī)格上加了一級,以示悼念與褒揚。 他對名分之事也慎重以待。自己的母親去世后,“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春秋》上也只記載“君氏卒”。而對允的母親,他則為她立廟并祭祀。因其是夫人,也是未來國君允的生母。 所以,他認為自己規(guī)行矩步,行事坦蕩,問心無愧。然而他似乎真的忘了,權力的爭奪本身就是一場極為野蠻殘酷的游戲。當那個駭人的建議說出口時,他與羽父都已經(jīng)沒有了退路,至少羽父不會給他退路。他卻以為什么都沒有變,將此事想得過于幼稚與天真。于是才有了那一天,他如常出宮祭奠鐘巫,毫無戒備。 沒有退路的羽父其實也是被逼到了絕境上。他畢竟只是個臣子,若他日太子允登上君位,聽聞他曾如此進言,他會是什么下場呢?遂當機立斷,決定先下手為強。他轉而密告允,稱息姑有害他之心,不如早做準備,并表示愿為馬前卒。 允心動了。君主之位離自己只有一步之遙,而這一步他已經(jīng)等得太久了。這么多年,自己就像個透明的人,隱匿在息姑的影子下。自己什么時候能擺脫這個影子呢?他不知道,也不敢問。現(xiàn)在機會來了,他不想在不確定上再等待下去了。況且這個位子,原本就是自己的。 次月,冬夜,歹人攻破了大夫寪氏的家門。 息姑或許覺得自己有些冤枉,但他其實并非全然無辜。他似乎忘了前車之鑒,忘了周朝初建時,他的先祖周公也曾面臨相似的處境,甚至處境更為艱難。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去世,當時滅商不久,局勢未定,周成王幼小,就由武王之弟周公代為攝政。而這引起了武王其他幾位弟弟管叔、蔡叔等人的不滿。他們散布流言,說周公意圖對成王不軌。隨后與商朝后裔武庚暗中勾結,起兵叛亂。周初的不少地方原本就是商朝舊邑,聞訊也紛紛附和。 面對其他輔政大臣的疑慮,管、蔡等人以及商朝后裔的異心,周公果斷地誅殺了管叔與武庚,放逐了蔡叔,平定了叛亂;在七年后,將一個安定有序的周王朝交付給成王,才徹底地證實了自己的清白。 以周公的聲望與才干,武王去世后,他是*適合代為攝政的人選。即便如此,當他“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時,依舊要遭受如此嚴重的猜疑及流言蜚語。千年后,杜甫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并非虛言。而僅僅三百年后,他的子孫息姑卻渾然不覺,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條危險的道路上。 沒有足夠的威望,也缺少足夠的魄力,甚至沒有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警惕心,息姑卻妄想著自己能夠全身而退。 如果,如果他能往前一步,果決狠辣一些,如羽父所言的那樣鏟除后患,鏟除有異心的貴族勢力,未必不能開啟屬于自己的時代。又或者,他甘愿退讓,能毫無回避、坦誠地與太子允交涉關于讓位的事宜,也未嘗不能取得諒解而避免手足相殘的悲劇。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能力所限,性格所限,他只能止步于此。 │五、尾聲│ 息姑死了。 寪氏成了替罪羊,也不過是做個象征性的討伐,*后不了了之。誰是躲在幕后的那個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只是無人敢去深究。 息姑被剝奪了作為君主的尊嚴,甚至沒能以國君之禮下葬,謚號也只是一個尷尬的“隱”字。“不尸其位曰隱”,史筆暗諷他徒居其位而無突出作為。這對他顯然是不公平的,保境安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許他至死都心懷理想與天真,暢想著能成就一段兄友弟恭的佳話,但是世事豈能盡如人意。攝政十一年而不歸政,原本就脆弱的兄弟情,如何經(jīng)得起這漫長的時間考驗,如何能躲得過人心的猜疑與離間。 他不是周公,歷史沒能證明他的清白。 他沒能去成菟裘,這場夢怕是永遠也無法抵達了。
春秋:裂隙中的面孔 作者簡介
朱夏楠,出生于浙江寧波,畢業(yè)于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現(xiàn)為文學雜志編輯。曾參與《中國文學年鑒》“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綜述”及相關著作評介的撰寫工作,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先秦傳播研究項目的文本整理工作。入選浙江省第五批“新荷計劃人才庫”。作品散見于《作家》《詩刊》《美文》《青年文摘》等。
- >
姑媽的寶刀
- >
名家?guī)阕x魯迅:朝花夕拾
- >
莉莉和章魚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經(jīng)典常談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史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