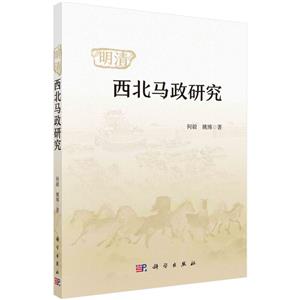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明清西北馬政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00575
- 條形碼:9787030700575 ; 978-7-03-070057-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明清西北馬政研究 內容簡介
馬政,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國家的行政制度,即國家對官用馬匹的采辦、牧養、訓練和使用所實施的管理制度。自秦漢以降,迄于明清,它一直是歷代兵制、驛傳和財賦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西北馬政研究,自然也是考察明清兵制、驛傳和財賦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明清西北馬政研究,又廣泛涉及西北五省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同樣也是考察明清西北地區歷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明清兩代政治經營西北地區的當否。
明清西北馬政研究 目錄
緒論 1
上編
**章 明代馬政視野下的西北馬政 16
一、明代君臣重視馬政 16
二、明代的馬政體系 18
三、西北馬政的主要機構 20
第二章 明代西北仆苑變遷與茶馬職官演變 27
一、中晚明行太仆寺的職官演變 27
二、中晚明苑馬寺的變遷與成因 28
三、督理西北茶馬的差官變化 37
第三章 明代西北的仆苑官牧之制 39
一、牧馬草場 39
二、牧馬軍人 41
三、馬價 44
四、營衛放牧 48
五、仆苑孳牧 49
六、印烙 51
七、關換 53
八、比較 54
九、買補 55
十、禁約 57
第四章 明代西北官用馬匹之采辦途徑 59
一、茶馬與貢馬 59
二、商人中鹽納馬 63
三、銀鈔市馬 66
四、絲綢布帛易馬 68
五、馬市互易 69
第五章 明代的茶馬、貢馬制度及性質 77
一、茶價、馬價與茶馬易例 77
二、番族納馬之制 79
三、番族貢馬之制 84
四、納馬與貢馬性質 86
第六章 中晚明對西北馬政的整飭 88
一、中晚明西北馬政之弊端與緣由 88
二、弘治、正德朝楊一清對西北馬政的修復 95
三、嘉靖以降西北馬政的失控之勢 103
下編
第七章 清代馬政視野下的西北馬政 115
一、清代君臣重視馬政 115
二、清代的馬政體系 121
三、西北馬政的主要內容 125
第八章 清代西北茶馬與官牧之制 127
一、茶價、馬價與茶馬易例 127
二、西北茶馬司的嬗變 129
三、對西北現役軍馬的管理 133
四、綠營、八旗馬廠之制 136
第九章 清代西北官馬的采辦途徑 145
一、貢馬 145
二、租馬 147
三、捐輸馬 147
四、絹馬貿易 148
五、茶馬互市 149
第十章 清代西北官牧馬廠的變遷 154
一、西北馬廠的性質與類型 154
二、寧夏的馬廠 155
三、甘肅的馬廠 156
四、青海的馬廠 159
五、新疆的馬廠 162
第十一章 中晚清對西北馬政的整飭 169
一、清代西北馬政的興盛之因 169
二、清代西北馬政的衰敗之由 172
三、中晚清對西北馬政的失控 179
第十二章 明清西北馬政的特點、地位與作用 183
一、明清西北馬政之時代特點 183
二、明清西北馬政與西北邊防 185
三、明清西北馬政與社會經濟 187
附錄 190
楊一清與西北馬政 190
明代西北馬政機構置廢考 199
試論明代西北馬政的衰敗原因 208
明代西北馬市述略 215
明代西北官牧制度中的“馬價”問題 222
明代茶馬互市中的“勘合制”問題 228
明代西北馬政中的中鹽馬制度 235
明代西北仆苑官牧制度及其演變 240
參考文獻 249
后記 252
明清西北馬政研究 節選
緒論 馬政,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國家的行政制度,即國家對官用馬匹的采辦、牧養、訓練和使用所實施的管理制度。自秦漢以降,迄于明清,它一直是歷代兵制、驛傳和財賦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馬政與它的性質 馬,是人類社會前行的重要拉動力。早先,還有“問國之富,數馬以對”的說法,把它當成衡量國家富強與否的標準之一。 在古代,馬的用途遠比近現代要廣泛和重要得多,它不獨是當時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的主要畜力,同時也是驛傳交通和軍事戰爭的重要工具。即以后者而論,在近代戰爭手段出現之先,即冷兵器時代,戰爭的勝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戰馬的多寡與優劣。正如東漢馬援所說:“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他還深刻揭示了這種“用”的實質,即“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至于宋人文彥博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為重”,明人徐恪謂“兵政莫急于馬”,實際上是先秦以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思想的自然延伸。所以,歷代統治者無不特別重視馬政。 古之馬政,濫觴于周,告罄于清。 “馬政”一詞,語出《周禮》:“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在這里,“閑”即馬廄。《禮記》又云: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東漢鄭玄解釋道:“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 另外,《尚書》中“穆王命伯冏為周太仆正”一語,透露出了這樣一些信息:穆王為周代的第五位天子,生活的時代為公元前十世紀前后;伯冏是史上*早有名有姓的馬政官員,而周代的馬政主官謂之“太仆正”。所以,后來的馬政主官太仆(寺)卿,又有“冏卿”之稱,馬政也有“冏政”之謂。 《周禮》上還說:周有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他們屬于“卿”一類的內服官員,地位僅次于“公”一級的太師和太保。夏官“司馬”,主管軍隊和軍賦,自然也包括軍用馬匹;而其屬下的“馬質”和“校人”,大略是分管區分馬之品相、價值和教養事務的官員;在內服的低級事務性官員中,還有“趣馬”和“仆”這類人員,具體負責周王用馬和駕車出行;而“巫馬”、“牧師”、“庾人”和“圉師”,則分管治療、牧廠和放牧。至于“圉師”之下的“圉人”,則純屬服役的牧馬人,自然也不在官員的行列了。 成書于戰國的《周禮》,所記自然不是周代制度的原貌,可也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書中還有一些涉及馬政的條文,包括養馬、牧地、交配、執駒、醫療以及祭祀之類的制度,對考察馬政的源頭和內含不乏參證價值。 春秋戰國,戰事頻仍,騎兵與戰車成了軍隊的主力,從而也凸顯了馬的作用;“千乘之國”“萬乘之國”,往往也成了國力大小的一個重要標志。各國設官雖不盡相同,可也大略仿效周朝制度。于輔佐諸侯的執政“卿”之下,一般也設立司徒、司馬、司寇和司空之類的政務官員。而作為武官的“司馬”,和先前一樣,還是主管軍隊、軍賦和軍馬;后來,在“郡”、“縣”這些新區,也有負責類似事務的“司馬”。總的說來,這時候的官馬,大體與周代一樣,主要用于王室、戰爭和祭祀。 至秦漢,中原政權的活動范圍比早先更大了。征嶺南,擊匈奴,入河套,開河西,通西域和守長城,也使馬在軍事活動和驛傳交通中具有廣泛的用武之地。所以,秦漢王朝十分重視馬政,使之成為國家正式的軍事經濟制度;馬政職官也有所細化,有關養馬、用馬的管理規定更為具體,成為中國古代馬政**個大發展時期。 在“三公九卿”中,“太仆”是負責全國馬政的主官。《漢書》上說:“太仆,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屬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不過,清人蔡方炳考辨說:“以太仆而專命司馬者,始于漢代,非周官本職也。” 綜合秦漢文獻,官馬牧養可分兩大類:一是宮廷馬廄,包括大廄、中廄、小廄、宮廄、章廄、左廄和右廄;二是地方馬廄,主要集中在塞北和西北,清人錢大昭考論說:“漢制,邊郡牧師苑,官有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另外,關東也設置有馬政官署,出現了像濟南馬丞、代郡馬丞、睢陵馬丞、上虞馬丞、陜縣馬丞、傿陵馬丞、鄚縣馬丞、贛揄馬丞、圜陽馬丞、虢縣馬丞、下密馬丞、原都馬丞、洽平馬丞、汾陰馬丞之類的馬政官員。 魏晉南北朝之馬政,大致沿襲了漢代體制,而實效則遠不及漢代了。隋朝伊始,太仆寺設官與職司略有變化。《隋書》上說:“太仆卿,位視黃門侍郎,統領南馬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丞。又有弘訓太仆,亦置屬官。”又云:“太仆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產之屬,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牝、駝牛、司羊、乘黃、車府等署令、丞。驊騮署,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駝牛署,有典駝、特牛、牸牛三局。司羊署,有特羊、牸羊局。諸局并有都尉,寺又領司訟、典臘、出入等三局丞。”可見,太仆寺實際上是負責全國畜牧的衙門,自然也包括對官用馬匹的放養和管理。另外,又設隴右牧總監,下有二十四個軍馬牧廠。后來,隋煬帝仿西周之制,改驊騮署入尚乘局,下設飛黃、吉良、龍媒、駒賒、駒馱和天苑六閑,每閑又分左右,合計十二閑,即十二處皇家馬廄,以附會“天子十有二閑”之意。 至唐代,雖承隋制,可馬政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歐陽修總結道:“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于近世。”這里所謂的“近世”,實際上正是唐代。具體說來,太仆寺、駕部和尚乘局,是中央馬政機構,分別管理全國的畜牧業、輿輦車乘、驛傳交通以及天子乘御。于地方,則有隸屬于太仆寺上、中、下等牧監;另外,中晚唐的不少藩鎮,還有自設的大小牧監。馬政的興衰,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強弱。至于五代,雖還大多沿襲唐朝的做法,而實際效果畢竟難以望其項背了。 而宋代馬政,又為之一變。早先,由左右飛龍院、天廄坊、左右騏驥院負責馬政;爾后,太仆寺、群牧司和茶馬司成為主要的馬政機構。不過,比之漢唐,因國土萎縮、宜馬區域狹小而馬政情勢走低,南渡以后則更不景氣。在與長于游牧的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族的軍事對抗中,北宋與南宋每每落于下風,原因雖說是多方面的,而馬政情形不理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遼、夏、金、元四代,在馬背上立國,十分重視馬匹的牧養與管理;至于一般民眾,又習慣于逐水草而居。因而,這些馬背民族的王朝馬政,很不同于漢唐宋這樣的中原國家。在它們當中,元代馬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史書上說:“國朝肇基朔方,地大以遠,橐駝馬牛羊莫可以限量而數計。今則牧馬之地,東越躭羅,北逾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云南,凡十有四所 在朝置太仆寺,典御馬及供宗廟、影堂、山陵祭祀,與玉食之挏乳。馬之在民間者,有抽分之制,數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 或遇征伐及邊圉乏馬,則和市拘括,以應倉卒之用。”入主中原后,元朝統治者主要通過“和買”、“拘括”和“牧養”方式采辦官用馬匹。而“和買”“拘括”之類手段,實則是對民眾的一種變相掠奪,從而也激化了民族與社會矛盾。 明代馬政,既兼用了唐宋成制,又有所變通發展,以至于更加完備縝密。用弘治朝大學士丘濬的話來說:“按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后則畜之民,又其后則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于川陜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明史》上這樣解釋道:“明制,馬之屬內廄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于大壩,蓋仿《周禮》十有二閑意。牧于官者,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即唐四十八監意。牧于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 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 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于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于番,以貨市于邊 此其大凡也。”大略說來,按其牧養形式,一般可分為官牧、民牧和京府寄牧;對官牧、民牧和寄牧馬,自有不同的管理辦法,早先的效果應該說也不錯。不過,《明史》上又說:“蓋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明代馬政,既有官府經營的監苑官牧,又有南北兩畿、魯豫編戶養馬的民牧。而后者比之北宋保馬法,讓民戶深感負擔更為沉重,丘濬即云:“編戶養馬之害,甚于熙寧保馬之法。”入清,即對這種不得人心的做法進行了調整。先是,順治元年(1644),改為額征馬價錢糧;而后,康熙二年(1663),又將馬價錢糧編入條銀征收。這樣一來,直隸、江南、河南和山東四省的漢人,只需繳納賦稅即可,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民養官馬之苦。 對周秦至明代馬政,蔡方炳總結道:“歷考古今馬政之變,其官民通牧者,周也;其于民而用于官者,漢也;牧于官而給于民者,唐也;其始則牧之在官,后則畜之于民,而又市之于邊境者,宋也;其內地散之于民,在邊地則牧之于軍,而專易之于西番者,明也。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歷數而見焉。”蔡氏之說,未必真切,不過也大略可取,足備有關研究者體悟參考。 清代馬政之于明代,也是既有承襲又有變通。從所及內容來看,主要包括上駟院職司及牧廠、太仆寺職司及牧廠、八旗馬政與綠營馬政、除官牧外官馬之來源途徑四個方面。 上駟院的前身,是御馬監,具體的職司,一是管理、供養宮內馬匹;二是負責騎試、挑選御馬,以供帝后、嬪妃和皇子之用;三是主管治療皇家馬駝疾病;四是經營大凌河和察哈爾的商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岡愛牧廠。太仆寺與上駟院一樣,同屬中央馬政機構,專司左右兩翼牧廠事務。八旗、綠營馬政,是對軍隊戰馬的管理。而清代官用馬匹的來源,除官牧外,主要是貢馬、租馬、捐輸馬、絹馬貿易和茶馬互市。貢馬者,大略是蒙古王公、臺吉、四川土司、甘肅唐古特七族以及青海和涼州番族的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租馬者,主要是針對新疆的少數民族;捐輸馬者,則主要來自蒙古各旗王公、臺吉;絹馬貿易者,則主要來源于準噶爾部和哈薩克人;至于茶馬互市,它先是沿襲了明代的做法,又漸次于雍正、乾隆朝終結。至中晚清,在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打擊下,對馬政經營的興趣銳減以至于它幾乎一蹶不振。 二、西北馬政的源與流 西北廣袤無垠,宜牧區域遼闊。所以,由馬政產生伊始,直至晚清、民國,西北馬政在中國馬政史上一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周、秦京師偏西,又重王室和軍隊馬政。不難理解,關中和隴右是其馬政的重心所在。即以秦而論,它的崛起也與養馬有關。司馬遷追述說:秦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羌渭之間,馬大蕃息 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仍為朕息馬,朕封其土為附庸。’”犬丘,即今陜西興平。鄭玄《毛詩 秦譜》云:“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汧即汧水,是渭水的一大支流。非子因養馬而受封侯,也成了秦人立國的開端。秦霸西戎后,兵馬日多,國勢日盛。至戰國,張儀游說韓王稱:“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后,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與后之秦始皇兵馬俑坑,俱已表明立足于關中、隴右的秦人馬政之恢宏氣象。 西漢承秦,也立足于關中、隴右。擊匈奴,開河西和通西域,刺激了統治者關注馬政的熱情。而牧師苑之設,則表明西北已成為馬政的重心所在。東漢應劭說:“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養馬三十萬頭。”司馬彪又云:“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而河西六郡,按錢大昭的說法,即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隴西郡,治狄道(今甘肅臨洮);天水
- >
朝聞道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姑媽的寶刀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推拿
- >
史學評論
- >
二體千字文
- >
山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