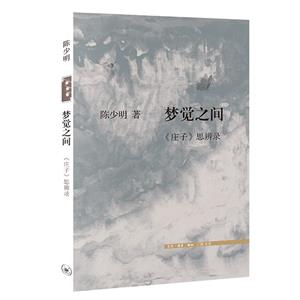-
>
道德經說什么
-
>
電商勇氣三部曲:被討厭的勇氣+幸福的勇氣+不完美的勇氣2
-
>
新時期宗教工作與管理
-
>
帛書道德經
-
>
傳習錄
-
>
齊奧朗作品·苦論
-
>
無障礙閱讀典藏版:莊子全書
夢覺之間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1057
- 條形碼:9787108071057 ; 978-7-108-07105-7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夢覺之間 本書特色
陳少明是當代重要的中國哲學研究者,其關于《莊子》的研究是看家本領,也頗具價值與影響力。作者一直以來主張“做”中國哲學(曾在三聯出版《做中國哲學》一書),強調實踐,尤其是經典思想資源與當代哲學的碰撞。而莊學正是其*早做哲學練習的園地。在這一意義上,本書是對方法論如何實踐的具體呈現,向讀者展示了作者如何將莊子與現代哲學論說的關系更清楚地揭示出來。也是在此意義上,此書不僅是對經典文本的解讀與研究,更是作者本人及其所代表的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在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交匯處如何煥發經典資源之生命力的思想歷程的呈現。
夢覺之間 內容簡介
近代西方以降,以理解、宰制外物為目標的科學技術逐漸成為哲學模仿的對象,通過制作成套的理論系統對“物”進行*大限度地追逐。相比之下,前科學時代的莊學不是簡單的形而上學追問,其目標既非沒有方所的物,也非先天定在的理。莊子以其創造的獨特道論,致力于揭開俗世積習的面紗,刷新我們對生命的認識。
作者通過勾連中國傳統思想中視覺與思想的內在關系,強調以“思想視角”考察《莊子》,著重刻畫了莊子的講述方式,從而論述這一中國哲學的偉大人物其反常規的視角所呈現的生命場景,與其致力于為人生揭蔽的思想立場,兩者密切相關并因此呈現出莊子之道的哲學意義。
夢覺之間 目錄
自 序 生命的精神場景
**編 文 本
一 從《齊物論》看《莊子》
二 人、物之間:理解《莊子》哲學的一個關鍵
第二編 思 維
三 通往想象的世界
四 歷史的寓言化:對《莊子》歷史論述的一種解讀
第三編 哲 學
五 “吾喪我”:一種古典的自我觀念
六 莊子觀夢:物我與生死
七 廣“小大之辯”
八 “庖丁解牛”申論
九 由“魚之樂”說及“知”之問題
第四編 歷 史
十 從莊子看心學
十一 白沙心學與道家自然主義
十二 啟蒙視野中的莊子
夢覺之間 節選
晉人嵇康說《莊子》:“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世說新語·文學》)一語道出許多好莊者的心聲。訓詁、注疏或校勘,只是專家的事情。而《莊子》一書,并非為專家所作。愛讀書的人,即使不曉得“道”是“有”還是“無”,不知“道”從哪來和到哪去,也不妨礙其讀《莊》獲得的樂趣。莊書讓讀者快慰或沉迷的原因,在于其講故事的魅力及其所呈現的生命的精神場景。
問題的奧秘,要從其獨特的講述方式說起。 《莊子》把自己的講述方式稱作“三言”,寓言、重言與卮言。一般認為,表達的主要方式是寓言,而所述的觀念為卮言。什么是寓言?《寓言》篇的說法是:“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意思是表達者的意圖不能直陳,要借助某種中介來傳達,以加強其說服力。這是比喻,也類一則微型寓言。綜覽全書,這種方式就是通過陳述故事來傳達對生命或生活的觀點。故事不必復雜,無須史詩式的長篇,只要精致的情節或場景。所涉者無非生活中的要素,人、事、物之類。其要義就是通過情景來呈現觀點,而非通過概念去推論,即故事能讓讀者或聽眾直接感受其意義。用《秋水》篇的話說,意義是“觀”出來的。但它不是普通方式的“觀”,“以物觀物”所得者,只是庸常的觀念;要做到“以道觀物”,那才是道行之所在。因此,“觀”是需要訓練或者修養出來的能力。
漢語中,望、視、見、觀等詞與“看”有共同的意義,都指通過運用眼睛的視覺功能去掌握對象的行為。整個行為的完成,包括若干要素,如意愿、對象、位置、行動以及結果。這樣看來,同是表達視覺行為的詞,意義的側重點可能就不太一樣。例如,“望”字表達意愿與行動,但不一定望得出什么結果。故《莊子》說“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天運》)。荀子也言“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勸學》)。“視”亦然,一般是近視遠望。《秋水》中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的河伯,“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同樣也“視而不見”。“看”字起源較早,但其流行則時間上偏后。它也存在著“看見”與“看不見”的問題。如果什么都看不見,看了也白看。因此,“見”除了表達直接察看的意思,更重要的,還意味著看到一定的結果。前義如《論語》中的“子見南子”(《雍也》),“子路慍見曰”(《衛靈公》),以及《莊子》中的“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天運》)。后義如“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天道》),“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運》)等,往往表示“看”出了結果,有所收獲,所以叫有所“見”。因此,“見”之古義也同“現”。但是,所見是否如所愿,則是另一個問題。因此,也存在淺見、偏見和洞見、遠見之分,或者如佛學說的有正見、倒見之別。東施效顰就是見非所是或者同看不同見的例證:“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天運》)
“觀”則包含“看”(或視、望)與“見”兩義而有所超越。先看“觀”“看”之異。偶然的撞見或無心的一瞥,都是看。而且看是在特定的視角范圍才有效。河伯出崖涘時“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北海若告訴他:“觀于大海,乃知爾丑,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秋水》)觀水較有普遍性,儒家也主張“君子見大水必觀”(《荀子·宥坐》)。比較而言,“觀”是更自覺的行為,同時視野更深遠,甚至越出視覺的限制,不但“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易·系辭下》),還可以“觀古今之異”,對象從空間擴展到時間。再看“觀”與“見”。字形構造上,觀字包含見字在內。“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逍遙游》)與“望之而不能見”義同,觀與見都有看到結果的意思。但是,當其行為對象相同時,見、觀意義便有別。“見人”指直接的會面,如“子見南子”或“孔子見老聃”。但“觀人”則不是見人,如“今吾觀子非圣人也”(《天道》),或“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天下》),其重點不是看一眼或會一面,而在于對人格及思想的考察、品鑒。觀的過程包含有觀念思考的成分。《齊物論》有:“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同樣是所“見”具體,所“觀”抽象。重要的是,當下的視覺都是有限制的,有限的言行不能評價一個人,壯麗的風景無法一眼望盡。因此,“觀”不是視覺形象的一次性捕捉,而是一個過程。它需要不同視覺片斷的連接。這些片斷可以來自同一視角下對象的變化,也可以圍繞著對象進行不同角度的觀察。過程一旦拉長,這種“觀”就需要知識的輔助或補充。或者說,“觀”把眼前的經驗與過去經驗相聯結的思想活動,是觀察向思考的過渡。因此,同是看海,觀海與見海就不一樣。見海是指獲得關于海洋的視覺形象,觀海(或觀水)則獲得比視覺更多的內容,如胸懷、氣度、境界等等。《秋水》中,北海若說河伯“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崖涘,觀于大海,乃知爾丑,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這也意味著“觀”不是裸視,而是有準備的思想行為。所以,不但可以觀天文地理,也可以觀風土人情。同時,這種“觀”還需要突破視覺表象,透過事物的外部形態去抓取其內在結構。如《易傳》的“觀物取象”,就不僅限于直觀的行為,還有“取”的思想主動性。
老子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道德經》**章)《莊子》借北海若之口接著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以功觀之,……以趣觀之,……”(《秋水》)所謂“以X觀之”,不論是以“道”,還是以物,以俗,以差,以功,以趣,同老子的“無欲”“有欲”一樣,表明這個“觀”是需要立場或“先見”的。北海若所說的“以道觀之”之“道”,就是莊子觀天下人生的知識或思想依托。毫無疑問,莊子的“觀”超越“見”,意義更寬廣。日后,“觀”便慢慢延伸出更抽象的含義,而且更突出觀看的成果,如觀點或觀念。不但觀心,而且可以觀道。*終,道觀、觀道一體。今日所謂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之類,均由此延伸而來。
人是視覺的動物。這不是說只有人類才有視覺,而是指人類能把視覺的功能發揮到極致,把它從看得到或可以看的事物上運用到“看不到”或“不能看”的目標中。看不到者如宏觀、微觀對象,不能看者如思想現象。所謂“宏觀世界”“微觀世界”,或者“思想世界”“精神世界”,就是人類用思考模擬觀看的表現。這不只是視覺需要思想,而且是視覺如何進入及支配思想的問題。章太炎甚至主張,中國傳統的道學,與其叫作哲學,不如稱為“見”學:“九流皆言道。道者彼也,能道者此也。白蘿門書謂之陀爾奢那,此則言見,自宋始言道學(理學、心學皆分別之名)。今又通言哲學矣。”他引荀子《天論》的說法,“慎子有見于后,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詘[屈],無見于信[伸];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強調“予之名曰見者,是蔥嶺以南之典言也”。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把荀子同佛學聯系起來,斷言思想與視覺一樣,其有效性可通過驗證來判斷。“見無符驗,知一而不通類,謂之蔽(釋氏所謂倒見見取)。誠有所見,無所凝滯,謂之智(釋氏所謂正見見諦)。”觀察結果與對象不一致,或者看到事物特殊性而不知其普遍性,都是蔽的表現。見而無蔽稱為智。然而,視覺上還存在“見”與“蔽”的另一種對立。對物體的任何一次觀察,都只能見到其中的一個側面,而看不見其位置相反的一面,故有所見便有所蔽。思想也是這樣,囿于自己的立場,便會產生“有見于后,無見于先”或“有見于少,無見于多”這種局限。思想家的局限,也是觀念史的問題。例如“道”,本意是走路,慢慢變成路,又變成到達目的地的途徑,再變成達致抽象理想的措施,*后變成規則甚至形而上的本體。而每一新義的出現,都是對舊義的掩蓋。有所見必有所蔽,遮蔽既久,根源就容易被忘記。正如考古場地一樣,越原始的層次埋得越深。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到《易傳》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再到王弼“以無為本”的道,道越來越離開其根基,同時也越來越玄虛。因此,那些有根源性追求的思想家就會出來揭蔽,或者叫作思想考古,從唐代開始便先后有韓愈、章學誠、章太炎等接二連三的《原道》。章太炎以為,智者的使命便是通過思想的解蔽,獲得對道的洞見。太炎為何獨尊“見”而不稱“觀”,我們不知道。但兩者的思想邏輯是相容的,觀道或見道,就是哲學的一個概念模型。
夢覺之間 作者簡介
陳少明,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系學術委員會主任,長江學者。出版有《〈齊物論〉及其影響》(2004)、《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2008)、《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2015)等著作多種。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月亮與六便士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經典常談
- >
月亮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