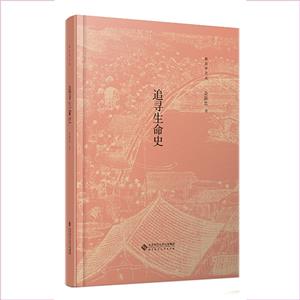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zhàn)為何爆發(fā)及戰(zhàn)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追尋生命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3263158
- 條形碼:9787303263158 ; 978-7-303-26315-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追尋生命史 本書特色
本書探究的是歷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僅要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物質、制度和環(huán)境等外在性的事務,同時更要關注個人與群體的生命認知、體驗與表達。歷史是由生命書寫的,生命是豐富多彩而能動的,而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
追尋生命史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關于醫(yī)療史與疾病史的系統(tǒng)思考,作者認為,“生命史學”的核心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識,讓其回到人間,聚焦健康。也就是說,我們探究的是歷目前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僅要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物質、制度和環(huán)境等外在性事務,同時更要關注個人與群體的生命認知、體驗與表達。意味著我們探究歷史時關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識是理所當然的。鮮活而能動的生命不僅讓歷史充滿了偶然性和多樣性,也讓書寫豐富、復雜而生動的歷史成為可能并且變得必要。作為中國社會史、醫(yī)療史研究領軍人物,作者的思考對于系統(tǒng)反思我們的史學方法具有啟發(fā)意義。
追尋生命史 目錄
自序
疫病社會史研究:現(xiàn)實與史學發(fā)展的共同要求
從社會到生命:中國疾病、醫(yī)療社會史探索的過去、現(xiàn)實與可能,
衛(wèi)生史與環(huán)境史:以中國近世歷史為中心的思考
回到人間 聚焦健康:新世紀中國醫(yī)療史研究芻議
醫(yī)療史研究中的生態(tài)視角芻議
微觀史與中國醫(yī)療史
當今中國醫(yī)療史研究的問題與前景
生命史學:醫(yī)療史研究的趨向
在對具象生命的關注中彰顯歷史的意義
淺議生態(tài)史研究中的文化維度:基于疾病與健康議題的思考
環(huán)境史研究中的環(huán)境維度和歷史維度
文化史視野下的中國災荒史研究芻議
新文化史視野下的史料探論
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
個人·地方·總體史:以晚清法云和尚為個案的思考
“良醫(yī)良相”說源流考論:兼論宋至清醫(yī)生的社會地位
揚州“名醫(yī)”李炳的醫(yī)療生涯及其歷史記憶:兼論清代醫(yī)生醫(yī)名的獲取與流傳
醫(yī)圣的層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與現(xiàn)代中醫(yī)知識建構系列研究之一
追尋生命史 節(jié)選
疫病社會史研究:現(xiàn)實與史學發(fā)展的共同要求 說起中國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當歷史修養(yǎng)的知識人,也會感到茫然。在傳統(tǒng)的史學視野中,瘟疫這樣似乎無關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規(guī)律的內容,不過為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jié),至多也只是歷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故而長期以來,閱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并不能讓人明白“瘟疫”為何物。如今,生活在科技飛速發(fā)展時代、享受著現(xiàn)代醫(yī)學種種嘉惠的人們,與那種危害重大的瘟疫的記憶自然更是漸行漸遠。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2年年底以來,一種全新的疫病SARS突然降臨于神州大地,并幾乎迅速傳遍全國并遠流海外。面對這一不期而至的現(xiàn)代瘟疫,社會一時流言四起、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令人不得不感喟,原來,那種能夠危及全民的瘟疫并非只存在于塵封的歷史中,而是隨時都有可能進入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現(xiàn)在,這場令人心悸的災難至少暫時已經(jīng)過去,隨著人們日常生活漸漸恢復正常,那些曾經(jīng)由SARS帶來的生活限制、緊張、焦慮以及混亂也自然會慢慢地淡出蕓蕓眾生的記憶。但無論如何,在思想文化界,知識人顯然不可能輕易地讓這場銘心的災難如此迅速地消散于無形的空氣中,從而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失去一次“亡羊補牢”的機會。毫無疑問,非典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醫(yī)療衛(wèi)生問題,由這場現(xiàn)代瘟疫所引發(fā)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問題,無論哪一方面都值得我們整個社會很好地省思。“亡羊補牢,未為晚矣”乃是中華民族早已爛熟于心的道理,事實上,所謂“后SARS時代”的種種反思目前已在學界廣泛地開展起來。這些反思是多層面的,既有對現(xiàn)實社會機制的批判和建構,也有對當今社會發(fā)展總體理念以及中國文化建設的重新思考,還有有關當下學術發(fā)展理路的反省,等等。這些從不同視角出發(fā)的反思無疑都自有其價值,不過,無論如何,這些省思不可能僅僅立足于SARS本身而展開,而必然需要了解甚至深入認識人類以往的相關經(jīng)驗,否則,反思也就不可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厚度。由此可見,對人類瘟疫歷史的回顧與認知具有毋庸置疑的現(xiàn)實意義,實際上,面對非典,我們的政府、社會和民眾所表現(xiàn)出的驚慌無措、應對失宜,也與今人對瘟疫史的失憶不無關系。顯而易見,瘟疫絕不僅僅是自然生理現(xiàn)象,而是關涉醫(yī)療乃至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社會文化問題,故而,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實際上,確切地講,其欲探討的也就不應稱之為瘟疫史,而應是疫病社會史或疫病醫(yī)療社會史。即該研究并不只是關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從疫病以及醫(yī)療問題入手,呈現(xiàn)歷史上人類的生存境況與社會變遷的軌跡。當然,開展這一研究,并非只是出于其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或許更為重要的還是源于其獨特的學術價值。人之一生,與自身*密切相關的莫過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這些似乎無關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之類宏旨的細微小事,其實正是人類歷史*真實、*具體的內容。現(xiàn)代國際學術發(fā)展趨向,已經(jīng)逐漸擺脫對結構、規(guī)律和因果關系等的過度追求,而表現(xiàn)出對人本身的關注以及對呈現(xiàn)人類經(jīng)驗的重視。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史學工作者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于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以及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等問題的探討之中,而對歷史上人的生存狀況、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信仰等與人本身直接相關的問題則往往視而不見,瘟疫這一雖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但顯然并不直接關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且本身又不具規(guī)律性的內容,自然就更不在歷史學家的視野之中了。在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雖然隨著社會史研究的興起,衣食住行已越來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注目,但直接關乎生老病死的疾病醫(yī)療,基本還是歷史學的“漏網(wǎng)之魚”。然而實際上,只要稍作考量,便不難發(fā)現(xiàn),疫病與醫(yī)療無論對歷史還是當今社會都有著極其重要而深刻的影響,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曾在《瘟疫與人》中指出:“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xiàn)的年代早于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shù)以及決定因子。”“流行病傳染模式的變遷,過去和現(xiàn)在一直都是人類生態(tài)上的基本地標,值得更多地關注。”[1]由于疫病始終與人類相伴隨,給人類帶來了難以盡述的痛苦和恐懼,因此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應對疾病的醫(yī)療觀念和實踐也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和形塑著人類的行為和思想,進而廣泛而具體地對歷史進程產(chǎn)生影響。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呈現(xiàn)和透視歷史上的疾病醫(yī)療,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人類的生存狀況以及社會歷史的變遷。由此可見,疫病社會史研究乃是一個十分重要并具有廣闊前景的研究領域。從筆者自身的研究體會來說,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對了解歷史上人們的生存狀況、精神面貌、環(huán)境與社會的變動、民眾的心態(tài)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將可以使我們看到一幅“真實存在”卻長期以來未被發(fā)掘的重要歷史面相。歷史學對包括瘟疫在內的疾病醫(yī)療的忽視,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乃是一個世界性普遍問題。不過,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一傾向在西方史學界就已出現(xiàn)改觀,至今,探討歷史上的疾病醫(yī)療以及借此透視社會和文化的醫(yī)療社會史和身體史研究乃是當前史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并業(yè)已成為主流史學的一部分。這一潮流自然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海外乃至國內的中國史研究,1975年美國的鄧海倫(Helen Dunstan)發(fā)表了國際中國史學界*早的具有自覺意識的疫病社會史論文——《明末時疫初探》[2]。隨后,大約分別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和大陸史學界也逐漸興起了疫病醫(yī)療社會史研究。當然,海峽兩岸這一研究的興起,并非僅是世界史學潮流影響而致,可能更為重要的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內部對以往研究的不滿與積極反省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和臺灣史學界不約而同地開始對史學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條公式主義的困境”或“社會科學方法的貧乏”展開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對以往研究過于側重政治、經(jīng)濟、階級斗爭及外交和軍事等做法表示出了強烈不滿,提出了“還歷史以血肉”或“由‘骨骼’進而增益‘血肉’”這樣帶有普遍性的訴求。[3]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社會群體、社會生活、社會人口、社會救濟、社會環(huán)境等一些過去不被注意的課題開始紛紛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大大拓展了歷史研究的界域。在臺灣,在梁其姿、杜正勝等人的努力實踐和積極倡導下,其研究目前已漸成風氣,成為臺灣史學的熱點之一。而大陸雖然起步較晚,而且當下的研究與臺灣相比,仍處于散兵游勇狀態(tài),既乏人倡導,也未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自然就更談不上有什么指引和規(guī)劃,但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甚至涉足這一研究領域,同時,還不斷有年輕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開始介入其中,顯現(xiàn)出這一研究未來良好的發(fā)展勢頭。[4]由此,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剛剛起步但具有方向性和廣闊前景的研究領域。人類瘟疫歷史長期被歷史學界所忽視,應該不是偶然的,個中的緣由,除了史料中有關瘟疫的記載相對較少、瘟疫本身不具有規(guī)律性等自身因素以外,特別對中國史學界來說,恐怕更主要還與我們的學術理念乃至思想文化取向有關。那就是,在我們學術理念中,缺乏一種對生命的真正的關懷。為了生存和發(fā)展以及鑒往知來,往往熱衷于社會的進步、經(jīng)濟的發(fā)展或者歷史規(guī)律的探尋,而唯獨忽視了歷史的主體——人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雖然生命的可貴對每個人來說可能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我們整體的社會理念中,個體的生命在很多情況下其實不過是實現(xiàn)某種整體社會目標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和工具,而較少能真正體認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生命的存在乃是人類社會的*高倫理。其實,對生命的缺乏關懷又豈止存在于學術理念之中,在我們的社會意識、統(tǒng)治思想中又何嘗不是如此?穩(wěn)定和發(fā)展對人的生存自然是重要的,但如果這一切不能建立在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珍視的基礎上,不僅穩(wěn)定和發(fā)展恐怕很難長久地保持,而且更為根本的,若穩(wěn)定和發(fā)展不是為了個體生命的福祉,那意義又在哪里呢?認識到了這一點,其實就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學術上以及現(xiàn)實中的很多積習其實都與我們缺乏對生命的真正關懷和珍視有關。比如,學術上,過于追求宏大敘述而輕忽歷史細節(jié),熱衷于規(guī)律的探尋而忽視人的生存境況等;現(xiàn)實中,片面強調“發(fā)展才是硬道理”,不加思考地將“革命”“改革”視為社會*高目標,施政辦事不立足民生的改善而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匿災不報等。如果從這一角度而言,瘟疫史的研究,通過對歷史上與人類生存環(huán)境和境況息息相關的瘟疫的鉤沉,將有利于我們真正了解歷史上的生命,從而培養(yǎng)我們關注生命、珍視生命的意識。而一旦這樣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也就增加了破除以往學術上、社會上乃至政治上的種種積習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在我們當前的境遇下,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將有可能同時具備學術和現(xiàn)實的雙重意義。由此可見,從社會史的視角探討歷史上的瘟疫與醫(yī)療的疫病醫(yī)療社會史研究,在當前的情形下,無論從現(xiàn)實還是學理來說,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義的。本文原刊于《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追尋生命史 作者簡介
余新忠,浙江臨安人,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后。現(xiàn)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兼院長,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職。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等著作5部,在《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百余篇。入選教育部領軍人才計劃青年學者和特聘教授等人才項目。榮獲全國優(yōu)博論文獎,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一、二等獎等獎勵。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月亮與六便士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推拿
- >
名家?guī)阕x魯迅:故事新編
- >
經(jīng)典常談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