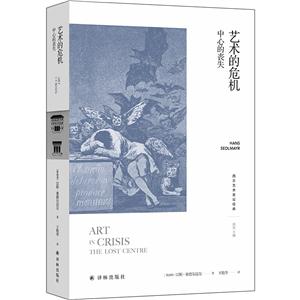-
>
東洋鏡:京華舊影
-
>
東洋鏡:嵩山少林寺舊影
-
>
東洋鏡:晚清雜觀
-
>
關中木雕
-
>
國博日歷2024年禮盒版
-
>
中國書法一本通
-
>
中國美術8000年
西方藝術史論經典藝術的危機:中心的喪失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82999
- 條形碼:9787544782999 ; 978-7-5447-8299-9
- 裝幀:80g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方藝術史論經典藝術的危機:中心的喪失 本書特色
? 奧地利著名藝術史學家賽德爾邁爾集大成之作。 ? 以藝術作品的風格變化為基礎,探討社會更迭的現象與含義。 ? 這是一部探討藝術作品的文藝之作,更是一部關于精神的批評之作。
西方藝術史論經典藝術的危機:中心的喪失 內容簡介
賽德爾邁爾將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藝術品作為理解社會轉變的基礎,將每個時期出現的新的藝術現象視為時代的“癥候”,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診斷整合成“中心的喪失”這一概念。現代藝術的審美脫節不僅意味著風格問題,而且指向了更深層的文化和宗教瓦解過程。因此,這是一部關于精神的批評之作,作者從藝術出發,既考量時代的豐功偉業,又不回避它的苦難深重。本書的問世引起了藝術評論家和神學思想家的共同關注。
西方藝術史論經典藝術的危機:中心的喪失 目錄
導 言
**部分 征兆
**章 新的主要形式問題
第二章 尋找一種消失的風格
第三章 藝術的分立
第四章 對建筑的攻擊
第五章 分裂的意義
第六章 混沌出世
第二部分 病程以及診斷
第七章 “癥候的類型”
第八章 “自治的”人
第九章 現代的開端
第十章 現代藝術的先驅
第十一章 十八世紀的三次藝術革命
第十二章 從藝術的解放到藝術的否定
第三部分 預測和*后的審判
第十三章 世紀的審判
第十四章 現代藝術評判標準
第十五章 現代藝術:西方藝術的第四階段
第十六章 當代社會:人類歷史的轉折點
第十七章 預測未來
后 記
理解藝術的四種途徑
人名索引
西方藝術史論經典藝術的危機:中心的喪失 節選
**章 新的主要形式問題 我們當前的任務一點不少于生活本身,因為一切都圍繞著讓具體的形式開口表達。 ——H.施拉德 自十八世紀末以來,我們的主要任務開始涵蓋了一些全新的內容。它們可能是一些之前從未出現過的新問題,或者,它們可能出現過卻一直處于不重要的附屬地位。 過去人們主要關注的是教堂和宮殿,但是,現今這些事物被擱置一側,一系列新的亟待解決的形式問題接踵而來,開始取代教堂和宮殿的地位。自1760年至今,我們能清楚地辨別出六七種不同的主要形式問題,每一個問題在它的時代都在整個歐洲范圍內大聲疾呼,渴望得到解決方案。在此,我們所指的是風景花園、建筑紀念碑、博物館、劇院、展覽(館)以及工廠。這些形式問題中沒有哪一個能夠在一代或至多兩代人中占據主要地位。然而,它們之中的每一個都是一個時代征兆,我們能夠根據它們彼此交替的序列去認識某種特殊的發展趨勢。 事實上,這些新的主要形式呈現了一條藝術發展主線,這比其他任何藝術發展脈絡都更加典型、更加清晰。不過,當受到一些外來的或者跨學科的流行風尚或潮流影響時,這條發展脈絡在一定程度上會變得模糊而令人捉摸不定,然而究其根本,它們彼此在內在本質上是毫不相關的。所以,如果我們從這些新的主要形式入手去理解藝術的發展過程,我們就會獲得*好、*實用的導覽線索,去破解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藝術謎徑。 接下來,在入文前還有一點說明。雖然剛才我們一直提到某些主要的形式問題,但是,在此我們真正重點關注的是一些關鍵性的建筑形式。我們認為,只有通過對建筑形式的探討才能將這些問題揭示出來。所以,只有建筑師以及偉大的園林設計師的思想,才與我們的研究密切相關—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必須得首先澄明:以上所提出的問題,只在較小的程度上適用于繪畫領域的不朽杰作,盡管偉大的畫作在自己的領域里獨領風騷,創造出非凡的價值和意義,但是與我的論題不十分相關。繪畫領域自身地位十分獨特,它與這些主要的形式問題所生成的土壤有一定距離,甚至相距較遠。事實上,我所提到的這些形式問題,不是圖畫問題。繪畫實踐是自由的藝術形式創造,任何形式的“終結”對它都無甚影響,它不是那種服從于某種明確界定的、展現于公眾視野的藝術實踐。 然而,根據這種關聯性我們可以肯定,新的主要形式問題與綜合藝術作品(比如宮殿或教堂)是不直接相關的,后者為造型藝術提供了獨特的創作場域和創作題材;新的主要形式或者與純建筑形式相關,比如建筑紀念碑,或者與那種僅僅以建筑結構作為基礎的建筑物相關,比如房屋或者博物館等,在這些建筑形式之中,人們可以根據不同的趣味要求選擇構建不同的自由藝術形式。只有在十九世紀中期所幸出現了劇院這一形式之時,才興起了綜合藝術作品的復興,這時(唯有在這段歷史時期),在處理與以上所提及的所有新的建筑形式相關的創作任務時,非凡的畫家與雕刻家才在嚴格設定的創作原則和規定之下去完成他們的使命。 那么,我們在何種意義上來討論這些主要的形式問題呢?在多樣性的研究對象之中,我們選取了如上一些主要形式,這并非是武斷、任意的,因為它們已經開始引起極具有獨創精神的藝術家們的注意。而且,除了此處所遴選的這些形式問題之外,證券交易所也正在被建造,以及國會大廈、大學、酒店、醫院、火車站等,也陸續出現。 所以,首先,我們是根據如下理由來確定“主要的形式問題”這一術語與具體作品的聯系的: 1. 因為這些作品都具有一個共性,即能夠激發創造性想象力; 2. 因為當考察這些形式問題時,我們可以運用一套共同的研究方法,因此這些問題可以遵循統一原則進行類型的劃分; 3. 因為即使程度不一甚至在極小的程度上,在風格總體發展方面,這些主要的形式問題都能夠施以創造性貢獻,所以,它們可以為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參照的范本或可資借鑒的案例; 4. 因為不管是出自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目的,這些主要的形式問題都可以取代古代神圣、莊嚴的建筑形式。 此外,對于許多可以用“主要的形式問題”這一術語來表述的作品而言,它們對藝術的公共性價值和影響力的表征,它們所體現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所特有的、不可估量的個體主義傾向,將可能喪失。因為,盡管它們不具備偉大的、過去時代的綜合藝術作品的影響力,它們實際上確實是那些綜合藝術作品的合法繼承者。 對于歐洲文明的早期階段而言,主要形式問題是教堂建筑。那時綜合藝術作品是*為杰出的藝術形式,它們凝聚并表征了所有藝術創作的上乘手法。在那個時代沒有哪一種藝術形式可以與之匹敵,綜合藝術作品地位首屈一指,所有其他的藝術形式都要在風格和母題方面以之為借鑒。 自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開始,新的主要形式問題開始出現。出現在偏遠或封閉、孤立地區的一些新的形式問題,比如市政廳等,它們在短期內取得了與教堂建筑地位平等的卓越成就,此后便接著開始推進自己獨特的、新的圖像世界的發展。它們在后來發展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問題,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對同一形式的兩種發展,是對同一問題作出的兩種不同表達,這兩種形式問題是城堡和宮殿。這些新的形式在十四世紀被創造出來,待及發展到十五世紀,它們已經獲得與教堂建筑同等重要的地位。事實上,有時它們的影響力更大更為廣泛。它們也成為神圣、莊嚴的建筑形式,成為偶像崇拜的核心表征性建筑,而且,它們還推進了自己的圖像世界的發展,即它們自己的圖像志。這時,與以教堂為代表的綜合藝術形式相比照而言,在世俗的圖像領域出現了與其比肩的建筑形式,而這兩種新形式似乎更能表征偉大的文明地位和自我肯定。 古代綜合藝術的沒落 在十九世紀的發展中,古老的主要形式問題開始逐漸喪失它們的主導性。不僅城堡修建得越來越少,宮殿和教堂也逐漸無人問津。雖然許多古老建筑仍然矗立在各地,可是它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古老的文化自信和自我肯定已然褪色,可是,新的建筑體系還缺少獨創性精神,新的獨創性形式尚寥寥無幾。 在新的教堂結構中,輪廓分明的建筑將難再出現了。人們開始探索一種新的空殼架構形式,然而舉棋不定,因為傳統的教堂結構仍然試圖去全權掌控這種新形式,可是這只能是一種徒勞;新的教堂形式開始探索早期基督教建筑、拜占庭建筑、羅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及文藝復興建筑。有時,它甚至委身于希臘神廟的外觀形式之上去尋求庇護和存在感。然而,這種形式體系整體上來講是多么地流于膚淺和表面化,申克爾所設計的韋爾德大教堂地處柏林,它就是典型一例,它不遺余力地、清晰地呈現了這一特征。作為地基的立方體結構仍然保持原狀沒有改變,然而它也被喬裝改造了一番,它戴上了面具以迎合新的、改變了的觀者的奇想需求,有時它披覆上羅馬式建筑的外衣,有時它隱藏在哥特式風格的表象之下,有時又偽裝成為古風形式的象征之物。這種不甚高明的基底與附屬部分之間的分離,以及將后者簡單看作裝飾部分的做法,昭示了歐洲藝術整體的未來命運,然而,作為教會建筑的特點再也無法辨別出來—當然這其中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 事實上,整個關于教堂建筑的觀念成為關于厚重的團塊和赤裸的無裝飾之物的總的觀念,這不僅發生在新教國家,這種轉變自身就說明了其中的原因。宗教元素不再顯得神圣而神秘,它是詩意的,卻不再是有機的整體而是成為一種外衣,一塊意識形態帷帳,從過去和歷史借鑒而來。只有在1760年至今的整個發展階段,教會建筑形式才仿佛再一次迎來了復興,成為時代的主要形式問題。那開始于神圣同盟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申克爾決定以哥特式風格來為德國設計一座國立教堂。1815年,一部篇幅較小的著作《新教堂》面世了,此后不久人們就開始構建科隆大教堂,并在同一時期竣工。在這一教堂的建設中,人們投注了極大的熱情。可是,同樣的,這一構建方案及其思想再一次披露了一種空洞性,甚至在那個紀元的后半期,當新興的“新哥特式”教堂開始更加忠實并強調它們的歷史傳統范本時,新的教堂建筑的許多細部也同樣反映了來自另一世界的、無實體的某些幽靈的征兆和特質。所以,“新哥特式”建筑只是教會建筑形式維系自身存在一致性、追求*長久持續生命力的一種表征,然而作為獨立的藝術形式,它自身卻轉向崇尚另外一種更為廣泛、多樣的精神態度。直到我們當今的時代,教堂仍然繼續依據“新哥特式”風格在陸續地被建造。 然而,與學院派哲學的復蘇不同,哥特式教堂的復興并未取得成功,因為它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內涵。事實是,在當時的文化語境看來,在復興哥特式教堂建筑風格的同時,繪畫領域中并未發展出對應的形式,這一事實表明了這一建筑形式在當時尚未取得成功。這時,建筑成就不再與當時的宗教藝術領域中所開展的嘔心瀝血的刻苦創作發生聯系。十九世紀的教堂就其作為“圖像志”的本質而言,已經走上了末路。當時的繪畫領域大量產出神學題材的作品,卻完全喪失了人類的想象力,它們的題材變得主觀化,失去了真正清晰的思想表達。基督圖像志創作方面的衰落與古代神話學的衰落屬于同一過程,關于這一流變將來會有專門著述來詳加描述。到那時,我們會真正了解十九世紀的教堂到底發生了什么。總之從這時起,不再有真正的神學繪畫作品出現,它們作為神學崇拜媒介的地位也難再維持。所以,就這一點而言人類無法再回歸到過去的傳統之中,因為宗教思想已經為純粹的美學思想所取代。 把這種所謂“現代的”建筑學的發展趨勢引向教會建筑領域并試圖取得豐碩成果,那已經是后來的事情,而且,即使一些杰出的、卓越的藝術家可以創造出非凡的成果,然而總體看來,這種教會建筑再創造是失敗的,這如同試圖讓工人們重返基督教的圣殿一樣,是難以實現的。建筑工人們難再信仰基督教,新的技術架構也難再構建基督式建筑了。然而,那些新興的鋼筋玻璃架構的宏大建筑倒似乎內在地呈現了神圣化的內涵,人們不禁會聯想到,這些建筑結構所體現的宏偉觀念也許會預示一種新的教堂類型的出現,確切而言,與古代時期新興的彰顯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宏大建筑出現時的情形類似,這些基督教堂也可以通過相似的途徑從那時的世俗建筑中脫穎而出。然而,這種新的教堂類型的發展機遇卻并沒有引起當時人們的注意,或者即使有人已經意識到,卻無法進行深入的研究。 城堡和宮殿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那個世紀中期的城堡建筑表現出更明顯的保守傾向,比教堂還要保守,它的傳統形式秉承了一種時間上的非關聯性,這啟發了后來博物館的構造。然而,1830年前后,這個領域仍然受到了多方面不確定因素的干擾。一種新的城堡類型出現了,真正明確的意義卻消失殆盡,這成了它必然的命運。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二世時期的城堡建筑,似乎呈現了一種極端風格的一般性創作技法和原則;結果是整個城堡建筑僅凸顯了戲劇性特征,這再糟糕不過了。海倫吉姆宮的凡爾賽系列作品是*能體現這一趨勢的又一例證,許多人都試圖去賦予它更為深刻的意義,可是它實在無法承載。海倫吉姆宮中有一些僧侶居住的房屋,供一位精神幾近崩潰的僧人居住,這種設計幾乎在呼應一種新的“太陽王”(Roi Soleil)風格,然而它的設計方案雜糅了其他各種流派手法,讓人根本無法分辨出它的創作目的和特征。坦白地說,這組建筑是沒有任何意義可言的。這組象征性案例表明了城堡與精神性之間的新的關系—城堡的各種山寨版圖像志形式自身是空洞而蒼白無力的。 在處理這些古代的主要形式問題時人們逐漸加強了對不確定性的強調,這源自對感官感受的過度討巧;事實上,真正有意義的嘗試去構建一個全新的風格,應該源自對于某個全新主題的探索,源自人們努力去解決西方文化早期時代中尚未出現過的一些形式問題,或者世界歷史有所記錄的其他文明中同樣尚未出現過的一些形式問題。 雖然如此,然而,在這場一般性的歷史性回溯開啟之初,我們還是從一種藝術形式入手吧,在過去的七十年間,它一直致力于將精神性與物質性的能量等同地注入大型建筑之中。所以,它完全稱得上是“主要的形式問題”—盡管在它盛行的年代人們有時對于其他形式的研究和考察更為熱心,而且,它的象征性意義對于本書的研究主題而言,意義非凡。下面我們將討論這種主要形式,它是風景花園。 風景花園 在1972年前后的英格蘭,作為對法國建筑花園的一種理性反叛,出現了風景花園這一形式。當時法式花園在外觀設計方面采用了幾何形式手法,后來人們批判這一做法在本質上違反了自然法則。所以,自1760年起,“英式花園”熱潮迅速席卷歐洲大陸,人們的熱情程度之高以及狂潮“席卷”的速度之快,在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根據藝術家的日記記載,英式花園一經興起,它早期的、尚待歷史檢驗的創作探索就立即引發了興建熱潮,到處“大興土木”,那種壯觀景象真是前所未有。許多法式公園都開始紛紛轉型,有時工程十分浩大,他們經改造后*終呈現為英式花園的格局。直到世紀末期,約略1830年前后,整個歐洲大陸都幾乎遍布了自然的英式花園。這種對新藝術的狂熱追求使當時的藝術界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甚至當我們提起世紀末期的阿爾明?馮?蒲克勒—姆斯考王子時—他因為兩次試圖將西里西安的廣袤家園變成單一的風景園區而不得不面臨破產,我們不由得將這一悲劇事件認定為“花園狂躁癥”的盛行所致。 自從文藝復興開始,對先前藝術形式的反叛開始成為藝術理論家反復討論的主題。如今,風景花園在這一點上首屈一指。藝術理論界也對其進行了多方論證。首先,風景花園在折中、融合其他形式之后成為一種*具有綜合性的藝術形式,就空間而言,它融合了雕塑和建筑,甚至可以說,它作為建筑融合了雕塑、繪畫和裝飾等幾種藝術形式。所以,風景花園成為一切想象性藝術作品中堪稱*綜合性的藝術,或者可稱作“超綜合藝術作品”。然而,當我們運用“綜合性”一詞去描述這種藝術時,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一方面,這種描述可說明風景花園確實是建筑的勁敵,首先它僅通過作品的規模就可以超越建筑;進一步而言,對于*壯觀、宏偉的設計而言,它可以自由地利用空間,自由地進行空間創造。在構造方面,風景花園可以利用灌木叢和樹林等有機團塊來進行設計,可以布置小山的方位,并設計出池塘和小溪穿梭在其間,它還可以在這些樹林之中蜿蜒、迂回地點綴一些裝飾性元素,比如一些能盛開美麗花朵的植物叢。在這些大自然的組成要素之外,它可以構成一幅幅無與倫比的自然風景畫,而畫家如果依從它的風格進行創作,也只能在二維的框架里來完成作品;進一步與音樂藝術比照而言,風景花園可以構成一幅幅整體連續性的畫面,這種與眾不同的審美效果只有通過音樂藝術才能體現出來,其他任何藝術形式都是無法比擬的。在它所呈現的這些不同場景之中,它可以移步易景并喚起人們種種不同的感受,比如,人們會時而為壯觀、宏偉的景物所震撼,或者時而陶醉于美景,享受一種宜人、寧靜的氛圍,又或者,人們會隨著景、物的變幻而陷入沉思和憂郁,偶或心生蒼涼之感。而*為重要的一方面是,這種藝術形式與自然自身關系*為緊密,它也在氣質上與大自然*為相像,都是那么令人難以捉摸,又極富于變化性。“沒有哪一門模仿藝術能像風景花園藝術一樣與自然那么水乳交融,也沒有哪一門藝術能與大自然如此相像了。”可見,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風景花園具有明顯的優勢,有關于此的理論論證也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風景花園激發了人們極大的創作熱情,這是當時其他藝術形式所望塵莫及的。人們隨處可以看到,許多人真正熱情地去構建樣式新穎的風景花園,人們對興建風景花園投注了極高的熱情,就這一點而言,甚至堪比巴洛克建筑盛行時期引發的社會反響。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風景花園不僅是一種新的園林樣式的出現。它暗示了一種對建筑霸權的反叛,暗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一種全新的關系,一個一般的關于藝術的新的觀念。 風景花園若要登上歷史舞臺,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人與自然原本的主動性關系必須由被動性關系來取代!這個新的、被動的對自然的從屬關系的確立反映了一個倫理學的以及宗教方面的需求;事實上,“自然”一詞本身如今擁有了一種宗教色彩,這個概念開始獲得了泛神論意義。自然被賦予了一個極高的地位,她成為一種泛靈的力量,能夠滲透到一切人與事物之中去。她不再以一種異化的身份與人類相對峙,人類已經被“同意”織入了她的存在。“在人與自然兩者之間,皆可顯露出相同的富于生氣的實體存在,它是不可言喻的,它友好地靠近我們,將它自身注入一切。自然所創造的一切萬物都是完美的,她所創造的一切都是美的。人類*終的統治者存在于自然之中,用以感受美的理性和內在直覺等,一切都統統被賦予了自然之力。” 英國人阿什利?庫珀是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他被歌德視為*富有才智的人,被視為整整影響一個時代并可以表征一個時代性格的思想家之一。正是這位阿什利?庫珀成了這種新的泛神論自然崇拜的預言者,這一崇拜對整個歐洲尤其是德國影響非常深遠。斯凱爾以及萊內的作品*集中地體現了它的影響,他們是當時*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的很多成就至今仍尚未為人所知。 使園林設計師的藝術盛行的**個條件得以滿足之后,我們再來說明第二個決定性條件,后者幾乎是神秘、不為人察覺的。自然的完善只能以理念的方式存在;這種理念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美(或極為抽象的美),它通過被創造之物散發耀眼的光輝,或者,它可以指向存在于世界起點的原始伊甸園,那也是人們不斷努力尋求回歸的地方。正是這第二種理念或構想,成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性的精神力量。 自然在過去是一座原始的、完美的花園—關于這種觀念的宗教起源說法不一,尚無法得到確切的考證—若以此為前提,那么藝術的任務,就是依據自然的這種*初的完善以及完美性去二次創造自然,在地球的某些地方,這種(完美)狀態已然被保存完好。然而,通常來講(此處的說法也尚待商榷),完美的自然圖畫只能在所謂的“史詩般的”風景畫中被臨摹。 就這*后一點而言,畫家已然在不同類型的美之中做出了選擇,并確定了創作的主題來統一他所選定的對象,他遵從某些特定的規則作畫。他所選取的對象或多或少對應了園林設計師所努力實現的三維的再現。所以,他要經常、反復地思忖那些園林設計師在風格構造方面提供的技法和訓諭,也就是說,他需要用偉大的風景畫家的想法填充他的頭腦,而且,只要有需要或者有的放矢,他自己就要盡可能地充當風景畫家,如此一來,他才能使得他的模仿性作品與完美的原始圖景相統一。因此,風景畫家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要反復構想并設計上帝自己的創造場景并以此為依據,而且,風景畫家只能憑借他們頭腦中的構想,從而使上帝創造之物的完美之處得以顯現。 這些畫家們早先規定的技法和規則,后來隨著時間的進程逐漸喪失了。當新藝術創作進入一種自覺的發展過程,并且開始強調并確立自身的獨特個性和內在原則時,這些屬于過去的種種規則和限定就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然而,即使在這時,人們仍感覺到,園林應該在觀者的記憶之中激發起人們對于古老伊甸園的回憶,讓人們憶起伊甸園、阿卡狄亞、彌爾頓的樂園、極樂之境,或者詩中的田園或仙境。
西方藝術史論經典藝術的危機:中心的喪失 作者簡介
漢斯?賽德爾邁爾(1896—1984) 奧地利藝術史學家,新維也納學派藝術史學創始人,曾執教于維也納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加入納粹黨,不久退黨,卻因此被維也納大學辭退,此后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并以“漢斯?施瓦茨”的筆名發表文章。1951年重返講臺,先后于慕尼黑大學和薩爾茨堡大學教授藝術史。主要著作有《藝術與真理》、《黃金時代》等,《藝術的危機》是其代表作。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莉莉和章魚
- >
推拿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姑媽的寶刀
- >
月亮虎
- >
史學評論
- >
唐代進士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