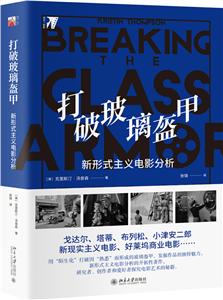-
>
東洋鏡:京華舊影
-
>
東洋鏡:嵩山少林寺舊影
-
>
東洋鏡:晚清雜觀
-
>
關中木雕
-
>
國博日歷2024年禮盒版
-
>
中國書法一本通
-
>
中國美術8000年
培文·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10847
- 條形碼:9787301310847 ; 978-7-301-31084-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培文·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 本書特色
聚焦新千年以后,把握好萊塢電影產業發展脈絡與進程。
培文·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 內容簡介
“古典作品由于耳熟能詳而被罩上了玻璃盔甲……”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這樣寫道。在《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中,克里斯汀?湯普森用十一部電影將讀者“陌生化”。她充分證明了新形式主義分析技法的靈活性。她認為,批評家們常常使用已經固化的方法,再去選擇適用那些方法的影片。新形式主義卻不然,它鼓勵批評家對每部影片都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處理,并不斷地修正他們的分析中的假定。 因此,湯普森的分析新穎多樣且富有啟發,涉及的影片涵蓋廣泛的范圍,從普通的好萊塢片影片《恐怖之夜》,到《晚春》《湖上騎士蘭斯洛特》這樣的大師之作。她提出了一種形式的歷史方法來對待現實主義,并以《偷自行車的人》和《游戲規則》作為實例。《舞臺驚魂》和《勞拉秘史》這兩個案例則說明了古典電影如何通過與觀眾的預期進行游戲,從而將自身的慣例陌生化的。其他章節還分析了塔蒂的《于洛先生的假期》《玩樂時間》和戈達爾的《一切安好》《各自逃生》。 盡管新形式主義分析是一條嚴謹、獨特的路徑,但它避免了大量的專業詞匯和深奧概念:本書各章也可以視讀者的興趣單獨抽出來閱讀。然而,本書的總體目標遠遠不止是讓特定的影片更易理解、更具吸引力,而是提出那些將電影作為一個整體來審視的新方式。
培文·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 目錄
前言與致謝........001
**部分 電影分析的新形式主義路徑
**章 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一條路徑、多種方法........007
電影分析的目的 / 007
藝術作品的本性 / 014
歷史中的電影 / 033
觀影者的角色 / 040
基本的分析工具 / 052
對敘事電影的分析 / 057
本書中的影片 / 065
第二部分 普通影片
第二章 “不,萊斯特雷德,此案中的一切皆非偶然。”
——《恐怖之夜》中的動機與延遲........071
對普通影片的分析 / 071
敘事:梯級建構 / 077
風格與動機 / 100
結論:意識形態的含義 / 121
第三部分 分析主導性
第三章 沙灘上的無聊——《于洛先生的假期》中的瑣事與幽默........135
主導性 / 135
《于洛先生的假期》中的主導性 / 144
風格系統 / 147
敘事系統 / 160
主題系統 / 166
結論 / 169
第四章 鋸斷枝干——作為布萊希特式電影的《一切安好》........173
元素的間離作為主導性 / 173
元素間離的原則 / 177
間離的一般結構 / 193
結論 / 203
第四部分 古典電影中的陌生化
第五章 兩面派敘述和《舞臺驚魂》 ........211
古典敘述中的兩面派 / 211
真假謎題 / 221
戲劇意象 / 235
結論:其他影片中的兩面派 / 248
第六章 夢中的結局?——《勞拉秘史》中的視點 ........253
視點的多個層面 / 253
類型層面:偵探故事 / 266
因果關系層面:夢境 / 268
空間層面:對人物的黏著 / 272
時間層面:過往 / 287
意識形態層面:肖像與兩種男人 / 289
結論 / 302
第五部分 從形式的視角看現實主義
第七章 電影中的現實主義——《偷自行車的人》........309
作為歷史現象的現實主義 / 309
我們何以認為《偷自行車的人》是現實主義的? / 317
主題 / 322
敘事結構 / 324
場面調度與攝影 / 330
意識形態 / 333
對古典電影的引用 / 335
結論:《偷自行車的人》在美國的流行 / 337
第八章 差異性矛盾的美學——《游戲規則》........341
《游戲規則》的主導性 / 341
敘事:平行對應與曖昧性 / 343
空間與時間 / 359
結論 / 389
第六部分 參數形式的知覺挑戰
第九章 《玩樂時間》——知覺邊緣的喜劇........395
參數形式 / 395
知覺的玩樂時間 / 399
知覺的困難 / 405
手法的裸化 / 413
結論:偏離到過度 / 417
第十章 戈達爾的未知國度——《各自逃生》........421
敘事結構與裂隙 / 421
總體策略 / 435
密集的風格織體 / 440
結論 / 452
第十一章 盔甲的光澤、馬的嘶鳴
——《湖上騎士蘭斯洛特》中疏淡的參數風格........457
省略化敘事 / 457
風格的敘事功能與非敘事功能 / 472
結論 / 504
第十二章 《晚春》和小津安二郎的非理性風格........509
風格與意識形態 / 509
非傳統的日本家庭 / 511
隨心所欲的風格 / 521
自我強加的法則 / 528
游戲 / 551
譯后記........581
培文·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 節選
電影分析的目的 電影分析不可能沒有路徑(approach)。批評家們去看電影,并不是去搜集影片的一些事實,再用一種原封不動的方式將這些事實傳遞給他人。我們把一部影片的“事實”看成什么,將部分地取決于我們假定那些影片是由什么構成的,我們假定人們是如何觀看電影的,我們相信影片是如何與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相互關聯的,以及我們的分析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我們沒有仔細考慮這些假定,我們的路徑可能是隨機的并且自相矛盾的。然而,如果我們能對我們的假定進行檢視,至少我們有可能創造出一條比較系統的分析路徑。那么,一條美學的路徑——就我在此正在使用的這個術語而言,是指一整套假定,包括關于不同藝術作品所共享的特質的假定,關于觀影者在理解所有藝術作品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程序的假定,以及關于藝術作品與社會相互關聯的方式的假定。這些假定可以被一般化,并且由此能夠構建起至少是一套粗線條的理論。因此,路徑可以幫助我們在研究一件以上的藝術作品的時候能保持分析的一致性。我會考慮一種更加具體的方法:用于實際分析過程的一整套流程。 一個電影批評家所采用或設計的路徑,常常取決于她或他想要分析影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們會看到,分析者在決定分析一部影片的時候,典型地存在著兩種總體上的方式:一種是以一條路徑為中心,一條以影片本身為中心。 人們在決定對一部影片進行審視的時候,其目的可以是為了證明一條路徑以及伴隨這條路徑的那種方法(method,因為對于大多數的路徑來說,一般只有一種方法)。在當下的學術性電影研究中,這是一種很常見的手法。電影批評家從一種分析方法開始,這種方法常常來源于文學研究的、精神分析的、語言學的或者哲學的方法;然后,她或他選擇一部影片,這部影片看起來很適合展示那種方法。當我在1970年代早期**次開始做電影分析的時候,這種電影批評的聲勢洶洶,似乎是不證自明的。方法是至高無上的,而如果一個人在開始分析影片之前沒有展現出一種方法,就難免被視為幼稚和糊涂。 然而,這種傾向在我看來會出現非常嚴重的潛在危險。電影批評家當然真的可以利用對一部影片的分析,拿來作為對方法的一種實際檢驗,從而挑戰這種方法甚至改變方法。但是,在過去五十年左右[1]的影片分析文字中,更常見的是:選擇一部影片僅僅是用來肯定這種方法。于是,近乎毫不奇怪,精神分析的電影讀物可以通過分析《愛德華大夫》(Spellbound)和《迷魂記》(Vertigo)這樣的影片來完成;這樣的分析很少對一種方法形成挑戰。但是,精神分析的方法能同樣有效地處理《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或者 《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而且不讓影片削足適履地去滿足一種簡單的和扭曲的解讀嗎? 由此,我們遇到這種生搬硬套的手法所產生的另一個問題。事先形成的方法只是用于證明的目的,通常的結果是降低了影片的復雜性。因為方法存在于對影片的選擇與分析過程之前,方法所含有的假定必須有足夠的普適性來容納任何影片。于是每一部影片在某種程度上都必須被認定為“同樣的”,從而使其能符合方法,而方法普適的假定會傾向于消除差異。如果每一部影片都不過是完成了一部俄狄浦斯情結的戲劇,那么我們的分析將不可避免地使得影片開始變得彼此相似。其結果就是影評讓影片看起來沉悶乏味——而我認為,影評工作的目的,至少有一部分是強調影片那些吸引人的方面。 如此同質化的影片分析,更進一步還意味著,由于選擇單一的方法,并如同餅干切割刀那樣,將其強行應用于每一部影片,我們還會面臨在影片分析中喪失一切挑戰意識的危險。我們用來作為例子的是那些適用于這種方法的影片,其結果就是我們的路徑變成了永恒的自我證明。對于系統來說便不存在任何困難,而這種舒適悠閑則會抑制對系統的改變。實際上,對開發出一種方法,再運用這種方法以證明它的電影批評家來說,對系統的改變則常常來自電影領域之外。語言學或精神分析的發展可能會改變這一方法,但電影媒介對它的影響通常卻非常之小(這通常是因為在這樣的一些情形中,*初的路徑本身——無論是精神分析還是語言學等——都外在于美學研究領域)。 在多年的電影工作之后,我已經逐漸遠離這一觀念,即應用一個預先存在的方法來證明這個方法。相應地,我在此會設想,我們通常對一部影片進行分析,是因為這部影片具有吸引力。換句話說,對于這部影片來說,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基于我們路徑既有的假定所無法解釋的。在觀影之后,仍然是難以捉摸、讓人迷惑的問題。這并不是說,我們起步于完全沒有路徑之處。相反,我們總的路徑將不會完全決定我們如何對任何特定的影片進行分析。因為慣例總是處于變化之中,而且現有慣例在任何特定的時刻都內在地有著無限可能的多樣性,我們幾乎不可能期待一條路徑能夠預測每一種可能性。當我們發現一些影片對我們構成挑戰的時候,那就是很確定的信號在敦促我們對它們進行分析,也是很確定的信號在表明對這些影片的分析會有助于延展或修改這一路徑。或者,有時候我們會感覺到,這一路徑就現狀來說,其中存在著缺失,從而有意識地去尋找一部影片,這部影片能給這一路徑的薄弱環節提供分析的困難。我在本書中選擇的幾部影片就是出于這一理由。例如,人們認為形式主義的方法*適合于分析那些高度風格化或者不同尋常的影片。我選擇了《恐怖之夜》(Terror By Night)來開始我的分析,正是因為這是一部相當平常的古典電影。此外,很多人會認為現實主義對于形式主義來說是一種挑戰,于是我分析了那些*廣泛認同的現實主義影片中的兩部——《游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和《偷自行車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從而展示出新形式主義是如何能夠將現實主義分析為一種風格樣式的。 我相信,電影分析包含有一種專注的、細致的影片觀看行為——這種觀看行為讓分析者能有機會以從容不迫的姿態去檢視那些吸引他或她*初的以及后續的觀影活動的那些結構與材料。其實說起來,影片本身就能推動我們去進行這樣的觀看;這就是說,當我們在體驗影片的結構時,在我們帶進影片的觀看技巧和影片的結構之間出現了某種不一致。我們遭遇到我們原本沒能預計會看到的事情(再說明一次,這種不確定的特性可以從路徑自身的范圍中浮現出來:我們可能會認識到,我們原本希望路徑應該包含的某種東西實際上缺失了,而我們因此需要尋找一部或多部影片能幫助我們填補這一空缺)。 在影片刺激起我們的興趣時,我們對影片的分析是為了從形式的和歷史的角度去解釋,作品中究竟發生了什么情況,能讓它提示[2]給我們這樣的反應。同樣,在我們應用一條路徑中產生了一個超出規范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反應應該是轉向一組多樣化的影片,從而去弄明白路徑會如何處理這些影片所產生的問題的。然后我們將這個仔細觀看的結果傳遞給其他人,他們可能也發現了這部影片或相似的影片具有吸引力,傳遞給另一些人,他們至少已經被這個由影片分析所產生的問題所吸引——*終,我們為所產生的這些問題而寫作與閱讀的批評文章會跟對單部影片進行說明的批評文章一樣多。理論與批評因此變成同一個意見交換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 新形式主義是一條走向美學分析的路徑,非常親密地基于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的作品。這些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和批評家活躍的時期是從1910年代中期一直到大約1930年,之后受到壓力被迫改變他們的觀點。在我前一本電影分析的著作《愛森斯坦的〈伊凡雷帝〉:一種新形式主義分析》中,我闡述了*初的俄國形式主義的那些假定是如何可以用于電影分析的。本書我不再回溯到這個環節;相應,我將對新形式主義本身展開論述,不再頻繁地引用俄國形式主義者的論著——引用的主要情況,是在它們可能提供特定術語或概念*清晰的定義的時候。[3]在本書中,我感興趣的是新形式主義是如何應用于電影的,但這一路徑基于很多關于藝術一般屬性的假定。因此,我也將很隨意地引用來自其他媒介藝術作品中的例子。 新形式主義分析具有產生理論問題的潛力。而且,除非我們希望不斷重復地跟同樣的理論材料打交道,我們就必須有一種足夠靈活的路徑,能對那些問題的結果做出反應并加以吸收。這一路徑必須能適用于每一部影片,它還必須在自身之中建立起一種需求——迎接不斷的挑戰,并由此發生改變。每一次分析所能告訴我們的,應該不僅僅是關于目標影片本身的問題,也是關于電影作為一門藝術的可能性。新形式主義在自身內部建立在這種對不斷修正的需求。這就意味著在理論與批評之間的一種雙向交流。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它并不是上述的那樣一種方法。新形式主義作為一條路徑,的確提供了一系列廣泛的假定,關于藝術作品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以及它們在提示觀眾做出反應的時候是如何操作的。但新形式主義不會去規定這些假定是如何嵌入具體的影片之中的。相反,基本的假定可以用于建構一種針對每部影片產生的問題的方法。1924年,鮑里斯·艾亨鮑姆(Boris Eikhenbaum)強調過語詞“方法”(method)的有限含義。 “方法”這個詞必須重新賦予其先前較為溫和的含義,即一種用于對任何具體問題進行研究的手法。對形式進行研究的方法會在堅持一個單一原則(principle)的同時,基于主題、材料以及問題的提出方式不同而可以隨意改變。對文本進行研究的方法,對詩詞韻文的研究方法,對一個特定時期的研究方法,以及諸如此類——這些都是對“方法”這一語詞的自然用法……我們操作的不是各種方法,而是一種原則。你可以隨意想出盡可能多的方法,但*好的方法將會是能夠*可靠地滿足目的的那種方法。我們自己就擁有無限多的方法。但根本就不存在十種原則和平共存的情況,甚至兩種原則都不可能。原則確定了一門特定科學的內容與客體,從而必須獨一無二地存在著。我們的原則是將文學作為一種特定的現象類型進行研究。[4] 實際上,正是艾亨鮑姆所說的“原則”,以及我所謂的“路徑”,使得我們能夠判斷,在我們對一部作品所能提出的眾多(實際上是無窮多)問題中,哪些是*有用以及*有趣的部分。方法于是成為我們設計出來用于回答這些問題的一種工具。由于這些問題對于每一部作品來說是不同的(至少是輕微不同),方法也會是不同的。當然,我們(作為繁忙的專業學者)可以自行將這些事情簡化,每次都詢問同樣的問題,選擇同樣類型的影片,并使用同樣的方法。但這會使得目的落空,這個目的是為了發現每一部新的作品中那些吸引人的或者具有挑戰性的東西;此外,這樣也無法通過每一次新的研究來修正以及闡明我們的路徑。 設想一條總的路徑,這條路徑使得我們每一次新的影片分析所使用的方法能夠得以修正或者完全改變,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新形式主義電影批評就避免了那種不證自明的方法類型所內在的問題。它并沒有事先假定,文本具有一個讓我們的分析活動進入并發現的固定式樣(pattern)。畢竟,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假定文本包含了什么,我們就會傾向于去尋找它。因此,新形式主義將分析當成一種通過實際的影片來檢測其自身的手段,從而避開了俗套(cliché)與單調。
培文·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 作者簡介
克里斯汀·湯普森(Kristin Thompson),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名譽教授。她擁有艾奧瓦大學電影專業碩士學位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電影專業博士學位。她的專著除本書外,還有《愛森斯坦的〈伊凡雷帝〉:一種新形式主義分析》(1981)、《出口娛樂:1907年至1934年世界電影市場中的美國》(1985)、《新好萊塢的故事講述:理解古典敘事技法》(1999)、《電影與電視中的故事講述》(2003)、《劉別謙先生去好萊塢: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與美國電影》(2005)、《佛羅多特許經營:和現代好萊塢》(2007)等。她也是一位業余的埃及學研究者,2001年以來一直是某埃及考察隊的成員。 譯者張錦,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碩士、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文學碩士,國家公派訪問學者。譯著有《電影詩學》《瑪雅·德倫論電影》,專著有《信息與傳播:研究分野與交融》《電影作為檔案》《英國電影編導教育簡史》等。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唐代進士錄
- >
月亮與六便士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自卑與超越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