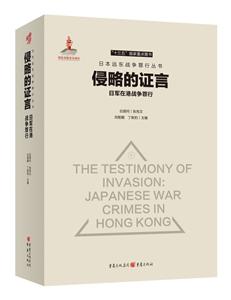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9149567
- 條形碼:9787229149567 ; 978-7-229-14956-7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 本書特色
“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 獨家披露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陸軍部珍貴檔案,實地采訪日軍暴行幸存者及其后代,揭露日軍占領香港的累累罪行。 * “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 * 獨家披露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陸軍部珍貴檔案,實地采訪日軍暴行幸存者及其后代,揭露日軍占領香港的累累罪行 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全國各界以不同的方式紀念抗戰勝利。七十五年前取得的勝利,是數百萬中國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提及日軍的侵華罪行,我們會想到很多,比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等。事實上,日軍在我國內地猖狂肆虐的同時,還將侵略的魔爪延伸到了香港。戰后對日本的法庭審判以及對其罪行的蓋棺定論,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法律資料,被各國歷史研究者所珍視,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對這些資料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便是一本鉤沉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陸軍部珍貴檔案,重現日軍侵占香港的歷史片段的著作。 本書從長達8000頁的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陸軍部檔案中梳理出與日軍侵占香港有關的暴行,并根據檔案中提到的線索,實地走訪日軍罪行發生地的幸存者和他們的后代,通過檔案翻譯和口述記錄的相互印證,補充了日軍戰爭罪行的證據鏈條。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臭名昭著的日本憲兵隊對當地居民和來自各國的戰俘所實施慘無人道的虐待、屠殺,讓數以萬計的人失去了生命,而幸存下來的普通市民和戰俘,提到那段悲慘的歲月,仍然會不寒而栗;侵占香港的日軍為了節省糧食,將市民遺棄荒島,導致餓死、病死或者死于非命者無數;殘酷不仁的憲兵隊對戰俘進行虐待后,丟棄在人滿為患、擁擠不堪的俘虜收容所,導致痢疾、白喉等傳染病肆虐,越來越多的被關押者死于惡劣的環境;更有甚者,即便是在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之際,日軍依舊以搜捕游擊隊為名,對香港當地民眾實施猖獗的報復……《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再現了香港近代*黑暗的那段歷史,揭露了日軍占領香港的累累罪行,揭示歷史真相,意在告慰逝者,更在警示后人。 本書結合檔案,無可辯駁地揭露、批判了日軍在香港的罪惡,彌補了國內相關領域的空白,有助于推進全球史視野下的日軍戰爭罪行研究。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 張憲文本書收集整理了日本奴役香港的歷史資料,用日本戰犯的自供狀,揭露了日軍占領香港的累累罪行,發人深省,令人深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日本史學會榮譽會長 湯重南這是以全球史視野研究日軍侵略香港暴行的探索之作。深入揭露二戰中日本侵略罪行,警示后人,拒絕戰爭,捍衛和平,應為中國史學界的學術擔當和歷史責任。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 翟新本書作者根據庭審線索,實地考察了許多案件發生的地點,專程采訪了部分重要暴行的親歷者和受害者,極大地豐富了歷史的細節,讀后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連紅本書以英國國家檔案館藏陸軍部檔案為依據,整理出香港軍事法庭記錄,并以此為據,真實再現了日占時期香港的深重苦難,揭示歷史真相,意在告慰逝者,更在警示后人。 ——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軍事歷史》總編輯 潘宏
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 內容簡介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然襲擊香港,香港的英國守軍奮戰十八天后彈盡援絕,被迫投降。在其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占時期,日軍對香港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奴役。由于種種原因,香港近代很黑暗的這段歷史一直被掩埋,直到近十年才引起歷史學界和香港普通市民的廣泛關注。 為了更加全面、真實地展現這一時期的歷史片段,揭露日軍占領香港的累累罪行,香港史專家劉智鵬教授、丁新豹教授撰寫了四篇專題研究,詳細敘述了日軍猖獗恐怖的暴行;又從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數量龐大的陸軍部檔案中整理、翻譯出十份香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珍貴檔案,并根據庭審線索,實地考察了許多案件發生的地點,專程采訪了香港日軍戰爭暴行的部分幸存者及其后代,根據他們的口述實錄,撰寫了十個專題報告。 本書是揭露日軍在港戰爭暴行的力作,以翔實的資料展現了日軍占領香港時期,當地居民和來自英國、加拿大等國戰俘被日軍隨意逮捕、審問、虐待的悲慘遭遇。他們不僅要擔負繁重的苦役,還要與白喉、痢疾等傳染病肆虐的居住環境作斗爭,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殺戮和酷刑。從十八日戰爭到深水埗戰俘營、赤柱監獄,從圣士提反書院慘案到銀礦灣慘案,無一不是日軍累累侵略罪行的鐵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 目錄
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 節選
強迫歸鄉 日軍攻占香港后,首先要面對糧食不足的問題。香港生產的糧食有限,雖然戰前香港政府貯存了足夠的糧食,但都陸續被日軍調往前線用作軍糧,剩余的糧食不可能維持一百八十萬人口的生計。日本人為解決糧荒,打算將大量人口遷離香港,強迫他們回鄉,務求將香港人口減至五十萬,以減輕對糧食及其他物資的消耗。 日軍占領香港后隨即實施歸鄉政策。按照日軍的計劃,遣返的類型分為三類。**類為自愿遣返:歸鄉市民會以自費方式離港回鄉,或是通過社團及同鄉會的協助歸鄉,這些團體會協助他們申請離境證(渡船許可證),亦會協助他們購買離港的船票,也會資助無交通費的民眾步行回鄉。第二類為勸諭遣返:經勸諭而離港的人會獲政府提供寄宿、膳食及交通資助,費用全免,他們會登上由政府安排的船只,送往內地的指定地點。*后一類為強迫遣返:對象為無業流浪人,即流氓、乞丐等,以及罪犯如劫匪和強盜,憲兵會將他們拘捕,再集中于難民營,待人數足夠后就用船運走。離港后政府會給他們派發少量的糧食及金錢。 歸鄉政策由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的民治部負責統籌,并成立歸鄉事務所協助執行。另外通訊部、交通部、衛生部及海港辦事處亦有參與,并負責陸上交通、安排船只及船上衛生等工作。憲兵隊的主要工作是在街上拘捕民眾,再帶他們到北角難民營等候遣返,并且派員看守難民營,以防止有人逃走。其次,憲兵與警備隊要在遣返過程中隨船而行,負責警衛事務。除了官方機構外,總督亦要求“兩華會”協助執行歸鄉措施,負責勸諭無業流浪者“自愿”回鄉,以及聯系各社團和同鄉會協助市民歸鄉。 日軍起初只是勸諭市民自愿撤離,但由于未能達到預期成效,憲兵早于1942年年中開始在街上抓捕平民,再用船只將他們強行運返廣東各地。到了1944年底至1945年初,拘捕行動更為嚴厲,憲兵在街上用繩索圍捕市民,被捕者無論是何等職業、何等身份,都一概囚于難民營,等候遣返。 除了以上部門,區役所也會協助執行遣返措施,其中一項工作為接受被捕者家屬的保釋申請。由于憲兵濫捕,因此有不少市民無辜被抓,這些市民的家人可以到區役所申請保釋,如經調查證實為有米票,以及有戶口登記,就會獲發證明,準予釋放。不過申請的程序非常繁雜,實際上能夠獲釋的人只占被捕者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家人要先到區役所申請,取得保釋證明后轉交到地區事務所登記,再呈交遣返辦公室處理,*后才到達難民營。如此一來需時甚久,故即使家屬能取得保釋證明,但到命令下達至難民營時,被捕者很大可能已經上船遣返。 悲慘的歸鄉旅途 很多難民在遣返的過程中,都沒有獲發足夠糧食;有的甚至未出發就已經餓死于難民營之中。即使能抵達目的地,難民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甚至無法繼續走動。日軍為防止香港物資外流,只準歸鄉市民攜帶少量行李,以致他們饑寒交迫,不少人死于流亡途中。 1942年,歐蓮(音譯:Au Lin)和她的夫曾茂庭(音譯:Tsang Mau Ting)被迫遣返。農歷四月初四中午,夫婦二人正在吃午餐,突然一批憲兵及印籍憲查闖入家中將二人拘捕,并帶到駱克道的一個防空洞內囚禁。洞內有士兵負責把守,防止有人逃走。翌日早上十點,他們被趕上貨車,運往西環登船。他們被捕時,身上全無行李。當時一同被捕者有數千人,被運往西環者共有近萬人。碼頭合共有十九艘船,他們二人乘坐的船只較小,只能載幾百人。登船時,每人獲派兩斤白米、兩個面包、國幣十元。登船后,士兵將他們推入船艙,禁止他們進出。 啟程時已是晚上七時,十九艘船由一艘火輪船拖領。開行不久,即遇上風暴。當時憲兵在火輪船上值班,由于火輪船抵擋不住強大風浪,憲兵于是斬纜自逃。剩下的十九艘船在海面漂流,其中多艘沉沒。歐蓮二人所乘的船只船頭破裂,大量海水涌入船身,致多人死亡。 船只漂流四日四夜后,開始有一火輪船“金星”號到場施救。當時海上只余下三艘船,船上有不少尸體。火輪船把船只拖行到一山邊,再由漁船把難民接駁上岸。據船夫所指,上岸地點名為“半天云”。上岸后各人沿路而行,有些人因過于饑餓而無法走動,只有留落在沙灘上等死。因為早前有另一批難民流落到此地,所以岸上遍布尸體,臭氣熏天。二人由黑夜走到日出,終于抵達一個村落,幸好當時身上尚有余錢,*終能返回香港。 此等事件在淪陷期間時有發生。1944年6月,漁民彭任升(音譯:Pang Yan Sing)在捕魚期間無故被憲兵拘捕到赤柱憲兵部。幾日后,憲兵帶他到北角難民營。到營后隨即登記姓名,并在此處囚禁了十日之久。當時難民營內有八百多人,眾人均表示不知因何被捕,亦無經過審問。五六日后,營內人數增至一千人,憲兵便將他們分成兩組,各自登上兩艘帆船前往南澳。此外,還有一艘載有數名憲兵及憲查的火輪船,他們配備槍械,準備射殺跳海逃走者。 船只在早上八點起程。到達長洲后,火輪船離開,憲兵指示帆船水手將難民帶到南澳。當船駛到擔竿山時,由于風浪太大,要折返蒲臺島。這時船身進水,水深及膝,四五十名老人跌倒并且溺斃,尸體被拋落大海。到達蒲臺島后,船只下錨停行。彭任升趁機跳入水中,游到岸邊,找來一艘小艇。他把艇駛到船邊,救下其余二十多人,并帶回赤柱大潭灣水塘附近上岸。 1944年12月某日下午三時,莊娣正在山邊撿拾柴枝,突然有數名憲兵及憲查將她拘捕,并用刺刀刺傷她的背部。當時還有三名老婦人被捕,均被控撿拾樹枝。四人被帶到香港仔警署,到翌日運往北角難民營。囚禁在營內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更有小孩,門外有憲兵把守。兩星期后,在囚人數已有近四百人,憲兵于是強迫眾人登上一艘船的船艙內。眾人在船上既無糧食,又無獲發金錢。到了下午五時,船只啟動,船上難民均不知其去向。 二十四小時后,船只終于停航。所有難民被帶到船面。日本憲兵從眾人中挑選出身體健壯者,將約七十名殘弱及患病者逐一用刀斬殺后推落大海,然后命令余下的人登上另一艘帆船,并將他們帶到岸邊,上岸后始知該地名為“平海”。莊娣徒步走到惠州淪為乞丐。某日,她遇見兒子的朋友,朋友帶她到英軍服務團營地。在惠州逗留三個月后,她收到兒子從四邑寄來的錢,*終在1945年4月返回家鄉。 難民慘死荒島螺洲 螺洲島是一個無人居住的荒涼海島,位于香港島東南部鶴咀半島和蒲臺島之間。1944年7月,憲兵用兩艘船將數百名難民送往此島,遺棄于島上后隨即離去。雖然螺洲島與對岸的島嶼僅一水之隔,但流水湍急,即使擅長泳術者亦難以渡過。有部分難民為求生存,唯有冒險一試,可惜他們多已饑餓無力,*終多人溺斃。 留在孤島上的人,由于缺乏糧食,只好將死者身上的肉切下來進食,以免餓死。在島上,求救慘叫之聲不絕于耳,聲音隨風傳到對岸的鶴咀村。村內的漁民都不敢前往拯救,因為當時鶴咀村及赤柱均設有憲兵部,若漁民把難民救回村內,必定為憲兵所知,會處斬施救者。可憐的難民*終都相繼死去,尸體遍布于岸邊的石頭之間,有的被大浪沖走,有的被人吃掉。1945年5月,有漁民登上螺洲島,發現海濱暴露著很多人骨殘骸。 根據日方的統計數字,自日本占領香港直至1943年9月為止,離港人數已達九十七萬三千人,當中有三十八萬一千人自愿離港,五十七萬六千人經勸諭后撤離,還有一萬六千人屬強制遣返。當時日方已與內地商討,經勸諭離港的人士會集中遣返太平及江門兩個指定地點。1943年11月,遣返的地點增加了惠州淡水、汕頭等九個地方。 強迫遣返的地點則多數集中于大鵬灣一帶。1943年6月至12月期間,已有六千至九千名難民涌入大鵬灣,平均每月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他們從大鵬半島不同部分登陸,到處找尋食物,導致這個地區的饑荒問題日益嚴重。難民中身體較佳者,多向北面前進,步行四日到達*近的惠州難民營;年老體弱者多不能承受長途跋涉的磨難,每月至少有四百人死于路途。
侵略的證言:日軍在港戰爭罪行 作者簡介
劉智鵬,廣東揭陽人,華盛頓大學博士。現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歷史系教授,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主要論著有《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體回憶》《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等。 丁新豹,廣東豐順人,香港大學博士,曾任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大學名譽院士。代表作有《香港歷史散步》《香江有幸埋忠骨》等。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自卑與超越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巴金-再思錄
- >
煙與鏡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