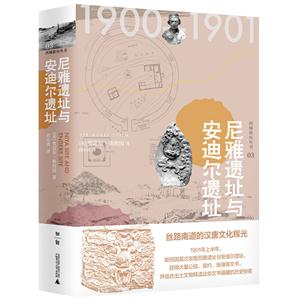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尼雅遺址與安迪爾遺址:1900-1901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27135
- 條形碼:9787559827135 ; 978-7-5598-2713-5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尼雅遺址與安迪爾遺址:1900-1901 內容簡介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奧雷爾??斯坦因先后到我國新疆及河西地區進行探險考古,并先后出版了這三次探險考古報告:《古代和田——中國新疆考古發掘的詳細報告》《西域考古圖記》《亞洲腹地考古圖記》。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較全面地記述了我國新疆漢唐時期的遺跡和遺物,以及敦煌石窟寶藏與千佛洞佛教藝術,揭開了該地區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紗。西域游歷叢書集斯坦因這三次中國西部探險考古資料于一體,對上述考古報告進行整合修訂,使大眾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經過和成果。叢書共15冊,本冊出自《古代和田——中國新疆考古發掘的詳細報告》:1901 年上半年,斯坦因首次發掘尼雅遺址與安迪爾遺址,獲得了大量的佉盧文、漢文、婆羅米文文書,并結合出土文物釋讀這些文書蘊藏的歷史秘密。
尼雅遺址與安迪爾遺址:1900-1901 目錄
**章 尼雅河盡頭以遠的古遺址
**節 廢墟 N.I 和首次發現的寫板 .........................................1
第二節 發掘古代住宅 N.II、N.III、N.IV ..............................29
第三節 古代垃圾堆 N.xv 中的發現物 ....................................53
第四節 古代木板和皮革上的文書 ..........................................65
第五節 古代垃圾堆 N.xv 出土的漢文文書和木簡 ..............88
第六節 解讀佉盧文和漢文古文書 ..........................................96
第七節 踏察廢墟 N.VI ~ N.VII 與遺址縱覽 .....................112
第二章 安迪爾遺址
**節 前往安迪爾河 ...............................................................137
第二節 發掘安迪爾寺廟 ...........................................................144
第三節 安迪爾遺址的廢堡和佛塔 ........................................164
第三章 喀拉墩遺址探險和探尋媲摩古城
**節 喀拉墩遺址探險 ...........................................................180
第二節 探尋媲摩古城 ...............................................................196
第三節 烏尊塔提和烏魯克吉亞拉特遺址 ...........................204
第四節 吐噶墩和克里雅至和田大道 ....................................217
第四章 阿克斯皮爾與熱瓦克遺址
**節 杭桂塔提和塔木烏格勒遺址 ....................................223
第二節 阿克斯皮爾和克格里克遺跡 ....................................229
第三節 熱瓦克佛塔 ....................................................................243
第四節 熱瓦克寺院的雕塑 ......................................................255
第五節 熱瓦克遺址的年代和朱拜庫木遺址 ......................277
第五章 離開和田
**節 伊斯拉木·阿洪及其偽造物 ....................................283
第二節 在和田綠洲*后的日子 .............................................295
第三節 從和田到倫敦 ...............................................................300
尼雅遺址與安迪爾遺址:1900-1901 節選
第四節 古代木板和皮革上的文書 上述古垃圾堆出土的大量文書,個體的形狀與質材上的多樣性,與大部分良好的保存狀況一樣明顯。這使我們可以方便地將對它們的描述,與對整個遺址出土文書主要類型的表面布局,與這些古代木、皮“紙”的制作技術的綜合分析結合起來。 佉盧文皮文書是 N.xv*先清理出的醒目的新東西,因此評述正好從這里開始。由于發現的總共 23件文書中,有不少于 11件是完整的,而且另有 3件也幾乎是完整的,所以這些文書總的形狀與布局從一開始就弄清楚了。從完整的標本判斷,這種文書總是由平整精致的橢圓形羊皮制成,只在一面書寫佉盧文,字行與長邊平行。大部分文書中,正面右邊底緣附近,與正文分開一段距離寫有簡單的日期項:mase(月)…divase(日)…,以及表示月、日的數字。我沒有見到一件文書上署有年份。幾乎所有保存正文抬頭部分的文書,起首格式都相同,為國王陛下敕諭,表明是官方文書,前文我們已經提到,這是楔形底牘正文起首的程式化套語。這些文書也一樣,套語與正文本身的開頭部分之間有很大的間隔。不用此格式開頭的文書沒有幾件,我們可以推測它們屬于非官方性質的文書。 大多數皮文書被發現時都疊成小冊子,其余的文書從羊皮磨損的折痕和其他痕跡判斷,以前也是折疊起來的。仍然保存完好的折疊著的文書,大多數我不怎么費勁就打開了。這些文書的折疊方法是:皮片沿縱線對折,然后再沿同一方向對折一次,這樣就將皮片沿縱向分成了四小片,*下面的一片一般只包含有日期項,成為折疊的窄長冊子的表面頁之一,但它的書寫面則朝里。這樣,整個寫有字跡的正面就得到了保護。*后,再將這樣折疊成的冊子垂直對折。這樣,文書左面的底緣可見切開一條半連著的窄條,左面本身朝左的折頁*末端折轉過來,剛好露出抬頭的首行字跡。盡管不那么清楚 ,其他皮文書中也見有類似的切條。我因此做這樣的猜測,即這種切條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與這種文書的捆綁有關。皮文書確切的捆綁方式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對此作過一些觀察,我認為值得在此一提。 鑒于為了保護寫在雙楔形或雙矩形木牘上的通信內容不被非法拆閱而采用了非常巧妙的設計,因此可以依此類推,為了保護皮文書,尤其是寫有官方律令的皮文書的內容不被非法拆閱,也一定采用了某種設計。按現在式樣做的信封當然可以達到這一目的,但在 N.xv的垃圾堆中,沒有發現任何這類東西,而其他種類的“信封”又那樣豐富,所以這個否定的事實就顯得很重要。在幾塊較大的皮文書中,有兩塊特別有趣。但有明確的跡象表明,這兩塊皮文書的第三折和第四折之間曾插有一個扁平的橢圓形物體,那里有曾放置的插入物在文書正面留下的凹印痕,以及由此引起的相應部分顏色的消褪。很明顯,這個插入物在那個位置保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以至于留下如此持久的一個痕跡。更可能的結論是,這個插入物是一枚印章。印痕是在與半連著的皮條同一面的文書上發現的,這個事實表明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系。 可以想象,不止一個裝置通過蓋上印戳被固定在那里。窄皮條散頭可能通過這樣一個裝置繞過折子的邊緣,*后從有印痕的兩個折層之間穿過。不過,由于沒有這方面的任何直接證據,詳細描述這種裝置毫無意義。按剛才所推測的方法捆扎起來的皮文書,如果要打開,則必須將皮條割斷,或者毀掉封印,就像打開泥封的佉盧文木牘那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如何才能防止重新插入一個新的假印記。折頁之間的有效空間非常有限,要在封料上插入一個合適的印記很困難。不過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像這些古代文書抄寫員那樣機敏的書吏,可以克服這一困難,尤其是如果封料主要是黏土,就像從該遺址未啟封和未分開的木牘上發現的所有印記那樣。在皮文書上我沒有發現任何殘存下來的真正的封印,因此只有對現已不存的封印留在皮面上的印戳進行化學檢查,也許才能使我們弄清所用的物質是什么。它對字跡不會產生影響,就像封臘一樣,這一點幾乎不必特別解釋了。 通過上述折疊處理,包含正文的整個文書正面得到了保護。背面除一行簡短字跡外,全都是空白。所有保存完好的標本中,這行字均出現于露在外面的那層折頁上。這一短行字總是以同一個單詞 dadavo(意為寄給)結尾。在所有楔形封牘正面的繩孔附近也出現這個字,其前面的兩或三個字總帶有屬格詞尾 -sa。這些事實表明,這行字包含的是地址。緊接所有官方文書起首格式之后,經常出現相同的名字,其中*常見的是州長索阇伽,由此我當即就確信這個推論是正確的。由于它的位置暴露在外,地址的字跡已變得模糊甚至被部分擦掉了,但正面原來的黑色墨跡大多完好保存。這樣,即使是皮片本身已經褪色或被染污,字跡也依然清楚可辨。 我很遺憾沒有安排對這種古墨進行化學檢測。但是,從其特征判斷,很可能是中國(或印度)墨,例如我在安迪爾戍堡邊的垃圾層中發現的那種小墨棒。木牘(包括佉盧文木牘和漢文木牘) 上所用的墨質量和濃度有很大不同,但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表明墨水成分存在差別的跡象。 上述文書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它們是至今發現*早的書早期印度語的皮文書標本。現存關于古代印度用皮革作書寫材料的文獻證據極其少見而且不確切。這一現象很容易認為是宗教方面的原因所致,因為根據宗教儀式,動物本體被認為屬于不潔之物。但這里我們有無可否認的證據證明,無論理論上有什么禁忌,它們對和田佛教徒的影響事實上并不比對克什米爾正統婆羅門的影響大。婆羅門可能從很早時期起就習慣于用皮革裝訂梵語法典,并一直延續至今。那些古文書反映出的精湛的皮革工藝,表明在材料的加工上已具有豐富的經驗。相同類型的小塊空白皮片無疑是從整張皮片上撕下來的,然后又被掃出公務房而成為垃圾。它們表明,住在這個廢棄住宅中的官員不僅收到過皮信,而且也向外寄出這種信件。盡管如此,與各種木牘相比,這種文書的數量相對較少,這無疑證明木材是當時更加流行的書寫材料。皮質材料的明顯優勢是輕便和易于處理,此外書寫者還可根據自己當時的需要進行裁剪。但木料可能更便宜,而且用它制作的“信紙”更易于捆扎。無論優先選擇木頭作為“信紙”材料的理由是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木牘不可能是當地制作,因為垃圾堆中沒有出土制作木牘時剩下的木屑和其他“木紙”殘跡。 沒有什么比 N.xv出土佉盧文木文書之間的巨大差異和總體保存良好的狀態,更使我能夠比較容易地弄清與它們不同類型的用途相關的全部技術細節。這里發現的楔形牘甚至為數更多(我們已從 N.i發現了很多),其中有 6對保存完好的完整雙牘,此外還有 45塊封牘和 34塊底牘。它們平均尺寸與首次發現的那些楔形牘完全一致。 仍然保存有扎繩的完整雙楔表明了這類文書的書寫和發送方式。繩子是寄信人當初用來將雙楔扎牢用的。這類文書一律由成對的木牘組成,相互尺寸完全匹配。每一套雙楔牘中,兩塊木牘的厚度也完全一樣,僅封牘的封泥座所在部分加厚。其余部分則可能與牘的大小和木頭的質量有關。很可能木匠在制作這種“信紙”時,首先在總體上做出一個楔形,然后將其鋸或劈成兩塊。 N.xv.24的制作者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因為其封牘和底牘的內表面顯示的斷紋相同。這種雙牘一頭削成方形,另一頭逐漸變尖,靠近尖部鉆有一個貫穿上下兩塊木牘的穿孔。正文寫在底牘磨平的正面,成行書寫,與楔形的上長邊平行,而且沒有一處超過 4行,其上置上牘或封牘以保護。封牘還起到一種信封的作用。如果信函內容較長,就接著寫到封牘的背面,其方法是:當封牘打開翻過來,整個正文可以同時看到,并且兩塊牘上的字跡方向一致。封牘 N.xv.24的位置將說明這一點。 封牘方頭較厚,外表面突起部一般位于離方頭 1.25~2.5英寸處,里面雕刻一個粗糙的矩形封泥座。在 N.xv.71和 N.i.103中,這個座或封泥凹穴是空的。而在 N.xv.137和 N.xv.24的封泥座中,則還填有封泥。封泥座和封牘長邊的邊緣之間,形成兩條突起的邊框,上刻三條線槽,以便用線繩子將成對的木牘捆綁起來。扎繩的方法很巧妙,安德魯斯先生所畫線圖(見下頁圖 A~D)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完整的楔形牘和許多分開的雙牘上多少還保留著很長的麻線,麻線先巧妙地穿過封牘和底牘的線孔,如圖 A所示。事先在線頭打出一個線圈(如圖 B所示),將線對折過來,把單線搓成雙股。然后把封牘放到合適的位置,將它的背面與底牘的正面相合,接著將兩牘尖頭的連接線圈拉緊,再將線沿底牘背面拉到封泥座的位置,如圖 C所示。在這里,這根線規則地扎成十字結,一律按圖 D所示方法,扎在封泥座的上面,在 N.i.103中也可見到,與封泥座相通的線槽用來固定線結的位置。*后,沒有固定的那端線頭在穿過離木牘尖頭*近的上緣線槽后,扎到底牘背面的縱向扎線部分上,并在那里扎緊,打成一個結,然后在封泥座中填上封泥,將交叉線蓋住。封泥上一旦蓋上寄信人的印章,如果不破壞印跡或切斷捆扎的線繩,就無法打開木牘。 這種巧妙的布置可以確保木牘內所寫內容的安全,防止非法折閱和篡改。如果接收人想保存封泥,同時希望閱后能夠方便地重新捆扎(一個明顯的優勢就是這種信可以隨時保存供以后參考),他只要在線孔附近將線剪斷即可。底牘因而就能很容易地從印下方的連接線中滑出來,閱畢又可重新插回到原來的位置。雙牘 N.xv.24、137在歷經這么多世紀之后,我們現在仍然能夠依此方法打開并重新恢復為原樣。 可能有這樣的情況,打開并閱讀后,楔形雙牘的收信人認為用一種明確的方式來保持兩塊木牘的聯系很重要。雙牘 N.xv.71是這方面的一個有趣的例子。它除保存有正規捆扎所需的全部布置(包括部分線)外,穿過兩塊木牘線孔并將它們捆扎在一起的一條單獨的短線上,還黏附著一塊很堅硬的微紅色封泥。這根線的質量與正常捆扎所用的線不同。我由此以及由幾乎不能穿過兩根線繩的小線孔我推斷,現在的捆扎線及懸掛著的封泥是文書被啟封后重新加上去的。我們發現,它的封泥座是空的,這次可能是用將原來填在封泥座中的封泥弄破這種方式啟封的。否則,處在封泥座中受到保護的封泥,似乎應比線孔處完全暴露的封泥更好地保存下來。若干現代法律文書的扎線或帶子上黏著的,同樣顯然也是這種封泥。對封泥的進一步描述留待介紹矩形木牘時再進行。這里簡單提一下保存完好的木牘外表面常出現的詞目,以結束對楔形文書的說明。封牘正面總是寫有收信人的姓名和頭銜。從方頭邊緣向封泥座方向書寫,空間不夠時,則延伸到封泥座的對面。封牘 N.xv.24、137上的名址讀作“Cojhbo Sojakasa”,即“致州長索阇伽”,這是所寄達官員的頭銜和姓名,在發掘 N.xv.時我就認出來了。那里發現的許多佉盧文文書,不論是皮質的還是木質的,都是寄給他的。如果這類文書是寄給兩個或更多的人,其姓名、地址行則向尖頭方向延續到封泥座對面,就像 N.i.104+16中的那樣,這件文書正面上的收信人姓名是州長毗摩和稅監黎貝耶。線孔左面,并且通常離線孔很近,寫著單詞: dadavo(意為寄給),這個詞是對封牘另一頭前面姓名、地址項的界定。 底牘背面靠近方頭規則地書寫一個簡短的詞條,如 N.xv.122、137、N.i.9。在拉普森教授翻譯的完整文書中,這個詞條總是包含有正文中作為送信人提到的使者或其他人的名字。其他底牘背面上所見相應的詞條可能用作同樣的目的。我們也有在介紹信的信封上寫送信人名字的習慣,這與之完全相似。在 N.i.122的背面,這一詞條的位置上橫向刻著三個大字。木牘的正文我看不懂,但能讀出其中一字為 Prascaya,這說明它們也包含有文書委托人的名字。在 N.xv.137的背面,除方頭附近明顯包含有送信人名字的一條簡短條目外,還有 4行寫得很密的字跡,雖然部分字跡已嚴重褪色,但仍可清楚認出它們出于不同人的手筆。波耶爾*近出版了一篇關于這件有趣文書的譯文,其中還附有注釋,認為它是一份拘捕某些逃亡者的命令。他表示,背面上的記錄已部分解讀出來,涉及的是同一對象。這難道是楔形雙牘的收信人州長索阇伽這位官員所處理過的命令或摘要?一個更粗陋、奇怪的特征是,有些底牘的背面刻有粗糙的刻痕。 N.xv.17.a上刻的是一個卍字符,N.xv.04、05上刻的是一個畫有一短線的小圓圈。顯然,它們都是些區別標記,可能是依照“尼散”刻畫的,印度有在信封上畫符號的習慣,以方便不識字的送信人正確遞送。在 N.xv.121中,我們發現封牘正面刻有兩個十字符。 如上所述,我們只有根據 N.xv.出土的真正完好的標本才能明確地弄清楚矩形雙牘的使用和捆扎方法。和 N.iv一樣, N.xv出土的這類佉盧文木文書大部是分開的散牘,曾經合在一起的封牘或底牘缺失。這里出土的這種不完整的文書中,封牘有 28塊,底牘 19塊。和楔形文書一樣,封牘占有主導地位,這一特殊結果是在這些“廢紙”被扔進垃圾堆的過程中形成的。啟封后,“信封”必然首先被扔到那里,而相應的底牘則可能要留下來以備以后參閱或作其他處置。這些處于分散狀態的木牘板外觀看起來令人迷惑不解,但當我發現**批四套完整的矩形雙牘( N.xv.151、155、 166、196),一切疑難便迎刃而解。從其中的 N.xv.155、166這兩件上可清楚看到,底牘兩側各有一條突起的緣,緣寬分別為 0.5和 1.25英寸。兩條緣之間剛好放進一塊封牘,封牘的正面中部突起,在突起部中心刻一方形或橢圓形封泥座。 .......
尼雅遺址與安迪爾遺址:1900-1901 作者簡介
奧雷爾·斯坦因(1862—1943),英國人,原籍匈牙利,20世紀上半葉享譽世界的考古探險家和東方學者。在英國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國新疆及河西地區進行考古探險。根據其考古探險經過及成果,先后撰寫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國新疆考古發掘的詳細報告》《西域考古圖記》《亞洲腹地考古圖記》等。 肖小勇,博士,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出版《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等譯著7部。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煙與鏡
- >
二體千字文
- >
莉莉和章魚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隨園食單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