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F(xi��n)���桶��������v����ͥ���Ѻۣ�������ͥ�P(gu��n)ϵ�е������c��С�
�Є�����(bi��o)ӛ����P(p��n)�ȸ�����ȫԔ��(x��)Ʒ���f(shu��)��>>
-
>
һ��(g��)İ��Ů�˵ā�(l��i)��:�������ƪС�f(shu��)��
-
>
Ů�˵Ą���
-
>
�絝�ʵۡ�ȫ����(c��)��
-
>
��������ӛ
-
>
ѩ��(gu��)
-
>
��߅�Ђ�(g��)С�u(m��i)��(��(hu��)��Ӱ���b)
-
>
����ӛ
(��)�������� ���(qu��n)��Ϣ
- ISBN��9787559623669
- �l�δa��9787559623669 ; 978-7-5596-2366-9
- �b������(ji��n)�b��
- ��(c��)��(sh��)�����o(w��)
- ���������o(w��)
- ���ٷ��(l��i)��>
(��)�������� ����(sh��)��ɫ
�^���r(sh��)�g֮�g������Ů���ӌO��֮������˹��ɯʿ�ȁ���ϵ��2018������: ���������ڱ�����÷���_˹��ԭ�������ؘ�(g��u)���������
�F(xi��n)���r(sh��)�գ����Jҕ�ǣ�С�f(shu��)��ʽ���F(xi��n)���桶��������v��ͥ�Ѻ��Լ������P(gu��n)ϵ�е������c��У�
���귭�g�����٩��(d��n)�V���g��*�ȱ���Ӣ��(gu��)��ͥ��ҵ������ζ��
���E�����ڲ��ҵĕr(sh��)��l(f��)����ֻ�����E�l(f��)���r(sh��)����(��i)߀��(l��i)�ü��
(��)�������� ��(n��i)�ݺ�(ji��n)��
�������l(shu��)��һ��(g��)��ý�ۇ�(gu��)�ľ����ߣ���(qu��n)����ؔ(c��i)���Ƿ���O�����^(gu��)�Ƕ����^(gu��)ȥ�r(sh��)�ˣ��F(xi��n)�ڣ������ǂ�(g��)�������������ˡ��ɂ�(g��)Ů�������^��������؝���͚��̣������H������Ӣ���m���^(q��)һ�Ұ��F�į��B(y��ng)Ժ��w�S���B(y��ng)Ժ�����ͳɹ��ˡ��ڿ�����Ļ�Ұ�У����뵽����ʏ�������ġ��@��(g��)�~���ؚw���c(di��n)������˼���������l(shu��)������ԓȥ�ă���������ԓ����������ݛՓ�������������У��](m��i)��֪�����͵����䡭��
(��)�������� ��(ji��)�x
���҂��](m��i)�г�ˎ���������f(shu��)��
���҂�ͣˎ�ˣ�/�҂������ˣ�����Ƥ�س�������(l��i)�����҂������ˣ��҂�ͣˎ�ˣ����죬��ͻȻ�������ͣ����������\ʲô�����҂��Ŀ�ˮ߀����ë������˯���I(l��ng)���ϣ��ɬF(xi��n)���҂���ͣˎ�ˣ�ˎ�����ڻ�ƿ���Щһ�~�m�˿��(zh��n)�o֮�O��Ҫ����ÿ���յ���Щ�ٺϡ�����
��һ�뵽��Щ�ٺ����l(shu��)�͵ġ��������ͺ����
�����o�����ϼһ��
���ҵĵۇ�(gu��)������͵���ˣ��Q��(l��i)��ʲô���@Щ�ưٺϣ���
��������Ҳ�ѵۇ�(gu��)�o�G�˰�����Ƥ��ͻȻ�Q��һ��Ψ��ʧ�Y��Ů���˵Ę��ӣ�������һ���ð���ʮ��̖(h��o)���g�ļ��Ľ�B�o���J(r��n)�R(sh��)�������@���õ��Ǽ����ݣ��䌍(sh��)���ǣ���Ƥ���։��������������vɽ���ۡ���
��ȫ�Ǻ��f(shu��)�˵��������ͳ��R�������������˺ö����ˡ���
���](m��i)�e(cu��)����Ƥ�ش˕r(sh��)���˹��R�� �������t(y��)������Ҫ���@Щ�ٺ��������_���z�����һЩ������ѵăA��ע�⣬ֻ�ǃA��ֻ�dz����ܵķ������˸������Aб���^�nj�(sh��)��?q��)����ǷN����ô�������İY���ǿ��Ծ���ģ�ֻ��(hu��)����һЩ���Ժ��Բ�Ӌ(j��)�ĸ����á�������ǰ̽�����ӣ��`��������Щ���˵�ˎ�Ҿ����ڻ�ƿ�����İٺ���һ�𣡡�
���^(gu��)ȥ��������^(gu��)һ��(g��)�ۇ�(gu��)���������f(shu��)�����Ҹ��](m��i)�����f(shu��)�^(gu��)������ô��͵�ߵģ���
���f(shu��)�˺ܶ���ˣ��ϵܣ��ܶ���ˡ���Ƥ�ص���˼�ֲ�֪�h���˺�̎��
�����M(f��i)�ŵ����������Σ��u�u�λεؿ���ײ����K��ֱͦ�����ӣ��(y��ng)��бб���صȲ����ļӺ��������[���۾�����
���Ү�(d��ng)�r(sh��)�������d�f(shu��)���ҵ���(w��)��(hu��)׃�ɡ��Lj�(zh��)�ж���(hu��)��ϯ�����������_(k��i)ʼ�ˣ��������w�C(j��)���S�ġ����a(ch��n)�ͱ�Ҫ���ؙ�(qu��n)�����ǰ���?f��)?d��n)������������������һ��ƿ�ٺϣ�С�ĵ�?c��i)[���ذ��ϣ������ճ����������С�����?f��)?d��n)�·š��Խ������Ҿ����@�Ӹ����f(shu��)�ģ��������ҟo(w��)�n�n�]���Θ�(l��)��(ch��ng)�����ԕr(sh��)�գ�Ҳ���ɞ���һ�˪�(d��)��������������
���ѣ��@��ã���Ƥ���f(shu��)��������������һ�˪�(d��)���������������@��֮ǰ�](m��i)�f(shu��)�^(gu��)����
������һ�ж��ǚw�ڡ����С��ģ��������d�����f(shu��)�����S���������룬����Ҳ����(d��ng)����(l��i)�������͵������С������ʲô���](m��i)�ˡ��](m��i)��һ��?x��n)|���ǿ��Լȱ����ߣ����ܱ����ġ�����
���@�ǟo(w��)���Sϵ������(ch��ng)����Ƥ�ز���һ�䣬������R.D.�R�� ���ǂ�(g��)���� �f(shu��)��һ�ӡ���
�����v����ĕr(sh��)��Ո(q��ng)��Ҫ����ң��������f(shu��)�����Ҹ��V�����d�@ֻ�Ǟ��˱ܶ����Ұѹ�˾ֱ�ӽ��o������͛](m��i)���^�ж��ˡ���߀�ǽ��c(di��n)���ɣ��������d�f(shu��)������t������ڄ��Z�Լ����^�Й�(qu��n)������
�������@��(g��)�����d��ϲ�g����Ƥ���f(shu��)���� (t��ng)��ȥ���ǂ�(g��)���ˣ����ǂ�(g��)��ˎ�������ǣ����X�ӵ��ˡ� ��
����ֻ��һ��(g��)�X�����ֲ��ǹ�������Ͳ��͟����f(shu��)�����ҵ��ǃɂ�(g��)Ů�������ݫF����
��ֻ��һ��(g��)�X������Ƥ���f(shu��)�����@�һ�ɉ�](m��i)�ŵģ���ֻҪ���˿�������ˎ���X����þ�Ůñ����۷��Ƶ� ����
�����ˣ����ˣ��������f(shu��)����̧�^�����컨�壬Ȼ��ģ�������d���ȵ��������](m��i)�Й�(qu��n)����������Ͳ�Ҫ�ԑٙ�(qu��n)����������Щ�����ˡ���t����ֻ�����ǣ�������ͣ�D��һ�£������ڌ���һ��(g��)��������f(shu��)������*��߀���ǃɂ�(g��)�~���Ϸ���ʯ��Ϳ�������Լ����^픡��������䡢���ˡ�����
���������䡢���ˡ�˥������������Ƥ���ñ����݆T������f(shu��)������̤��ÿ��(g��)����(ji��)���҂�����խխ�ĉ�?z��i)����_(t��i)�A�ϵ��_����ô�pӯ������һȺ���¡���˹̩�� ������������(d��ng)�IJ��ǹ��ȣ�����砵�����
��Ҋ(ji��n)���������͝q�t��Ę�f(shu��)���������ܲ��ܲ�Ҫ���Ǵ���ң���ǰ���f(shu��)Ԓ�ā�(l��i)����(hu��)����ࣻ����ֻ��(hu��)��혵� (t��ng)���������_(k��i)��Ҳ�Ǟ��˹��S�ң�Ҫô���ڸ��Ұ�ʾʲô��ؔ(c��i)֮�������㡭���㡭����
�����������т�����Ƥ���f(shu��)��������ǰ����һȺ��ŭ�ı�ͽ�� ���o�@λ����һ�c(di��n)���g���҂� (t��ng) (t��ng)������ʲô���f(shu��)�ġ���
�����ҵ����õ����e��ָ�֮�(hu��)�_���������ͺ�������Ү�(d��ng)�r(sh��)�����@ô�������d�f(shu��)�ġ����ҬF(xi��n)��ֻ��֪ͨ���ҵěQ�����](m��i)�І�(w��n)�����Ҋ(ji��n)����ֻ�܌�(sh��)�F(xi��n)�����С�����
������̧�ۿ��컨�塣
�����Ҳ�ֻ������Ɏ�������������߀ʣ�µ��������棬���Ǻ��㽻��*�õ�һλ�ˡ����f(shu��)�@Щ�Ǟ��˱��o(h��)�㡣��
�������xҲ���з����ģ�����ŭ�ȵ��������Լ�һ�ք�(chu��ng)�k�Ĺ�˾������Ҫ?ji��ng)e�ˁ�(l��i)������ô�������������e��ȭ�^���컨��]�˓]�����Ǿ�Ԓ�f(shu��)�꣬��ץ���(sh��)���Ϸ���һ�Ѽ������g��һ��(g��)����ؐ�ᵰ�� ���ѽ�(j��ng)���ǂ�(g��)�µ�����(g��)�ˣ���Щ���(gu��)�����^�ġ��ʼҚ��ɡ�����˟o(w��)Ȥ������һȺ�q̫���l(f��)��(h��)���`��(gu��)�ߣ��������_���Z�����Ļ��H��(gu��)�ݡ����Ҳ��ò����@Щ��ԓ���Ķ��(gu��)����������һ߅�Rһ߅����ö�ʵ����M(j��n)�˕�(sh��)������ıڠt�����һ��ȫ���������m�������@�����Ů����ô�f(shu��)��(l��i)�������҆�(w��n)�����d���������`���`�� ��ԓ���Ķ��(gu��)�����`���`��������
�������d��Ȼ��������(d��ng)���ҵ��@Щ��С��Ƣ�⡯�������ճ����@�ҵ��t(y��)�o(h��)�F(tu��n)�(du��)Ҳ��Щ��(d��n)�ġ��㿴�������͌�(du��)Ƥ�ؼ���(d��ng)���f(shu��)�������F(xi��n)�����ѽ�(j��ng)��ȫ���x����������뷨�ˡ����ѽ�(j��ng)���ˡ�����
���������ѽ�(j��ng)���ˡ������Ɂy��Ҋ(ji��n)�� �������R�ֵ�Ƥ���t(y��)���f(shu��)����
���ޣ��e�ٽo�����t(y��)���ˡ���
������ԓ���l(shu��)����Ƥ�؆�(w��n)��
��Ҋ(ji��n)�����������Լ�����
�������@��(g��)��߀��̫��(hu��)���������c(di��n)һ��(g��)����ģ��һ�c(di��n)�İɡ��s�����f�� ��ô�ӣ���Ƥ�؛](m��i)�еȻ؏�(f��)�����Ï��@�Ƶط�?j��ng)_��ȥ�ˣ��������������L(zh��ng)���Z(y��)�{(di��o)�f(shu��)�������������䣬�҂��@�ɂ�(g��)�����Լ����\(y��n)�������ˣ���ԓ�ڜص��נ� �ľ��^��(w��n)���Ҫ�ƺ��ˡ���
����һ���ð��ҵĹ����v����(l��i)�������Ͱ�������(l��i)�����ϵ۰����e�Ұl(f��)������
����֪������Ƥ�،�(du��)���͵İ����ƺ�ҕ����Ҋ(ji��n)�������ǣ����^(gu��)ȥ�ǡ�������(j��ng)�ǡ������l(shu��)���f(shu��)�������^(gu��)���˛](m��i)�С���һ��(g��)������ϲ���݆T�����һ��ˑn���Y��һ�N���ԵIJ��Y�������f(shu��)����ϲ���˵ı����Բ��Y�������f(shu��)���DZ����Ե�ϲ���˵ľ��Кvʷ���x�IJ��Y�������f(shu��)�����^(gu��)��ϲ���˼���ı����Բ��Y������ͣ���І�������f(shu��)�������X�Ӂy�ˡ���
���٣��ҿ������ˣ��ҿ������ˣ���Ƥ�؏�������������(l��i)��һ߅��һ߅��ס�����͵��ֱۣ�����Ҳ���D(zhu��n)����(l��i)�����������^(gu��)�^�ϣ���׃?c��)�����������ĸ�ͻȻֹͣ��߀һ�����_(k��i)�����͵ļ���@�r(sh��)����(l��i)һꇄx܇(ch��)�r(sh��)݆̥Ħ��·���������Ƥ�ز��M(j��n)��(l��i)���@��Ԓ����Ӱҕ����Į�(hu��)���������^(gu��)������Ҳ������ϵĄ�(d��ng)����������(g��)����һ�Ӵ�������P(p��n)���ڑ���߅��܇(ch��)ͣס�ˡ���
���ҿ��^(gu��)��ĺܶ���ף������ͺ����ؑ�(y��ng)�������ںܶ���(g��)��Ļ�ϡ���
��������Ҳ�](m��i)�f(shu��)���Ǫ�(d��)һ�o(w��)����ѽ����Ƥ�ص���ɫ���зN�t�d���Ժ���������ֻ����һ��(g��)Ƥ�ء��ֿˡ�1953�꣬��?y��n)�ĸ�H������ұ������@�����I�ȡ� ����(sh��)�ϣ���(d��ng)�r(sh��)���ₐ�ص��Ԓ������Ѓɰ���ʮһ��(g��)Ƥ�ء��ֿˡ��ǵ���ȱ����(ji��n)ֱ�^(gu��)ʣ����
����վ�ڷ��g���У���ס��һ�ӡ�
�����ҳ��h(yu��n)�ˣ���Ƥ�ؚg����f(shu��)�����������f(shu��)�f(shu��)��ġ��t(y��)���F(tu��n)�(du��)���ɣ����^����
���ҵ��t(y��)���F(tu��n)�(du��)���������X��һƬ���v���@��Ϥ���~������߅�ęڗUһ�ӱ���ץס�����](m��i)�e(cu��)���](m��i)�e(cu��)�������ҰћQ�����V�����d��ǰһ�죬�ҵ�˽���t(y��)���U���Լ��ҵ������d�������f(shu��)�ҡ����X����ЩС���ӡ���߀�f(shu��)��������δ�l(f��)�F(xi��n)ʲôֵ�ô���^(gu��)�֓�(d��n)�ĵĆ�(w��n)�}������
���@�����y��߀��ʲô��ԓ���^(gu��)�֓�(d��n)�ĵ����Ƥ���̲�ס��(w��n)�������y����Ҫ�҂����m��(d��ng)����(d��n)�ĵ���߀��������
���͔[�[�֣��](m��i)�ж�����(hu��)�������s���sһֻ�e��(zh��)�����nω��
�����ǣ�����(j��)�ǂ�(g��)�M���Ԓ���t(y��)�������Ǘl���r�Ķ��ߣ��ƻ���׃�� ��ʮ�����ˡ���������(y��ng)ԓ�t(y��)�g(sh��)�ܾ�տ�Ō�(du��)����������Ψһ�IJ��˿ɲ��DŽe�ˣ����Ұ������������ͣ�����һ߅�f(shu��)��һ߅���������ţ������������͡���
������(hu��)���ǂ�(g��)���ô��ý��ࡪ�����������Ͱɣ���Ƥ�؆�(w��n)����һ���d�^�y�͵Ę��ӣ���������*���X(qi��n)����֮һ�����S߀�����f(shu��)���@��(g��)������*�Й�(qu��n)��(sh��)���ˣ���
���ǣ��ǣ������ң������ҵ����֡����ҬF(xi��n)���f(shu��)��ijЩԒ���B������(l��i)����������u���ͣ�D(zhu��n)Ȧ���Ҿ��f(shu��)������(j��)�ǂ�(g��)�ɐ�����ͽ���ҵ��ǂ�(g��)�t(y��)������(y��ng)ԓ�M�����Ұl(f��)Ƣ�⣻����l(f��)��Ƣ��Ҳ�S��ȥ����Ҫ̫��(d��ng)���¡���
���������磬�L(f��ng)���������^(gu��)���^(q��)�r(sh��)����Ƣ�⡯���_(d��)��픷壬��Ƥ�ز���(b��o)���������h�ҕ�C(j��)ǰ���^�����M(j��n)�ؽѣ������Լ�������ʯ�^�ϡ���
���͓]�������ֱۣ����ǐ��˵��nωԽ��(l��i)Խ���ˡ�
���ҡ����҄��f(shu��)�����ˣ�����(du��)������СС�l(f��)��һ�»������d߀�Ǜ](m��i)ʲô����(y��ng)������X(ju��)�ò����Ҳ��nj�(du��)�ġ��@�r(sh��)����ע��ڠt���ǂ�(g��)�ʵ��ƺ��](m��i)�ܵ�ʲô�����������ǿĉ��ˣ��������ǽ������ģ����](m��i)��혏��ҵ���Ըˤ��(g��)���顣�����^(gu��)ȥ�����ҵ�����֮ŭȫ̤���@Ҫ���˱Ư�������ϣ����@�|�����������и��y��(du��)����һ�Ⱦͻ����ˡ�߀���Ҽ��r(sh��)ץס�˱ڠt�ܣ��ś](m��i)�е���(g��)���ߵء��ҿ�Ҋ(ji��n)���\(ch��ng)�������dվ����(l��i)�����������¡����@һ��ŭ��M�����D�r(sh��)��������(l��i)��
���������ˣ����������Ҹ������d�f(shu��)�������ǂ�(g��)�ʵ���Ŭ����������Ŀ֑֣��@�N�֑��ԏ��_(d��)��˹�Ǵ�Ī�����������֮���һֱ�m�p���ң���ˤ�������@�����Ϝy(c��)�����w�ٱ����ҡ����Ҳ�����ؓ(f��)��(d��n)�@ô�����ˣ������f(shu��)���������(hu��)�տ��ҵģ���������*ϲ�g���ϰ�Ϲ����ô������
����(ji��n)����֮����Ƥ���Ý��صľSҲ�{�����f(shu��)�����������Լ���Ů��׃��������ĸ�H���������������ڡ��l(xi��ng)�������͡��h(yu��n)�ο����� �Ĺս��ό�(du��)�����f(shu��)���ǘӡ�
���Ұ��x��*���Ĵ����_(k��i)�������Ͳ��Ƥ���^�m(x��)�f(shu��)�������Ѳʵ�Ͷ�o�˴��^(gu��)���L(f��ng)�������˽���Ҫ�յ���Y�ˣ������f(shu��)��
��������^�](m��i)�ȱ����Ʋ��У��������d�f(shu��)�����X���Ƚ��K��Ҫ����ˡ�����
�������@��(g��)�����d�������ǻۡ���Ƥ���f(shu��)��
����Ҫ���ҵ��� (t��ng)Ҋ(ji��n)���ˣ����������ģ�Ҳ����߅���£����˶����L(zh��ng)�[��ϲ��������ʹ��͛](m��i)���@ô�����ˡ������@���f(shu��)�������������dһ��(g��)�Y����@�������һ��(g��)ȥ�ɡ������(gu��)���`���`����̫���ˣ�Ҫ����(g��)��ؐ�ᵰ��b�b���ࡣ���Ҵ��_(k��i)��ϣ���ͬ��һ��(g��)���W�W�Ļ��ږ|���G���^(gu��)ȥ�������d���Һ��ҵļ������@�������İё��ѽ�(j��ng)�Î�ʮ���ˣ�*����һ��(g��)��������(l��i)����ͣ������҂����ڻ��@��������(g��)��ͨ�ļ�ͥһ�ӡ�����(g��)Ŭ�����[��ͨ��ͥ�ļ�ͥ�������d�p�ɽ�ס�ʵ�������һ����tɫ�ĵ��������漚(x��)С�@ʯ�v�M���e(cu��)��(g��u)�ɵľW(w��ng)�����������u(p��ng)�������L��������߅�������ϣ��ʵ�����÷ɭ���ȱ� ���u�u�λο�ס�ˡ���
����(x��)��(ji��)̫���ˣ��H��(��i)�ģ���Ƥ���f(shu��)�����F(xi��n)�ڳ���ϲ���Ԅٵđ�(d��o)�ݣ����e�e�á���
�����㑪(y��ng)ԓ���ٱ���һ���ֹɷݣ��������d�f(shu��)���������ҬF(xi��n)�ھͿ��Ը��V�㣬��������(hu��)�����S���h(hu��n)��һ̖(h��o)������˽�õġ�747�����ܚw�ڂ�(g��)�����¡���
�������S��������������(l��i)�������S�����͵��뷨�l(shu��)����r�����͵�Ը���l(shu��)�ҷ��棿��
�����Ͱ���߀�Æ�(w��n)���Ƥ���f(shu��)�����������Լ����l(shu��)Ҳ�](m��i)���@�ӵę�(qu��n)������������(j��ng)�У��^(gu��)ȥ�С���
���](m��i)���@��(g��)�l���ҵĶY��Ͳ��o�ˣ����f(shu��)�������������ҵ���˼��(l��i)���ɣ���
���T(m��n)�������������������׃�����DZ�����Ұ�F��
��������һ�䣬��Ƥ���f(shu��)��һ�¸Z������߅�������^��ӛ�ã���ˎ�Ę���Ҫ�У����e������ȥ���������P(gu��n)�յ����������Ǵ����������ӣ����҂������Խ�z֮�r(sh��)����
���](m��i)�e(cu��)���](m��i)�e(cu��)��������Ҳ����(y��ng)�����������������ӡ��M(j��n)��(l��i)���������К��(sh��)�غ���һ��
Ƥ���ž��ںߡ�����ՙ�������}����(l��)���@�r(sh��)ͻȻ������գ�����۾���
����Ҳ��ؑ�(y��ng)�������o(w��)���քe���������۲����Y(ji��)����׃�Ɍ�(du��)��Ƥ���p��ͬ�r(sh��)գ��գ��
��λ�o(h��)ʿ����С܇(ch��)�M(j��n)��(l��i)�ˣ�����ȫ��ˎƿ�����ϱ���
���������������ѽ�����_�����o(h��)ʿ�f(shu��)�����������Кq��(sh��)���^���һλ�����҂������X(ju��)����ô�Ӱ�����
�����Л](m��i)�����^(gu��)���_�����o(h��)ʿ����Ƥ�؆�(w��n)�������҂����ܲ�ֻ��һ�N�ľ������Λr�ǃɂ�(g��)�˼���һ�𣿡�
������Ҫ���ҁ�(l��i)�@���ˣ��ֿ����������_�����o(h��)ʿ�f(shu��)���������҂��Л](m��i)��ȥ�ە�(hu��)������
���҂��ľە�(hu��)�҂�?n��i)��^(gu��)�ˣ��ܸ��d�������R��(b��o)����һ�ɜ�ů��͵Ě���У��҂��ɹ��غʹ��һ����ܵ��˴��ͥ�Ĝ�ů����
Ħ���D�o(h��)ʿ�̲�ס����Ц����(l��i)��
���e�Z���������_�����o(h��)ʿ�@���ʾ���u(p��ng)�����҂�����(hu��)��͵͵��ȥ�ư��˰ɣ���
������Ү�(d��ng)��ʲô���ˣ���Ƥ�؆�(w��n)��
��һ��(g��)���^��β�ľƹ��������_�����o(h��)ʿ���S������
�������߀��ʲô�|���ܰ����T���@Ƭ�e�����J(r��n)�����g��(l��)������Ƥ�����ó����������݆T������������@��(g��)�ّn���ֵı��L(f��ng)�۞�����̎����Ȼ�ē�ο����ɽ�����������֭�����ʣ���I�羄��������Щ�ɑT�͑�(h��)�������ġ���
�����ˣ����_�����o(h��)ʿ�f(shu��)�����҂���(hu��)���o��ġ���
�����@÷���»ʌm���Ƥ���f(shu��)��˲�g׃���һ��(g��)��܊�y(t��ng)�������҂��ķ��l(w��i)�����˰ٷ�֮��ʮ���c(di��n)�ţ��ǰٷ�֮���c(di��n)һ������������ゃ�@Щ�һ�Ѽ�����һ��܊���i���˴��_(t��i)�ϣ�����˪���е�����һ����ָ����
��Ϲ��Ҳ�����˰ɣ����_�����o(h��)ʿ�f(shu��)�����@��ƿ��ô�ڵ��ϣ�Ħ���D�o(h��)ʿ�����韩��һ�Ȼ��Ո(q��ng)�����ֿ����������Լ����g������������Ҫ���ݡ��F(xi��n)�ڴ�ҵ���(g��)�e�ɣ���������Ҳ����Ƭ�̵İ�������
�����r(sh��)Ҋ(ji��n)�ˣ���Ӌ(j��)�������s�����f�����f(shu��)����������գ�����۾���
����߀���p��ͬ�r(sh��)գ�˺Î��£���ʾ������(du��)������˼��
������˳�ȥ֮���_�����o(h��)ʿ������܇(ch��)�M(j��n)���P�ҡ�
������㆖(w��n)����Ҋ(ji��n)���ҵ��X(ju��)�����ٸ��ֿ���������һ���ã������f(shu��)���������������ġ���
���ǵģ������͑B(t��i)���t���������f(shu��)�ú܌�(du��)���o(h��)ʿ���@������Щ�y�߰���ģ��Еr(sh��)�������X(ju��)����Щ���¡���
���H��(��i)�ģ����X(ju��)�ÿ�����һ�c(di��n)Ҳ�����⡣��(sh��)Ԓ�����f(shu��)���ҏā�(l��i)������(��i)����ǧ����Ƥ�ء��ֿˡ�����ÿ�ζ��Q�_(t��i)�����X(ju��)�ßo(w��)Փ��ô���^�����ǵ��ᡤ�P ����ѽ���Ǖr(sh��)��Ҹ��μ�һЩ��߀�еϿˡ���Ī�� ������Ц�����ˡ�����һ߅�Ĵ������͵����^һ߅��߶���������;����ڴ��أ���Ȼһ�������˲�֪�Լ����ں�̎��ģ�ӡ�
���F(xi��n)�ڣ��҂�?c��)��������ˎ�ˡ����_�����o(h��)ʿ�f(shu��)�����������ɂ�(g��)ˎƿ���֏įB����܇(ch��)һ�ǵ����ϱ���ȡ��һ��(g��)��
���҂��ȳ��@��(g��)�Gɫ����ɫ��ˎ���@ˎ�ɺ��ˣ����˕�(hu��)�X(ju��)�ú�ů�ͣ�����̹�������ñM���ܺ�(ji��n)�ε��Z(y��)�ԣ��@�ӿɑz�������Ͳ����� (t��ng)������Ȼ���ٳ��@��(g��)��ɫ�Ĵ�ˎƬ���@�ӾͲ���(hu��)��˼�y�룬����(hu��)�X(ju��)��Ů��������(��i)�҂���֮�(l��i)�ģ��ɲ�����Ů���������X(qi��n)�҂�����÷�����@����������طł�(g��)�L(zh��ng)�ن�҂���(d��ng)���@ô����������æ���۰�����ԓ�ú���Ϣһ���ˡ���
����֪�������ǐ�(��i)�ҵģ���ģ������ͽ��^(gu��)С���ӣ����Ҿ��Еr(sh��)���(hu��)�X(ju��)���Ժ�����
���Ժ��������ģ����_�����o(h��)ʿ�f(shu��)������������ŕ�(hu��)��(l��i)�@��ѽ���@���҂��Ϳ���������ˡ���
����߀��һ��(g��)Ů�����������̈́��_(k��i)�˂�(g��)�^��
��߀�Ђ�(g��)Ů�������_�����o(h��)ʿ�f(shu��)��������ȣ������ȥ������˹�t(y��)������һ����Ą����ˡ���
���Ͱ�ˎƬ���M(j��n)������^(gu��)�_�����o(h��)ʿ�f�^(gu��)��(l��i)�ı��ӣ����˿�ˮ�����м��س��o(h��)ʿЦ��Ц���ڴ����ɺã������f(shu��)Ԓ��ֱ�Ӱ��۾�Ҳ�]���ˡ�
���������ش�(g��)��ɣ����_�����o(h��)ʿ����С܇(ch��)�����ߣ�������(g��)�É�(m��ng)����
һ (t��ng)�����T(m��n)�P(gu��n)�ϵ��������͵��۾���ı��_(k��i)����������(l��i)����ˎ���������Ȼ��Ĵ�������(l��i)��������͏d�
���ݫF���������������Ե��R�������d����˺���ҵ��ģ��ҵă�(n��i)�K�����������������^���y����ë��ȫ��Ѫ�ۺ͠��⡣���p����ʎ���v؛����Ȼ����������˽���t(y��)�������@�˿ɓ�(d��n)ؓ(f��)�������͙z�����w����؟(z��)�������Й�(qu��n)���ɼ����͵�Ѫ�Ӻ���ӣ��z�����Ƿ���ǰ���ٰ��������Ͳ�����[��ı����w��������������������˽���t(y��)�������������������ġ�������̫�^(gu��)����(d��)�����ċD�ƴ���������мˣ������Ľ��Ź��ߣ���Ы��ļ���o��
������Ĵ�Ĵָ��ˎƬ�Ļ�ƿ��ƿ�i̎������ȥ��
���ゃ�Ԟ����@Щˎ�������ƣܛ��ţ��������f(shu��)����ͦ�ã��ゃ*�î�(d��ng)�ģ��ҵ��@Щ�v؛������Ҫ��(l��i)�ˡ���߀�](m��i)�ꡣ��Ҫ��(b��o)����Ҫ����߀�](m��i)���Ҫ��ʲô�������ҡ�����
�~���t�t����(l��i)���Q�ı��_(d��)��������ŭ����������Խ��Խ����ֱ�����_(k��i)ʼ�l(f��)����������ͬһƥ�����l(f��)���M(j��n)�����ǡ������ܵͳ���ҲԽ�l(f��)��ˣ�ֻ�����벻��Ҫ�����?q��ng)���ͻȻ�����Ͱѻ�ƿ�e�^(gu��)�^픣�Ҫ�����η��Ĵ���(h��)������ס�ˣ����Ҳ���ȥ��Ҳ�Ų���(l��i)�����o(w��)�����ܡ��͡�һ�o(w��)���ܡ��������w��һ��(ch��ng)���(zh��n)�������О鶼��˵����ˡ�
(��)�������� ���P(gu��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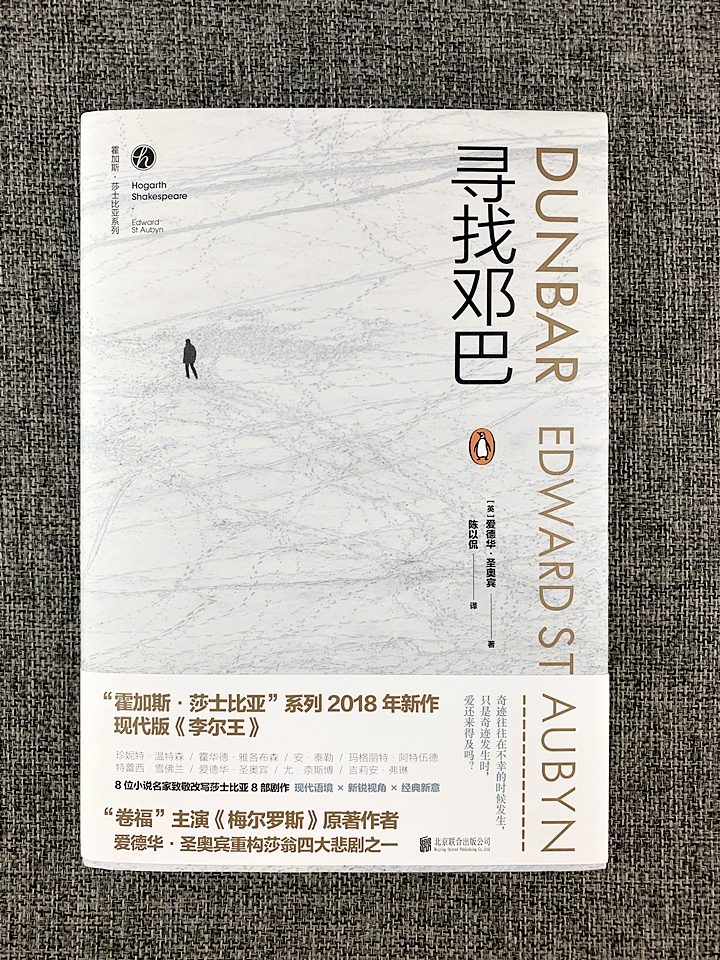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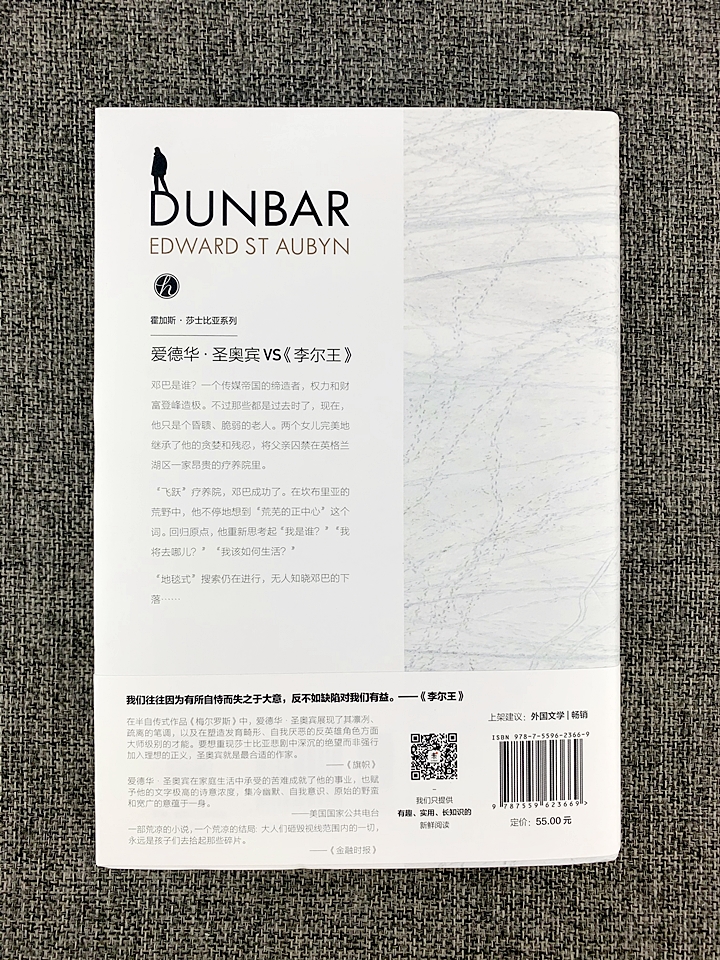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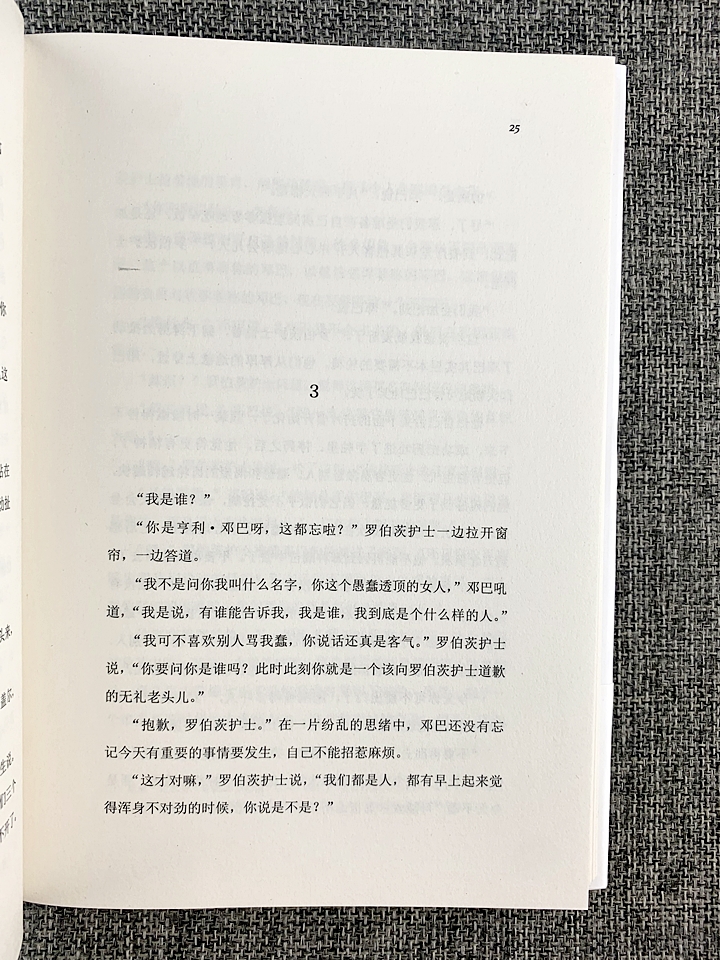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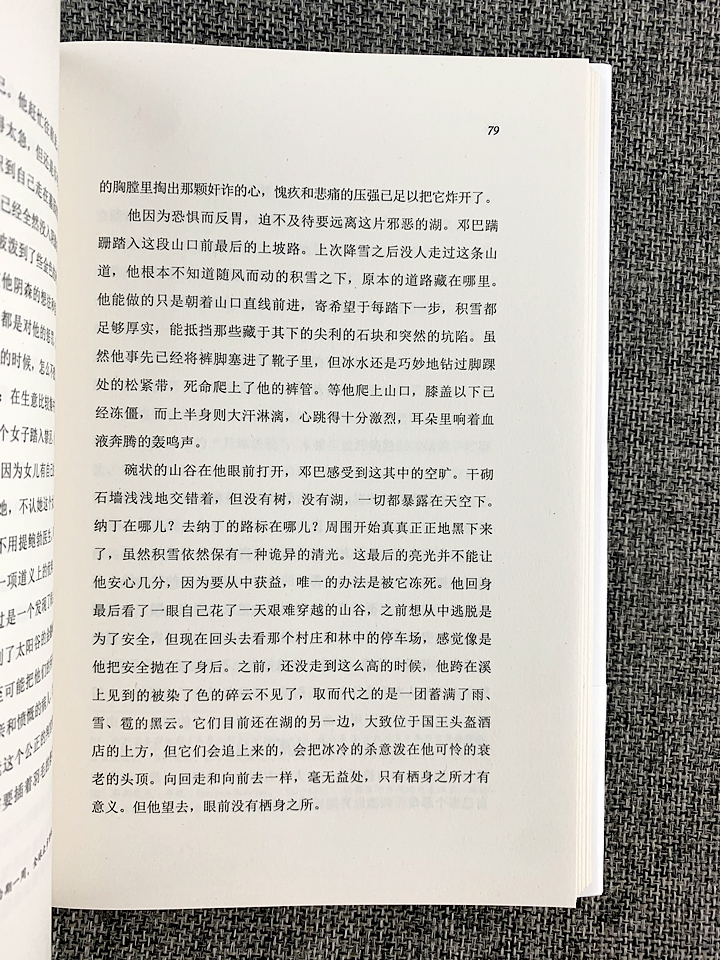
(��)�������� ���ߺ�(ji��n)��
��(��i)���A��ʥ�W�e��Edward St Aubyn�������˪�(ji��ng)�������ң�Ӣ��(gu��)��(d��ng)����ͥ��
��(��i)���A��ʥ�W�e����Ӣ��(gu��)�������(hu��)�ă�(y��u)��֮�ң�ͯ���L(zh��ng)���⸸�H��Ű����19�q�M(j��n)��ţ���W(xu��)����(x��)�ČW(xu��)�������^(gu��)�����ί������^(gu��)�ɶλ���������ǃɂ�(g��)���ӵĸ��H�������@�ο����Ľ�(j��ng)�v��(xi��)�M(j��n)���Ԃ��wϵ��С�f(shu��)��÷���_˹������(j��)С�f(shu��)�ľ���ͬ�����ㄡ���ڽ����_(k��i)�������ݱ���Ͽ��ء���������Q(ch��ng)ٝʥ�W�e�ǡ���(d��ng)��Ӣ�Z(y��)��������Խ������֮һ����
��(sh��)�ϣ��@�εČ�(xi��)���΄�(w��)��ʥ�W�e����(d��ng)�ҵ������硰ë�����]���ġ������_(d��)�ˌ�(du��)����ɯʿ�ȁ��P����C(j��)��ʧ�{(di��o)�ļ�ͥ���(zhu��n)�Ƶļ��L(zh��ng)��������dȤ������˹�������Y������~�����������p��������(zh��n)�̮�(hu��)���ڿ��ͥ�P(gu��n)ϵ�Ѻ۵IJ��ܡ����Q(ch��ng)���Č�(xi��)���������������x����(du��)��(��i)���A��ʥ�W�e��(l��i)�f(shu��)�������ͬ�ڹ�ķ���أ����](m��i)���L(zh��ng)ƪ�Ī�(d��)�ף���?y��n)����](m��i)�����������J(r��n)֪��������ץס�@�εęC(j��)��(hu��)̽��һ�£�������R(sh��)�͝����R(sh��)�ﵽ�װl(f��)����ʲô����
- �x��:�L(zh��ng)��1***(ُ(g��u)�I(m��i)�^(gu��)����(sh��))
- �x��:******(ُ(g��u)�I(m��i)�^(gu��)����(sh��))
- �x��:Ո(q��ng)���x***(ُ(g��u)�I(m��i)�^(gu��)����(sh��))
- ���}�������ռ�һ���I(m��i)�ĕ�(sh��)
���b�����ܷ⣻ɯʿ�ȁ���(j��ng)��Č�(xi��)ϵ���е�һ��(c��)���@���ǸČ�(xi��)�ġ��������
�x��:arm***(ُ(g��u)�I(m��i)�^(gu��)����(sh��))
- >
�����������
- >
����Ԣ��-�����ČW(xu��)�������-ȫ�g��
- >
�Ա��c��Խ
- >
����?gu��)����x��Ѹ:����Ϧʰ
- >
���{����,��Ҫȥ��(2021�°�)
- >
������
- >
���ČW(xu��)���ɾ���--��Ѹ�c���m/�t�T�W(xu��)�g(sh��)����(sh��)(�t�T�W(xu��)�g(sh��)����(sh��))
- >
Ԋ(sh��)��(j��ng)-����ĸ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