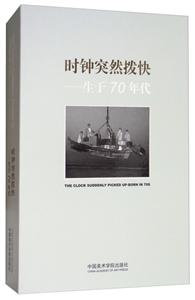-
>
東洋鏡:京華舊影
-
>
東洋鏡:嵩山少林寺舊影
-
>
東洋鏡:晚清雜觀
-
>
關中木雕
-
>
國博日歷2024年禮盒版
-
>
中國書法一本通
-
>
中國美術8000年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315143
- 條形碼:9787550315143 ; 978-7-5503-1514-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 本書特色
誰能說出這一切呢?每一個人都身處不同的語境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音與腔調。這本書的作者,是詩人、畫家、作家、評論家、導演。他們是*執迷不悟的觀察者與記錄者,他們追問人與這個世界的關系,用“創作”這個孤注一擲的方式——研磨情感,錘煉思想,熱情與冷酷都在一念之間。關于過往的這些陳述,是可能性的消失與個人歷史的定格,青年時代結束了。蘇七七、王犁主編的《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里,留下的是那些或明亮或幽暗的童年,是讀過的書,去過的地方,愛過的人。 我常常想不清楚,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的那些年。于我究竟是寶藏還是傷口。 ——毛尖 怎么辦?如果找不到歷史的契入點,你將無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價值感,如果無法感受到問題和矛盾之源,你就如進入無物之陣,陷入四面空虛的困境。難道因為我們生活在歷史的瑣屑之中,就不配擁有進入歷史并尋找自我的機會和權利? ——梁鴻 在現實的塵土飛揚與喧囂之中,你遲早會有一瞬,感到自己心中的音樂。與這座城市輕輕共振,如此悠揚,如此明亮。誰的生命曾被如此擦拭,必將終生懷念這段旋律。 ——綠妖 我落下來,成為新的灰塵,我知道這是宿命,關鍵這是要求的宿命。因此詩歌寫作就是一種要求,一種隱隱約約有聲響的要求,像一個黑衣人一瞬間路過了黑暗。 ——孫磊 離開那座山的后幾天,我回憶更多的倒是那條站滿松樹的路。我想塞尚在許多的日子里也曾走在類似的路上,背著一個框子和畫具,如同一個定時去耕作的農夫。我能想象的也只有這些,和他后來顯赫的結果比較起來,當初在工作的那個塞尚也許才是幸福的。 ——尹朝陽 誰能說出這一切呢?每一個人都身處不同的語境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音與腔調。這本書的作者,是詩人、畫家、作家、評論家、導演。他們是*執迷不悟的觀察者與記錄者,他們追問人與這個世界的關系,用“創作”這個孤注一擲的方式——研磨情感,錘煉思想,熱情與冷酷都在一念之間。關于過往的這些陳述,是可能性的消失與個人歷史的定格,青年時代結束了。這本書里,留下的是那些或明亮或幽暗的童年,是讀過的書,去過的地方,愛過的人。 ——蘇七七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 內容簡介
怎么辦?如果找不到歷史的契入點,你將無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價值感,如果無法感受到問題和矛盾之源,你就如進入無物之陣,陷入四面空虛的困境。難道因為我們生活在歷史的瑣屑之中,就不配擁有進入歷史并尋找自我的機會和權利? 在現實的塵土飛揚與喧囂之中,你遲早會有一瞬,感到自己心中的音樂,與這座城市輕輕共振,如此悠揚,如此明亮。誰的生命曾被如此擦拭,必將終生懷念這段旋律。我落下來,成為新的灰塵,我知道這是宿命,關鍵這是要求的宿命,因此詩歌寫作就是一種要求,一種隱隱約約有聲響的要求,像一個黑衣人一瞬間路過了黑暗。 離開那座山的后幾天,我回憶更多的倒是那條站滿松樹的路。我想塞尚在許多的日子里也曾走在類似的路上,背著一個框子和畫具,如同一個定時去耕作的農夫。我能想象的也只有這些,和他后來顯赫的結果比較起來,當初在工作的那個塞尚也許才是幸福的。 誰能說出這一切呢?每一個人都身處不同的語境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音與腔調。這《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的作者,是詩人、畫家、作家、評論家、導演,他們是*執迷不悟的觀察者與記錄者,他們追問人與這個世界的關系,用“創作”這個孤注一擲的方式——研磨情感,錘煉思想,熱情與冷酷都在一念之間。關于過往的這些陳述,是可能性的消失與個人歷史的定格,青年時代結束了。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里,留下的是那些或明亮或幽暗的童年,是讀過的書,去過的地方,愛過的人。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 目錄
序/在這個動蕩的盛世里蘇七七
梁鴻:歷史與“我”的幾個瞬間
韓松落:蘭州離別書
蔣志:沅江文學青年的回憶錄
毛尖:沒有人看見草生長
任曉雯:寫作是怎樣開始的
徐則臣:新世紀.com
廖偉棠:個70后詩人的雜食史
王一淳:不美好影集
綠妖:我曾遇到這城市的青春
黨震:灰色寓言
維舟:朝向開闊的彼岸
于艾君:外公的劇院
李云波:筋疲力盡,呼吸正常
張楚:野草在歌唱
柳營:他的佛
潘汶汛:落于萬物間
泉子:不存在的村莊
王曉漁:“一個人要多少次回頭”
桑格格:成都,成都
孫磊:灰塵從要求中落下來
王敖:一個70后的90年代
衛西諦:像我這一代觀眾
楊超:憤怒理想與自由理性
尹朝陽:遷徙者
杜小同:活著才是偶然
趙力:沒有流逝的記憶
祝錚鳴:杭州往事
金江波:不確定的記憶
張定浩:一份第三人稱的讀書自述
張莉:梨花又開放
譚韶遠:在路上
臧杰:從文青到文青
張見:如流記憶
夏烈:自我精神成長的考古記
王犁:排嶺的天空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 節選
《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 落戶蘭州之后,我被單位派回我家所在的小城,在那里的公路道班擔任養路工,我的職業生涯就此開始。 如果是運沙子或者石頭,每天的定量是12車拖拉機;如果是清理邊溝,每天的任務是120米;如果是油漆樹干,每天得刷完3公里路兩邊的所有樹干。休息的時候,我和工友們坐在路邊,觀看癡呆傻人。國道省道上,總是有那么多的癡呆傻人。有個終年不穿衣服的女人,還有個耷拉著舌頭、挺著大肚子在街上疾走的男人,還有個女人,總是在頭發上扎滿各種彩色的繩子和紙條。工友們笑嘻嘻地叫他們過來,給他們一塊糖,向他們問些奇怪的問題,聽他們胡言亂語。 那時開始,我決心讓我寫下的文字被人看到。不再像以前多少年來一樣,只是寫好,收起。 1996年,我的養路工生涯中,唯一能看到的一份報紙,離我*近的一份報紙,是《蘭州晚報》。它是蘭州唯一的一家小報,更重要的是,它有副刊版面。 我寫了信,給那時還在《蘭州晚報》副刊部工作的顏峻。那時,我對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詩人,是著名的樂評人,和我差不多年紀。但我能夠看出來的,是他的版面與眾不同,輪到他編的那期副刊,總是充滿了激越的、靈動的、新鮮的文字。我這樣想,他能夠欣賞那些文字,也許就能夠欣賞我。我寫了信給他,告訴他,我喜歡寫作,我也喜歡他寫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讓我覺得不孤獨,事實上,也是如此。我寄去了我寫的文章。那篇文章,叫《阿克塞爾·彼得森的木雕》,在1997年3月5日的《蘭州晚報》上,第7版,右上角。 顏峻給我回了信,大大的字,寫在《蘭州晚報》社的綠色格子的稿紙上,他說:“我們都是被命運驅趕……”他說,這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話。他寫給我的信,是我從字紙簍中找到的。是的,我的同事們,始終懷著一種對戴罪立功人員進行監管的態度和我相處,他們始終認為,我沒能留在蘭州,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他們毫不猶豫地拆看我的信件,看完之后,就丟進字紙簍中,并且在事后,故意閃閃躲躲地提及信件中的字句,看看我有什么反應。 從那之后,我開始使用我父親的地址,作為通信地址。 我的文章定期出現在《蘭州晚報》的第7版上。《蕭紅》《東山魁夷》《塞林格的(九故事)》《忘不了的書》《史蒂文斯》《火柴照亮的天堂》《焰火》《遙想(武林舊事)》《拾遺記》《懷斯三代》,我是如此珍愛這些文章,在許久之后也不能忘記,只是因為,它們,它們讓我忘記了自己,我仿佛已經能夠和我所寫的人比肩而立,仿佛已經可以平和地談及他們。我忘了自己,忘了12車沙子,120米邊溝,我知道我不在那里。而這一切,全都經過顏峻之手,他讓我忘了自己,忘了12車沙子,120米邊溝。 他總是給我回信,從不間斷,他給我說起那些我熟悉但又不可能認識的人,說起別人對我文章的印象。每封信,剪開封口,看完,我都把它立在書架上,直到下一封信代替它的位置。 他的信,總是寫在《蘭州晚報》社16開的綠格子稿紙上。那種紙,微微有些發黃,可以看見紙質的纖維;那種綠,是介于墨綠和草綠之間。他用藍黑色的墨水。還有,他的字,圓碩,沒有邊角,每個字都像是隨意畫出,卻清晰可辨,寫著寫著,那些字就離開了格子,像是快要向著信紙的邊緣傾倒而出。 ……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隨園食單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煙與鏡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月亮與六便士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