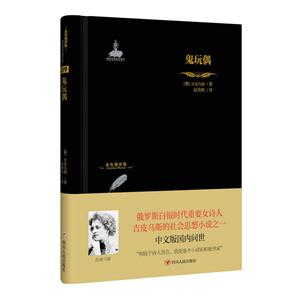鬼玩偶 本書特色
創作于1911年的小說《鬼玩偶》,以俄國1905年間發生的真實事件為故事背景,描寫主要人物尤里和米哈伊爾等人在俄國革命前的日常生活和境遇,還原俄國社會變革時期的歷史面貌,展現不同階層的人們對待俄國20世紀初歷史事件的不同態度和看法。作品不僅僅是對俄羅斯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描摹,而且還將吉皮烏斯本人的哲學、審美和宗教觀點融合在一起,用詩人慣用的象征手法重述人類存在的諸多永恒問題,如生與死、愛與犧牲、人的精神追求和探索、生活的意義和使命等。
19世紀以降,俄羅斯誕生了一大批世界級的文學巨匠,如普希金、赫爾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這些金子般的名字迄今仍在向世人閃爍著獨特的光芒。然而,作為一座富礦,俄羅斯文學在我國所顯露的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寶藏仍在我們有限的視閾之外。“金色俄羅斯叢書”進一步挖掘那些靜臥在俄羅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錠,向中國讀者展示赫爾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費特的唯美,苔菲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現實,哈爾姆斯的怪誕……可以這樣說,俄羅斯文學史即一部絕妙的俄國思想史,它所關注的始終是民族、人類的命運和遭際,還有在動蕩社會中人類感情的變異和理性的迷失。
“金色俄羅斯叢書”由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詩人、翻譯家汪劍釗主編,遴選普希金、赫爾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大師的經典作品,向中國讀者呈現優美而深厚的俄羅斯文學。
鬼玩偶 內容簡介
創作于1911年的小說《鬼玩偶》, 以俄國1905年間發生的真實事件為故事背景, 描寫主要人物尤里和米哈伊爾等人在俄國革命前的日常生活和境遇, 還原俄國社會變革時期的歷史面貌, 展現不同階層的人們對待俄國20世紀初歷史事件的不同態度和看法。作品不僅僅是對俄羅斯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描摹, 而且還將吉皮烏斯本人的哲學、審美和宗教觀點融合在一起, 用詩人慣用的象征手法重述人類存在的諸多永恒問題, 如生與死、愛與犧牲、人的精神追求和探索、生活的意義和使命等。
鬼玩偶 目錄
第二章學生方式/009
第三章嬌艷的花/014
第四章在母貓味兒的樓梯上/016
第五章階下囚/021
第六章多樣的愛/028
第七章鞋掌上的干草/044
第八章睡覺覺吧/049
第九章臥談會/054
第十章豐坦卡宅邸/067
第十一章法國女人/078
第十二章消遣/083
第十三章約會/090
第十四章何為罪/094
第十五章薩沙的事/097
第十六章自殺者/101
第十七章女裁縫/106
第十八章老生常談/113
第十九章判決/121
第二十章鬼玩偶/125
第二十一章槍聲事件/150
第二十二章屋頂上的馬蹄聲/159
第二十三章三一會/175
第二十四章幽暗的笑/191
第二十五章兒童娛樂/196
第二十六章沉默/205
第二十七章未收到的信/214
第二十八章末日/216
第二十九章咸海和綠海/231
第三十章公開的和秘密的/243
第三十一章過客/257
第三十二章紅房子/270
第三十三章頭骨/286
鬼玩偶 節選
第二十章 鬼玩偶
人們紛紛到場。
大概,全都聚齊了——人山人海。幾乎所有人都聚集在餐廳和隔壁的各個房間里,都還沒進入大廳。大廳里匆匆忙忙占位子的只有老人,胖瘦都有,以及女士和新來的一些普通訪客。
整個房間寬敞無比,顯得有些愚蠢,不知能用來做什么。其實,這里有個圖書館,在后面,有些暗,但很涼爽。而這個“時事”社團搞活動的大廳是組織者們按自己的方式布置的,布置得非常奇怪:長桌從主席臺搬下來放在房間中央,觀眾們坐的椅子圍成圈,分成幾排。這不是很方便,大廳長而狹窄,但莫爾索夫和他的助手們就決定這么干:他們厭惡“主席臺”,甚至想徹底鏟除“觀眾”;他們夢想的會議是每個人都能發言,能全程參與的大會。
這當然只是夢想,大多數與會者只是“觀眾”;雖不是普通觀眾,但終究只是觀眾。
尤里一踏進門就喜歡上這里的一切。
尤里把戰戰兢兢的麗塔安頓在大廳里坐下,大廳里分外刺眼的燈光讓她更加窘迫,尤里穿過餐廳慢慢向遠處擠出去。多么神奇的大會啊!是什么促使這些人同處一地呢?跟隨潮流?無所事事?熱衷“時事”社團?天真?玩耍?到底是什么呢?
尤里意識到,這些原因都有可能:既是興趣使然也是百無聊賴,既是游戲也是空虛寂寞。
來了很多“文化”人。“末代詩人”——長得像阿普赫金的胖子拉耶夫斯基正在和不修邊幅的“前輩詩人”雷日科夫安靜地交談。冷淡客氣的雅什文,在哪都是一個模樣——無論在家里、去做客還是開會;任何時候都始終如一,無論是中飯、晚飯還是早上五點。他正緩緩地向胡子剃得光光的禿頂小說家格魯哈廖夫做解說。這個格魯哈廖夫想出了自己一套宗教理論并信奉它,但事實上,他沒有纏著任何人宣揚自己的宗教,和別人爭辯也總是漫不經心。
小教授雷亭在人群里似乎馬上就要跑走,因為雖然他喜歡人群,但是希望和人群有些距離,*好他能從講臺面向大家。熱情洋溢、皮膚黝黑的歷史學家彼托姆斯基已經在和一排緊挨著坐在一起喝茶的記者們相互爭論起來。
尤里穿過人群走向彼托姆斯基,因為對方能幫他找到莫爾索夫。向左望去,門邊站著另一群人:所有的人都很莊重,有老有少,有穿著束腰細褶長外衣的,有蹬著大皮靴的。不遠處,尤里在一件沒塞進褲腰的藍襯衫后面發現了牧師十字架的閃光。
尤里其實還沒顧上仔細觀察眾人那些形形色色的臉龐;或許,它們比身上的衣著還要五花八門。一群類似高等女校學生的姑娘們在會場里來回穿梭,甚至還有一個婦女,不是“女士”,而明顯是一個婦女。她就站在墻邊一動不動。
“這才是聚會!”尤里快樂地想,“隨心所欲!”
緊挨著彼托姆斯基身旁,尤里碰到一位年輕且極具才華的詩人。詩人向他轉過臉,這是一張面無表情的漂亮臉蛋。
“您好。”
“怎么,您也在這兒啊!”尤里驚訝道,“您可是個隱士啊。”
“沒有啊。為什么這么說啊?我還在這兒看摘要呢……”“真是怪事!”尤里又想了想,叫住了彼托姆斯基:
“謝爾蓋·斯捷潘諾維奇!”
彼托姆斯基看到他很高興,但表現得有些夸張(他生性如此),并提議去藏書室。
路上尤里還發現了人群中的許多熟悉面孔,這些人能來很出乎意料,似乎他們從來都不會來這里的。
“你們這兒總是有這么多人嗎?”他問彼托姆斯基,他們從后面穿過人群去藏書室。
“是啊……這都是觀眾。不過觀眾當中有那么幾個杰出的人。”
莫爾索夫站在閱覽桌旁,不厭其詳地向一個上了年紀的靦腆女士做解釋。他身旁一個年輕的秘書迫不及待又躊躇不安:他覺得,大會應該開始了。
房間深處的壁爐旁有幾位教授模樣的人在那低聲交談。
莫爾索夫莫名其妙地一把抓住了尤里。
“您會發言嗎?會嗎?什么題目呢?您這回可看到我們的聽眾了!”
“我看到了,我不知道會不會發言。你們這兒什么人都有。該對誰‘發言’呢?”
“都有嗎?就應該對所有的人發言啊。本來就應當和所有的人交流呢!”
尤里笑了。
“您知道嗎?您說得沒錯。”
然后他又暗自思忖:
“發言是完全不需要的,但如果是游戲的話,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呢?”
秘書迫不及待地開始搖鈴。藏書室滿是人了。姑娘們一會兒跑向莫爾索夫,一會兒奔向雷亭,一會兒蹭到彼托姆斯基旁,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其中一個姑娘和尤里攀談起來。幾個工人正心平氣和地說服一位教授模樣黑頭發的人。維亞切斯拉沃夫出現了,他小心翼翼、一步一跛地向前走去。尤里對他知之甚少,莫名不太喜歡這位知名的作家,而此時此刻,尤里正饒有興味地端詳著他那散發金色光澤、稀疏蓬松的頭發下的面龐。
“如果他發言的話,有可能,會像莫爾索夫一樣,談談‘判決’這個話題。”尤里記得,莫爾索夫曾經自稱是這位作家的擁躉。
人們從藏書室涌向大廳,靠近桌旁,在一排排椅子間穿梭。
大廳擠滿了人。燈光和悶熱的預感籠罩著尤里。桌子不大,幾乎所有尤里的熟人都緊挨著坐在桌后。他更仔細地環顧四周。令他驚訝的是,那些他稱之為文化人和“社會精英”的人穿過餐廳都聚集在后排,而近處圍著桌子的,尤里看到的是一些老成持重穿長袍的人以及幾位著偏領男襯衫、外套夾克的年輕人——他們明顯是工人的裝束。
“嗬,有特色的地方主義,”尤里想,“莫爾索夫在搞民主。”
尤里仔細看了看后排,找到了麗塔。她旁邊是位女士,看不到臉,只看見額邊深色的劉海兒,彎腰坐著。尤里沒有看到科諾爾。再遇到誰他都不會驚訝了。恍惚覺得,所有人一定都在這兒,只是有些看見有些沒看見而已。
“先生們,”莫爾索夫開場,“我們像往常一樣沒有主席,我們避免一切官場上的形式,我們不喜歡善于辭令的演說家,我們希望我們的座談會不再是以前的模式。每個人都可以加入談話,對他偶然想到的內容加以解釋,我只負責監督*必要的秩序。我現在就用以下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段作品的理解開始我們的座談。”
“看吧,你發言是因為你應該發言。”尤里心想。
盡管莫爾索夫的發言沒有展現什么實質性的獨特新觀點,他的發言依然很精彩漂亮、有趣而充滿智慧。內容有些冗長和復雜,但還是透著智慧。他在發言伊始說道,這封由唯物主義自殺者因為無聊而臆想出來的信業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普遍病癥的幾乎所有真實自殺事件的基礎。假如每個人都能或者可以向自己徹底解釋清楚臨死之前的心理狀態,他都會留下這樣一封信。每一位自殺者都認為“無法生活”,因為沒有什么事情值得自己“同意繼續受苦”。實際上他想的是,為了什么呢?大自然有什么權力,沒經過他的允許,創造他這樣一個痛苦生活的人?人生是什么樣子呢?接下來:就算生活會改變,就算可以安身立命,按照理性的、科學上正確的社會基本原則構建自己的家園,而不是像在此之前那樣生活。他還是會問:為了什么呢?因為意識告訴他,明天這一切都將不復存在、化為烏有,包括所有“幸福的”生活和他本人。正是因為受到“明天一切將化為烏有”這樣的威脅,所以無法生活。“正是這種感受,這種直接感受,我無法與之抗爭。”
莫爾索夫細致入微、旗幟鮮明地宣傳這種“直接感受”。他證明,當你有這種感受,實際上無法繼續生活下去哪怕一秒鐘,這感受其實滲透在每一個人心中——即便是這里在座的各位——他們或許都活不到明天早上。
“我知道,”莫爾索夫補充道,“很多人真誠地幻想,即便他們確定死后自己的個體將會完全消失殆盡,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想要自殺。正是后面這一點證明,他們根本沒有仔細地思考問題,沒有非常清楚地看到自己所面臨的‘化為烏有的明天’,而他們的‘直接感受’和他們對‘化為烏有’的認識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確信,個體的概念……”
“還要繼續說啊,我建議過他不要夸夸其談的,”無所事事的尤里心想,“看來他根本沒有停止的打算。現在要講到基督教了。”
但莫爾索夫剛一談到基督教就岔開話題,完全跑到一邊去了,開始說些更讓人聽不懂、更繞的話,然后就結束了發言。
任何人都沒有做任何點評,況且也沒有機會,因為莫爾索夫的話立刻被彼托姆斯基接了過去。他旋即開始談起信仰、基督教,談起個體不朽說以及人的洞察力,也說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犯的一些嚴重錯誤。他慷慨激昂,尤里甚至驚訝不已。若一直眼睛盯著他會有些困難,但聽他說話卻莫名地讓人歡喜。尤里看見一些年邁的女士向前豎著兩只干瘦的耳朵,全神貫注地聽著這位黝黑的歷史學家發言,而歷史學家的夾鼻眼鏡總是由于激動滑向一邊。
他的發言莫名其妙地突然中斷了,出人意料。
“他們這是在為誰演說呢?”尤里暗自冷笑,“如果是為了那些老成持重的階級宗派主義者,那就是因為他們信這個,而如果是為了拉耶夫斯基、格魯哈廖夫、斯塔西克和我的麗莎,他們指望什么呢?”
但是,尤里其實馬上又意識到:“這不是專為了某個人。是為所有人……為自己。這本來就是一場游戲!”
彼托姆斯基結束發言后,鄰近的幾排人群開始騷動。一個年輕人清了清嗓子,他臉寬寬的,眉毛微微翹起。穿著藍色襯衫,可能是個工人。
“您想說話?”“非正式”主席禮貌地轉向他。
那個年輕人又咳嗽了一聲,沒有一絲畏懼、斷斷續續地開始發言:
“我……關于您的發言想說點什么。為什么我們要這樣立刻糾結著思考死亡,虛無和其他什么東西呢?……我們活著,很簡單,那就意味著,自我保護的本能還在運作。假如,虛無已經被證實了,我是說假如……大自然的本能將會有所行動。那么,比如說,我將來會饑餓嗎?而如果會饑餓的話,那我會開始尋找食物,那我將面臨虛無還是真實……”
“啊哈,”彼托姆斯基抓住一點,突然大喊,“也就是說,您認為,已經被證實是存在虛無的嗎?科學所達到的、所確定的就是一勞永逸的嗎?科學是在哪兒確定的呢?”
莫爾索夫微微揮了揮手。
“勞駕,勞駕,這和問題無關……”
但彼托姆斯基已經和小伙子爭執起來,兩人各抒己見,完全不顧對方的言語。還有幾個人也加入進來,形成一場混戰。一位穿皮靴的年邁長者不時捋捋自己灰白的胡子,嗡嗡說道:
“不是的,這當然是正確的……人的靈魂怎么可能不永生呢?但是也不必自作聰明……宗教人士大概也弄錯了……人們正在喪失信仰……”
“您在說,信仰……”一個姑娘在后面大喊了一聲并探身朝向彼托姆斯基和莫爾索夫,“那么如果丟失了信仰,又該如何獲得信仰呢?我經常在這里,聽演講,期待著;我以為,我會聽到這方面的內容……”
莫爾索夫無所適從,他搖了搖鈴。人群安靜了一些。一位年輕人,或者說只是看上去年輕的一個人站起身來,他憨態可掬,眼神銳利。
“我是這么認為的,先生們,我們很難為所有人作決定,盡管我們聚在一起,公開談論。當然,我認為現在任何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神,或者說自己的真理,他為了真理而活,不會折磨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想好了,就這樣生活。但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在眾人面前傾吐自己真理的時機還沒到。還沒到,還沒到時候。有的人即便完全知道,也相信自己的真理適用于所有人,但說實話,他也不會公之于眾的。沒有人說得出普遍的真理,也沒有地方可說,誰都不會徹底并且坦誠地說出來。這很好……”
“也就是說,您認為,”彼托姆斯基勃然大怒,“認為,認為我們……不真誠……”
眼神銳利的年輕人憂傷地望了他一眼。
“我不是說這個。”他嘆了口氣想繼續說,但這時尤里聲音洪亮、平靜而愉快地打斷了他:
“您說得不對。為什么誰都不會說呢?不是所有人都這樣的,有人會說的。比如我,不論何時何地,如果有人問我,我會坦誠地告訴對方,我靠什么生活,我生活得怎么樣。這就是我的真理,我還認為,它適用于所有人。我不去宣揚它,正是因為我非常確定它的普遍適用性。很多人現在就是以此為生,但可憐的是,自己卻不知道這一點。要去了解,理解——這是非常重要的。之后,所有的人都會了解。一定會的。至于什么時候能了解,是不是快了——我并不關心,對我來說都無所謂。”
“您是在說謎語嗎?說得含含糊糊的。”眼神銳利的年輕人拖長了聲音,直盯著尤里那張帥氣活潑的臉。
“請說說吧,說說吧!”莫爾索夫吆喝起來,打斷了別人的話,忘了自己不是“正式”主席,宣布道:“先生們!請尤里·尼古拉耶維奇·德沃耶庫洛夫發言!”
從自己的位置上尤里看不到坐在他后面的人,但他聽到身后有椅子響動。眼神銳利的年輕人就坐在他前面,穿著長袍的老先生們離他也很近。而在他們身后突然閃爍著一對熟悉的藍眼睛,但這是誰的眼睛——尤里沒時間猜。一切都讓人非常快樂和趣味橫生。
......
鬼玩偶 作者簡介
作者:
吉皮烏斯是俄羅斯“白銀時代”zui具個性、zui富宗教感的女詩人之一,她的創作被譽為“有著抒情的現代主義整整十五年的歷史”,其詩作在展示人類在生命的兩極之間彷徨、猶豫、掙扎的浮懸狀態的同時,也體現出這位女詩人對存在所抱有的“詩意的永恒渴望”,以及在苦難中咀嚼生活的甜蜜、在絕望中尋覓希望的高傲。
譯者:
趙艷秋,文學博士,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俄文系副系主任,國立莫斯科大學訪問學者,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上海市外文學會會員。主持教育部課題1項,參與國家ji社科項目1項,另有主持和參與校級或院級項目6項。獨立完成著作1部,參與編寫著作1部,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翻譯作品50萬字以上。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朝聞道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自卑與超越
- >
經典常談